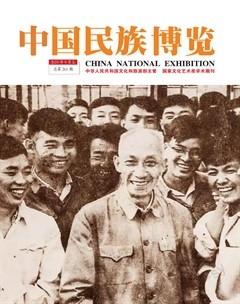“靈韻”與繪畫
【摘 要】“靈韻”概念由瓦爾特·本雅明在其著作《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出,隨著復制技術的出現與發展,傳統藝術面臨“靈韻”消失的危險,本文在對“靈韻”概念的研究與解析之基礎上,分析藝術的“靈韻”與復制技術、復制技術與繪畫之間的關系問題。
【關鍵詞】靈韻;繪畫;機械復制;藝術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17—208—03
一、“靈韻”的提出
本雅明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靈韻(Aura)”(也譯為“光暈”)一詞,它指涉過去的傳統藝術當中所共有的一種東西。在他的《攝影小史(1931)》,他是這樣解釋“靈韻”一詞的:“早期攝影中籠罩著一種靈韻(Aura),一種給人沁入其中的目光以滿足和踏實感的介質”[1],“那是時間和空間的一種奇異交織,是遙遠的東西絕無僅有地做出的無法再近的顯現。”[2]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是這樣定義的:“我們把自然事物的靈韻定義為遠方某物使你覺得如此貼近的那種獨有顯現。”[3]本雅明的描述是相對模糊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靈韻被描述成連接注視者和被注視者的中間介質,也就是作為主體與客體間的介質,這種介質表現為人的體驗,依靠人的主體感受,人通過體驗感受事物獨有的“靈韻”,而無法通過觀看獲得“靈韻”,“靈韻”不在注視當中,而在特定場景的感受中。另一方面,一件作品是否具有“靈韻”需要同時滿足時間和空間的共時性,與傳統發生聯結,并且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的特征,也就是所謂的“原真性”,才能夠顯現出其自身的“靈韻”。
本雅明肯定了攝影術出現的重要性,它預示著從前沿襲長久的傳統復制技術將迎來巨大的革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復制技術的變革將從前從事藝術創作的工匠和手藝人所特有的“再現”現實事物的技能中解放了出來,從此以后,“再現”某個窗外的景物或任何什么東西的介質,交給了那些掌握了攝影技術的觀察者,他們通過操作底片和光圈等一系列步驟,將鏡頭對準需要進行“再現”的事物,完成對現實的復制。這樣的“革命”性變化,本雅明敏感的捕捉到了傳統藝術即將受到的挑戰和隱含的危機,即藝術作品當中“靈韻”的流失。
二、“原真性”的祛散
本雅明提出“原真性”是指原作的“此時此地性”[4],過去的傳統藝術具有獨一無二的存在性,藝術作品的產生與發展都高度依賴于一個地區特有的歷史脈絡與人文記憶,產生出獨特的藝術作品,正是藉由這些特性,不同地區產生出來的藝術才會出現不同的面貌,擁有獨特的地理性特征,作品本身反映了獨特的歷史性,是歷史的一部分,“原真性”正是在歷史當中得以顯現自身。因為作品擁有獨一無二的歷史性,并且以物質的屬性存續,所以在復制品面前,具有“原真性”的作品自然而然的擁有了它的“權威性”。
過去的傳統藝術最廣泛、最重要的屬性是具有“膜拜價值”,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傳統和禮儀的不斷發展,為藝術的“原真性”提供了社會基礎,可以說“膜拜”效應使藝術深深地嵌入其歷史傳統中。
可是,隨著復制技術的出現,情況發生了變化,復制技術的發展將人的手解放出來,“使所負責的東西從其傳承關聯中脫離了出來”[5],藝術作品中的“原真性”開始逐漸褪去與消散,從前原作呈現出的視覺景觀,此后通過復制品便可以一覽其貌,并在不同的時空當中輕易地被提取觀看,復制品代替了原作的存在所具有的獨特性,也取代了只有原作才能帶給人的獨特感受。因此,機械復制手段使那些復制品具有了“現實感”。人們通過復制品這種中間物去體會原作的真實,因其無可避免的流失了“靈韻”,所以對“原真性”的感知必定是不完滿的。“靈韻”與“原真性”是不等同的,當我們觀看一件作品的時候,原真性“是它的物性和事性的統一,靈韻則是它的事性層面。”[6]技術復制手段的出現無法將事性層面的“靈韻”保留,故而導致觀者無法在復制品面前體會到在原作面前那樣的完滿感受,這是機械復制本身帶來的遺憾。但是,復制技術也為藝術生產提供了新的方式,其中可能蘊含著巨大的潛能。
三、“靈韻”之后的繪畫
19世紀的西方思想界,理性主義獲得了主導地位,啟蒙思想深入人心,藝術領域呼喚創造新的藝術風格和形式,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下,人要用理性做自然的主人,自我進一步被強調,這還不夠,然后是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受限地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新的觀念興起與復制技術的發展孕育了現代主義。
過去沿襲下來的偉大的藝術傳統里包含了透視法、明暗法、解剖學等基本法則,通過對現實的“模仿”去“再現”凝視的現實,目的在于呈現出逼真的視覺“假象”,營造三維空間的錯覺,以假亂真,以實現其自身的膜拜價值。復制技術的出現,使得藝術不再必須依賴過去的準則,該層面的變化預示著新的藝術生產方式的出現,但它不會導致有“靈韻”的藝術完全消失,“有韻藝術與無韻藝術并不是一個藝術發展分期的問題”。[7]實際上,無“靈韻”的藝術是相對于有“靈韻”的藝術而言的。
某種程度上,過去傳統藝術的神圣性被“祛魅”了,本雅明讓人們認識到,“原初的藝術創造活動只是藝術作品得以產生的前提”,“而復制活動則是藝術創造活動的技術化和擴大化。”[8]復制技術使得藝術品的批量生產成為可能,藝術復制品的大量出現催生了藝術商業產品的繁榮,幾乎沒有什么藝術作品是不可以被復制的,幾乎沒有什么復制品是不可以成為商品的。復制技術使得藝術傳播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更便利,更廣泛,效率更高,它“打破了精英階層對藝術的壟斷,使大眾也能參與藝術作品審美,技術和大眾的合作發揮出藝術的革命潛能。”[9]
在阿瑟·丹托對攝影與繪畫之間的比較和探討中,視覺和照相機通常所復制的“物”是不一樣的[10],照相機呈現的只是人的眼睛通過光學鏡頭注視的東西,這被認為是“光學真實”,而人眼實實在在地看到的東西,叫做“視覺真實”。丹托舉出的例子是埃德沃德·邁布里奇拍攝的奔跑的馬的一組攝影照片,在這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學真實”與“視覺真實”的不同。攝影術的發明為藝術創作者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就是“光學真實”,人眼從未感知到過的現實的另一種真實得以呈現在觀眾面前。丹托指出,繪畫的真實性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攝影這種“自然之筆只是捕捉了在鏡頭前的東西,沒有什么創造性想象力”[11]。也就是說,攝影之眼只能呈現物本來是什么,而在繪畫那里,藝術家之眼可以呈現物還可以是什么,所以,畫家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創造繪畫之“真實”,想象力成為了藝術家重要的工具。隨著藝術發展到現代主義階段,追求三維空間的深度已不再成為藝術家的興趣所在,藝術家的興趣轉向了更多的領域。
在繪畫領域,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等一系列新藝術實踐的發展為繪畫帶來全新的面貌,藝術家開始追求主觀的色彩、追求物像的變形、追求情感的抒發等等,突破了古典主義建立的美學標準,不斷地提出新的標準。攝影術的出現給繪畫帶來的沖擊在于,過去的傳統中“再現”事物真實的表面已經輕而易舉地被一項新發明解決,那么藝術的任務就發生了微妙的改變,至少對藝術家來說,求新求變成為了這一時期藝術家的共同目標,對于“新”的崇拜使得現代主義的藝術家們往往背離上一代藝術家們建立起來的審美標準,這是一種現代藝術內部的否定式延續。“現代藝術的其他派別也不同程度的驗證著本雅明理論的合理性”[12],反傳統、反經驗正是現代藝術的特點。
四、攝影與圖像時代的繪畫
戰爭之后,繪畫迎來了新的困局,達達主義的出現意在否定整個西方繪畫傳統,否定過去的繪畫主題和標準,杜尚作為現代藝術的先鋒人物,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架上繪畫,目的在于超越繪畫,將生活拉進藝術。面對這些變局與挑戰,這個時期的許多仍然堅守架上繪畫的藝術家也在進行積極的思考。同時,由于攝影術的傳播,一些畫家把目光投向攝影,開始利用攝影照片進行他們的繪畫實踐。
20世紀借助攝影方式進行繪畫創作的藝術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藝術家當屬德國藝術家格哈德·里希特,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基于圖像之上的再加工,形成了所謂的“照片繪畫”風格。他的作品表象看起來很像照片,但卻不是追求寫實的目的,藝術家刻意將繪畫出的對象進行模糊化處理,大面積的黑白灰構成作品的主要基調,探討記憶、歷史等主題,內化作者的思考于其中。里希特對攝影與繪畫的思考使他的作品產生了新的面貌,也讓繪畫產生了新的生機,他的創作為其他藝術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本和啟示,那就是攝影與繪畫之間是可以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影響、互為滲透的關系。
進入20世紀后,攝影技術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第一部數碼相機由美國柯達公司推入市場,攝影數碼化在隨后幾十年獲得了飛速發展和迅速普及,在大眾化、輕量化、便攜化和智能化的道路上獲得了主流市場的青睞,這也標志著大眾攝影時代的到來,進入21世紀后,更是一個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攝影不再是一個世紀前只能作為貴族或上層人士的小眾奢侈品,而是在一百多年的發展里不斷下沉到普通的中產階級再到普通的大眾也可以觸手可得的工具。而傳統的膠卷相機則逐漸淡出主流市場,被一些專業人士或愛好者所青睞。攝影的普及伴隨著電視媒體、新聞攝影的快速發展,其帶來的結果是圖像爆發式的增長,圖像以一種無孔不入般的勢頭逐漸充斥、占領著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這也預示著圖像時代的到來。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消費文化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大眾消費品,攝影及其生產的影像也毫不例外的成為大眾消費品。
這些領域的新發展和新變化,導致民眾與藝術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藝術品和人類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了,藝術家開始重新“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將其應用到藝術創作當中。在繪畫領域,許多稀松平常的生活用品,過去那些被認為無法入畫的日常之物,包括在城市化進程和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中的流水線產品,也開始出現在越來越多藝術家的畫面內容當中。美國波普藝術的代表之一安迪·沃霍爾是非常典型的將各種復制技術廣泛的應用到藝術創作當中的藝術家,他運用版畫絲網印刷、照片投影等多種復制技術,成批量的復制作品。
那么,這就帶來了新的問題,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采用新的復制技術手段生產藝術作品,復制品是不是藝術品呢?對復制品的復制品是不是藝術品呢?這無疑是棘手的問題,我們需要對復制品與藝術品在定義上有一個清晰的界定,這樣我們才能進一步去確定更具體的區分。但是,藝術史告訴我們,“藝術”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不斷流變、發展的概念,同樣的,技術發展演變的歷史告訴我們,技術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事物,復制技術也有很多種類,所以,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在當下回答復制品是或者不是藝術品都未免是個有些武斷的結論,我們可以暫時給出是或不是的回答并拿出適當的理由,但我們無法給出一個絕對的回答,我們必須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下不斷地考察這二者。
另一個問題是,本雅明所說的“靈韻”究竟有沒有完全消失?有學者認為“靈韻”的衰退不能夠證明其美學價值的喪失,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藝術欣賞方式發生了轉折與變化,藝術‘靈韻或許是在用另一種物質形式和另一種審美功能在替換或表現而已。”[13]“靈韻”是一個被廣泛討論和闡釋的概念,藝術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闡釋,在21世紀圖像時代的大背景下,技術注定還將一路高歌猛進,繪畫也將不斷面臨新的境況,21世紀的藝術的“靈韻”可能會以一種更為隱匿而含蓄的方式體現在藝術作品中,又或者代之以其他更新的語詞被闡釋出來,這是有可能的。
五、結語
當下復制技術的發展和復制技術與日常生活的緊密嵌合,恐怕早已超出本雅明書寫《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所處的時代所能想象到的程度,可以預見,“靈韻”這一觀念還將影響后來的研究者。之所以回望過去偉大的藝術傳統,是為了捕捉可能留存的“靈韻”之“余韻”,“靈韻”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過去的藝術,而技術的不斷發展必將催生新藝術的產生,我們需要認識到,技術本身帶有一種革命性的力量。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技術與藝術結合得更緊密的時代,繪畫在與新技術的碰撞中將繼續產生出新的火花,呈現出新的面貌。
參考文獻:
[1][2][3][4][5]本雅明.藝術社會學三論[M].王涌,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6]盧文超.藝術事件觀下的物性與事性——重讀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J].文學評論,2019(4).
[7]溫恕.從《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看本雅明的藝術生產思想[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8]冉彬.本雅明對機械復制時代藝術作品與受眾關系的分析——兼及與阿多諾的論爭[J].理論學刊,2005(8).
[9]王洋.審美政治化:藝術作品的革命潛能——讀《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J].人文天下,2021(6).
[10][11]阿瑟·丹托.何謂藝術[M].夏開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12]楊玉珍.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評析[D].保定:河北大學,2006.
[13]楊湛.藝術“靈韻”與藝術大眾化——重讀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J].寧波教育學院學報,2019(1).
作者簡介:王偉斌,男,漢族,云南文山人,學術型碩士,美術學專業,魯迅美術學院21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新古典主義精神在當代語境下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