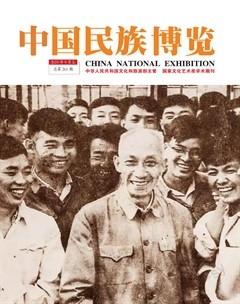貴州地方民俗旅游文化與外宣
黃丙剛 楊勇
【摘 要】地方民俗旅游文化既是國家最新“三農”工作中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點,也是國家文化與外宣中不可或缺的例示。地方民俗旅游項目不應僅囿于本土,更要著眼于跨境乃至跨國的外宣途徑以實現己身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目標。貴州地方民俗文化資源豐富,然而相應的外宣研究近于邊緣地帶。基于可及文獻的綜合梳理,研究認為,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屬于中國文化負載項,文化負載項的通用翻譯策略適用于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外宣。
【關鍵詞】三農;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外宣;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G127;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17—241—03
引言
201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2019中央一號文件。文件提出以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著力發展休閑旅游、餐飲民宿、文化體驗等鄉村新型服務業。于此,包括鄉村旅游的地方民俗旅游文化項目得以前景化,其己身發展有重要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意義。受其屬性的影響,國內對于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有顯性的地域特征劃分,如廣西、青海、海南、新疆、貴州等不一而足,而研究視閾主要集中于文化產業、項目發展、可持續發展等主題。
地方民俗旅游文化項目其產品開發、行業發展等不應僅囿于本土,還需跨學科、跨行業研究途徑的介入,更需兼具跨境乃至跨國外宣的格局,從而充分挖掘項目潛勢,促進地方區域經濟發展。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外宣,作為當前業內研究的邊緣地帶,正是本文探討的契入與著力點。
一、地方民俗旅游文化與外宣
(一)地方民俗旅游文化
民俗文化是指民間民眾的民俗生活文化的統稱,也泛指一個國家、民族、地區中集聚民眾所創造、共享、傳承的風俗生活習慣,是在普通民眾(相對于官方)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現象。從社會心理上,民俗文化旅游有審美新奇、心理愉悅和異質化文化體驗之功用;從旅游價值上,民俗文化有利于發揮本地或區域資源優勢,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是我國各民族、各地方間融通并邁向世界的通道,更是境外、國外了解我國地方或區域的重要窗口;從意識形態上,民俗文化旅游還可強化意識形態教育功能,進而弘揚民族精神。而所謂地方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人們離開己身慣常住地,到異地以其區域內民俗事項為主要觀賞內容而進行的文化旅游活動。地方民俗旅游有目標市場明晰、文化異質、文化體驗等顯性特征。
(二)文化外宣
文化外宣是文化對外宣傳的簡稱,是相對廣義的概念。“文化”有國家、民族、區域或地方乃至鄉村層次之分,而“對外”也有區域外、民族外、跨國家等不同的范疇,考慮個別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也有“域外”“境外”之說。不論是異域者引進來,還是本域者或本域文化走出去,更不論載體是主觀能動的人,還是文本、媒體,翻譯是文化外宣的必經途徑,有語內翻譯(intra—translation)和語外翻譯(inter—translation)之辨。本文語境中的翻譯專指狹義上的語外翻譯,也即一般意義上的翻譯(translation proper),同時鑒于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的考慮,又特指中—英翻譯。所以,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翻譯,是指把中文地方民俗旅游文化以英語進行語外翻譯,從而實現地方民俗文化的外宣。
二、貴州民俗旅游文化資源與外宣研究現狀
(一)貴州民俗旅游文化資源
貴州民族眾多,民族文化豐富多彩,其中苗、布依、侗、彝、仡佬、土家、水、回、壯、瑤等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歷史上,貴州曾是夜郎國所在地,夜郎古族有著與巴蜀、大理、滇國、南越的西南諸古族齊名的久遠輝煌的歷史。民族節日、酒文化,蠟染與刺繡、銅鼓與蘆笙、苗侗舞蹈、攤戲等眾多民俗文化活動可謂不勝枚舉。如以范疇劃分,又可大致分為飲食民俗類、建筑民居類、服飾民俗類、節慶民俗類和游藝民俗類等。
除此之外,紅色旅游文化也是貴州民俗旅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文中所指地方民俗旅游文化,是廣義概念,包括了其他研究者獨立分析的“紅色旅游文化”。根據新華社報道[1],2018年3月,貴州制定并頒布了《貴州省紅色旅游發展實施方案》,貴州將打造以“遵義會議”“四渡赤水”為代表的黔北紅色文化區,以“黎平會議”“木黃會師”為代表的黔東長征文化區,以“息烽集中營”“王若飛故居”為代表的黔中紅色革命旅游區和以“雞鳴三省”“盤縣會議”為代表的黔西紅色文化旅游區。
(二)外宣研究現狀
在貴州省坐擁豐富民俗旅游文化資源的背景下,為了描繪相關文化外宣的全景圖,“文獻計量法”是常用手法之一。以“文獻互引網絡”進行分析,按關鍵詞由高至低的頻次排名,前10位分別是鄉村旅游17次、民俗體育12次、民俗文化10次、體育旅游9次、生態博物館7次、民俗體育旅游7次、非物質文化遺產4次、民俗旅游4次、民俗文化旅游4次和少數民族4次。
然而與筆者研究假設相左的是,貴州“紅色民俗文化”或“紅色旅游文化”的相關研究并沒有出現于本組文獻中,這也佐證了部分學者提出的學理方面的爭議,即“民俗旅游文化”是否可以作為上義詞從概念的外延上包括“紅色民俗(旅游)文化”,本文持廣義概念立場。
綜上,通過文獻計量手法證實了本文引言中的概論,即當前國內學界研究中廣義上的貴州民俗旅游文化(包括紅色民俗文化)外宣處于邊緣地帶,數量不多,質量也不高,亟需跨學科、跨行業、跨部門研究的介入。下文中將在概述文化外宣通用翻譯策略的基礎上,結合貴州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的實例進行探討。
三、貴州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翻譯策略
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屬于某一國家或民族特色文化負載項,也有學者稱之為文化專有項(culture specific)。所謂文化負載項,廖七一在其翻譯專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中定義為“某種文化中特有的關于事物表達的詞、詞組或習語”[2],這些不同結構層次的特有表達體現或反映了民族經年累積而又獨一無二的活動方式和對世界的認識。包惠南則認為,翻譯中的文化負載詞是一種詞匯缺失現象,即源語中的某種詞(組)或習語表達在目的語中沒有相應的體現文化特色的“對等”(equivalence)[3]。但是這并非意味著文化負載項的不可譯,而是要采用“非常譯”策略,正如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所言,“人類共性使翻譯成為可能”。
(一)通用文化負載項翻譯策略
簡單說來,直譯是指既保持原文內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譯手法;而加注(annotation)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進一步闡釋來增加背景信息,從而使文化負載項在兼具民族或異域特色的同時,又為目標語受眾所接受。本文中的直譯,包括了部分學者研究中獨立出來的“音譯”法,故不另文討論。
(原文)紅色旅游、綠色山水旅游、歷史文化旅游三大板塊構筑了該市旅游產品的大框架,特別是紅色旅游在全國首屈一指。(引自《湘潭市情》)
原文中的“紅色旅游”,如果不加注,僅直譯為“Red Tourism”,對于前來文化旅游體驗的境外或國外游客,以及外宣至目標語國家或民族所在的受眾讀者,難免引起歧義或誤解,可能的誤解如“tourism in red”,即“穿紅色衣服進行旅游”,原因在于顏色詞本為多義詞,不同語境下會產生不同的引申義或隱喻義。事實上,“紅色文化”“紅色旅游”作為概念詞,在我國已有規約性的闡釋,而支撐這種規約的恰是其背景性的中國獨有的“紅色革命史”。以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的所有相關紀念館、紀念地、紀念物等為依托,吸引游客前來體驗紅色文化,領會接受紅色革命精神。換言之,紅色旅游文化體驗是一場紅色文化教育。所以,根據吳文艷的翻譯實踐報告[4],可加注翻譯(中—英)如下:
Red Tourism, focusing on learning about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spirit, depends on special tourist resources from commemorative revolutionary sites and memorials found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fter 1921.
除此以外,文化負載項通用翻譯策略還有“意譯”,又名“自由譯”(free translation),即注重源語與目標語的內容對等,在形式上多有損耗,故一般不再額外加注,本文也不展開討論。
(二)貴州地方特色的文化負載項翻譯——以興義市為例
(原文)…… 目前,興義威舍紅軍戰斗遺址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文本已上報省文物局。興義威舍紅軍戰斗遺址有望成為繼劉氏莊園、茶馬古道貴州段馬嶺古道后的我市第三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引自貴州省興義市人民政府官網[5])
“茶馬古道”直譯為“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的同時,還需加注闡釋具有區域特色的文化背景。茶馬古道是我國歷史上內地農業地區和邊疆游牧業地區進行“茶馬貿易”(又稱“茶馬互市”,即以茶換馬,或反向交易,屬于物物交換)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線,存在于中國西南地區,是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
(原文)……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時任知縣陶金詒再次倡議建橋。這一次,鑒于多次修建石橋均毀于洪水之經驗教訓,陶金詒組織人員細細勘查,最終選定原橋舊址下游百余米處重建石橋。這座橋梁,就是如今的馬別橋。(引自黔西南日報社數字報刊平臺[6])
“馬別橋”一詞在外宣中是直接完全音譯,即“Mabie Qiao”,還是音譯“馬別”,“橋”直譯,形成“Mabie Bridge”表達式,然后再加注;或者第三種可能的翻譯,即結合興義歷史文化背景,“馬別”也進行意譯,值得外宣翻譯工作者精心思考。根據《興義府志·地理志》“屯寨”篇,分別列有“馬別大寨”和“馬別橋寨”,因此可以確定“馬別”首先為興義地理志史上的地名,再加上此橋在中國清史中的兵家必爭之背景,筆者以為,上述三種翻譯策略中的第二種為佳,即“Mabie Bridge”再加注的表達形式。
上述兩例示當然無法也不能以偏概全,其他貴州地方民俗旅游文化也可按一定范疇分類的方法,逐類探討民俗文化的共有外宣策略,或者不同類別間有相對不同的手法,如飲食民俗類、建筑民居類、服飾民俗類、節慶民俗類和游藝民俗類等。學界目前普遍通用的手法“直譯+加注”,爭議較小,可供貴州地方民俗(旅游)文化外宣研究者、實踐者、規劃者等多行業、多部門人士參考。
四、結語
本文先對地方民俗旅游文化與文化外宣進行了學理厘清,然后在概述貴州省民俗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通過文獻計量法分析得出當前學界對于貴州民俗文化外宣研究數量不多,質量不高,從而引出主要探討所在,即地方民俗文化外宣中的翻譯策略。主要研究結論是文化負載項的通用翻譯手法適用于地方民俗文化外宣。另外,后續研究中還可加深或推進地方民俗文化外宣中的翻譯途徑探究,如多模態翻譯。
參考文獻:
[1]新華社.貴州打造中國紅色旅游重要目的地[EB/OL].[2018—03—03]. http://www.sohu.com/a/224772603_ 267106.
[2]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3]包惠南,包昂.中國文化與漢英翻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4]吳文艷.外宣翻譯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原則與方法[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4(11).
[5]貴州興義市人民政府.紅色歷史,不忘初心—興義市文體廣電旅游局對紅色文化保護與宣傳[EB/OL].[2019—02—21]. http://www.gzxy.gov.cn/html/ xygov/201902/21/43788572.html.
[6]黔西南日報社數字報刊平臺.一座橋,一段歷史,述說古今[EB/ OL].[2016—07—31].http://www. qxnrb.com/html/2016—07/31/ content_185949.htm.
基金項目:本文系興義民族師范學院博士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8XY BS10);黔西南州科技局科技計劃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貴州非通用語種發展策略研究”。
作者簡介:黃丙剛(1972—),男,山東臨沂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韓漢語言文化對比與翻譯、外語教育;楊勇(1978—),男,山東諸城人,馬來亞大學博士生,講師,研究方向為系統功能與認知語言學、外語翻譯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