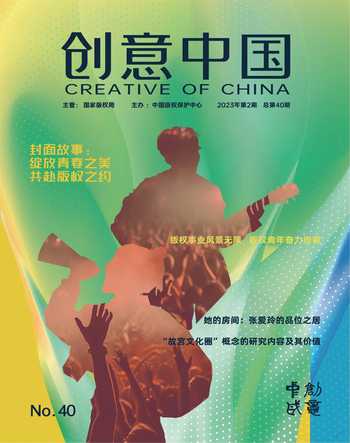當數字藏品遇上著作權:“熱”潮下的“冷”思考
洪詩濤

近年來,數字藏品與元宇宙掀起了一股熱潮。不久前,業界所稱的我國數字藏品第一案也入選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22年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我們知道,數字藏品,也就是非同質化權益憑證,它與特定的底層商品具有唯一的映射關系。那么,當數字藏品映射的底層商品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進而催化出數字藏品交易時,數字藏品就與著作權發生了相遇。數字藏品與著作權的相遇,無疑是一個新現象。這一新現象的背后,是否帶來了新問題呢?熱潮之下,需要進行冷靜的思考。
一、倒去“新瓶”中的“舊酒”:什么是數字藏品交易帶來的新問題
數字藏品交易通常具備鑄造-售前預覽-首次銷售-轉售的環節。茌著作權法視野下,鑄造環節的作品上傳構成復制,提供作品售前預覽構成信息網絡傳播,這些作品利用行為在傳統網紹環境下就已經出現,其著作權法定性也早已形成共識甚至成為常識。
可能存在疑問的是,出售數字藏品的行為,在著作權法上如何進行評價?根據傳統觀點,作品的網絡銷售似乎屬于信息網絡傳播。但不少意見則認為,數字藏品的技術架構決定了出售數字藏品應構成發行,進而,基于發行權用盡原則,轉售行為不受著作權控制。就此而言,當數字藏品與著作權相遇,可能催生出的新問題是:基于數字藏品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在解釋論上甚至立法論上將發行權延及網絡環境嗎?
二、“得不償失”:發行權解釋路徑之否棄
這個問題事關權利重塑和制度變革,必須認真考量相應的成本和效益。
(一)將發行權延及網絡環境的“成本-效益”考量
從國際社會看,選擇發行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二分模式的國家,都將發行權意義上的提供作品復制件限定為提供作品有形載體。這也是我國學界的傳統通說和司法實踐長期以來的做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意識到,對發行權作出背離傳統的解釋,必然要背負不可忽視的成本,包括混淆發行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界限的認識成本、重構發行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界限的制度成本、在實踐中落實重新劃定的權利范圍與權利界限的執行成本。
不過,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發行權存在內在的利益平衡機制,即發行權用盡原則。因此,如果某一商品流通行為因為落入著作權的范圍而遭到著作權人的不當控制,這一商品流通行為又與發行行為在法律要件上存在可類比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發行權的適用及其權利用盡原則的運用可能的確能夠發揮解套的功能,從而在功能主義的意義上帶來效益。
所以,即便在個別的情況下,對于將發行權及其權利用盡原則適用于網絡環境持開放態度,也需要確證,這么做能夠帶來的顯著效益,從而使我們背負相伴而生的制度成本是值當的、臺比例的。
(二)為什么說將出售數字藏品解釋為發行“得不償失”
然而,在出售數字藏品的場景下,比較成本與效益,我們會發現:適用發行權是得不償失的。
首先,將出售數字藏品解釋為“發行”需要背負什么成本呢?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制度成本外,還有一項容易被忽視但卻不可小視的成本。一般認為,發行權用盡原則的適用基礎在于著作權和所有權發生沖突。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如果認定出售數字藏品構成發行,可能使外界誤認為,法律承認買家對數字藏品享有所有權。而數字藏品的法律屬性是需要由民法進行統率回應的問題,著作權法不宜僭越。
那么,發行權解釋路徑是否存在效益呢?支持者的觀點,多數都是出于這樣的邏輯:他們認為,如果不適用發行權,出售數字藏品將歸于信息網絡傳播,轉售就將受到著作權的控制,為此,有必要保障買家對該財產的處分權,排除著作權人的不當控制,適用發行權可以解決這一點。
然而,出售數字藏品事實上并不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本身就不受著作權控制,所以,將出售數字藏品解釋成發行并不存在顯著的效益,因而是得不償失的。
三、為什么出售數字藏品不構成信息網絡傳播——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誤解澄清
那么,為什么出售數字藏品不構成信息網絡傳播?
(一)“使公眾可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或地點獲得作品”行為的規范評價屬性
我國著作權法中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直接來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第8條,這是有共識的。溯源循理,就應當明確,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的是“使公眾可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或地點獲得作品”的行為。但是,也不能認為:所有在事實層面對于公眾交互式獲得作品有促進作用的行為都構成信息網絡傳播。將其中哪些行為歸為直接侵權,不能僅停留在事實認定的層面,而應上升到規范評價的范疇,這不僅需要立足侵權法原理,也可能涉及特定的政策考量。就侵權法原理而言,因果關系的強弱和行為意志有無是區分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依據。具體到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對交互式傳播作用力的顯著與否、是否具有傳播作品的行為意志,構成了對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做出規范界定的實質標準。
(二)出售數字藏品構成信息網絡傳播之否證
回到出售數字藏品的定性上,我們不能認為,如果前手不出售,后手就無法獲得作品,因而前手的出售構成信息網絡傳播。事實上,后手買家之所以能夠獲得作品,是因為鑄造者發布的智能臺約所設定的規則是:每一次交易完成后,買家都可以基于其權益所有者身份,通過鏈上跳轉機制獲得作品——這構筑了一項作品傳播機制。而轉售只是使得后手買家成為新的權益所有者,對于交互式傳播的實現在作用力上居于輔助和次要地位。同時,轉售行為主要是為了讓渡權益憑證,很難說這一行為包含了傳播作品的意志。所以,應當認為其不構成信息網絡傳播。
四、新時代版權青年應懷有更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面對新挑戰,版權青年固然應當敢于批判,捕捉新生問題,但也有必要明辨是非。技術有變,法理有常。至少就目前而言,數字藏品帶來的新問題是有限的,數字藏品也并未對版權制度的運行和版權法原理的運用帶來顛覆性的挑戰。所以對于當前的版權制度,新時代版權青年應當懷有更多的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