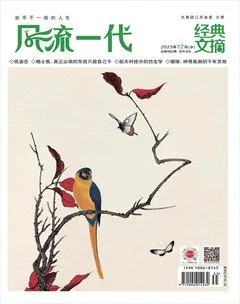在彈雨中舉起相機(jī):戰(zhàn)地記者究竟多危險(xiǎn)
許翔云
近日,巴以沖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親臨前線的戰(zhàn)地記者們把戰(zhàn)爭的場面?zhèn)鬟f給千家萬戶,他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jià)。至截稿時(shí),至少已有15名戰(zhàn)地記者在這場沖突中喪生。
對戰(zhàn)地記者而言,危險(xiǎn)本就是如影隨形,越靠近前線,拍到震撼人心的場景的可能性便越大,也越能寫出接近戰(zhàn)爭真實(shí)的報(bào)道。
狂轟濫炸下的戰(zhàn)地記者
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二戰(zhàn)正式爆發(fā)。然而,在此之前,零星戰(zhàn)火已在全球多地燃燒,一批戰(zhàn)地記者早已奔赴戰(zhàn)場,用他們的打字機(jī)與照相機(jī)記錄著時(shí)代的脈搏,并試圖從中管窺未來的走向。
1937年4月,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中,支持佛朗哥政權(quán)的德國空軍對格爾尼卡的平民展開狂轟濫炸,這一暴行拉開了現(xiàn)代戰(zhàn)爭針對非軍事目標(biāo)進(jìn)行大規(guī)模空襲的序幕,畢加索憤而創(chuàng)作了油畫《格爾尼卡》作為控訴。而在大半個(g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一位戰(zhàn)地記者也真實(shí)捕捉到了侵華日軍對上海大規(guī)模空襲所造成的慘象。
對赫斯特新聞社的王小亭而言,這已是他親歷的第三場戰(zhàn)爭了。他于1900年生在北京,似乎注定要與戰(zhàn)爭打一輩子交道。自20年代踏入新聞攝影這一行后,他拍攝過北伐戰(zhàn)爭的場景,也曾在九一八事變后赴東北的白山黑水報(bào)道抗戰(zhàn)進(jìn)程,可真正讓他被世界知道的,是1937年8月28日下午抓拍的一段新聞膠片。
那天午后,多國記者聚集在太古大廈樓頂,準(zhǔn)備拍攝轟炸場面,他們事先收到消息,日本海軍飛機(jī)將于下午2點(diǎn)左右發(fā)動(dòng)空襲。當(dāng)日下午3點(diǎn),日機(jī)遲遲不至,記者相繼散去了,只有王小亭仍在等待。
下午4時(shí)許,王小亭看到日機(jī)現(xiàn)身,在上海南站上空盤旋、投彈。當(dāng)時(shí)站臺(tái)上擠滿了焦急等待開往杭州列車的難民,待王小亭駕車趕到現(xiàn)場時(shí),已是血肉橫飛,“鐵道與站臺(tái)上滿是死傷的人群,斷肢到處都是……當(dāng)我停下來重裝膠卷時(shí),注意到我的鞋子已為鮮血所浸透。”
就在此時(shí),王小亭注意到一個(gè)人從軌道上小心翼翼地抱起一位孩子,將他放到站臺(tái)上,然后轉(zhuǎn)身去照料另一位受傷的孩子。此時(shí)彈如雨下,離開了大人的孩子在站臺(tái)上無助地哭泣,面前滿目瘡痍,四周皆是斷壁殘?jiān)M跣⊥づe起攝像機(jī),將剩余的膠卷都用在了孩子身上。
王小亭的膠卷先是搭乘美國海軍艦只來到馬尼拉,之后抵達(dá)紐約,9月中旬起,在美國各大影院電影開場前播放。美國人開始意識(shí)到日本侵華的切實(shí)存在,并喚起他們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
可惜的是,言語支持是一方面,采取行動(dòng)是另一方面。10月5日,羅斯福總統(tǒng)就中國局勢發(fā)表演說,呼吁國際社會(huì)行動(dòng)起來阻止侵略時(shí),響應(yīng)者寥寥。
隨著二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美國人驚恐地發(fā)現(xiàn),上海遭受的苦難,又降臨到了華沙、鹿特丹、倫敦等城市。1940年夏天起,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收聽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德華·默羅帶來的現(xiàn)場廣播,從中了解英國抗戰(zhàn)的進(jìn)程。
早在30年代中期,當(dāng)美國社會(huì)總體上對歐亞大陸的風(fēng)云變幻持漠不關(guān)心的態(tài)度時(shí),默羅已經(jīng)開始注意到令人不安的苗頭。他曾積極為納粹上臺(tái)后失去教職的知名德國學(xué)者們奔走呼告,爭取援助,也一手創(chuàng)建了被外界戲稱為“默羅家男孩們”的駐歐報(bào)道團(tuán)隊(duì)。
在1938年3月收到駐維也納記者威廉·夏伊勒的口信后,默羅從倫敦借道華沙,飛赴維也納,向聽眾現(xiàn)場直播德奧合并的進(jìn)度:“我是愛德華·默羅,在維也納進(jìn)行廣播……現(xiàn)在是早上2點(diǎn)30分,希特勒尚未抵達(dá)維也納……”下了節(jié)目后,默羅到一家酒吧消遣,親眼目睹一位猶太人“站了一會(huì)兒,然后從口袋中掏出一把老式刮胡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嚨”。
兩年半后,默羅再度見證了戰(zhàn)爭的慘烈。自1940年9月7日起,德國空軍開始空襲倫敦,企圖摧毀英國人的抵抗意志。每天晚上,默羅都爬上屋頂,聆聽警報(bào)的長鳴聲、飛機(jī)的轟鳴聲、高射炮火的怒吼與炸彈的作響,觀察著被白色探照燈與橘色火光點(diǎn)亮的夜空,嗅著騰起的火藥味與焦土味,說出以下三個(gè)詞“這里是倫敦”(This is London),接著稍加停頓,以吸引聽眾的注意力,然后再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見聞,最后以英國人常說的“晚安,好運(yùn)”(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作為結(jié)語。
把握戰(zhàn)爭脈搏的戰(zhàn)地記者
在美國聽眾心中,默羅沉靜的語調(diào)宛如英國的化身,象征著這個(gè)國家即便遭受深重苦難,在納粹德國猛攻面前仍屹立不倒。因此在默羅于1941年回國時(shí),受到了盛大的歡迎,羅斯福總統(tǒng)親自發(fā)電報(bào)祝賀,國會(huì)圖書館館長的致辭也反映出默羅廣播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你將倫敦燃燒的場景在我們的家中重現(xiàn),我們感受到了赤焰。你將倫敦的死傷情況放到我們家門口,我們明白,那些死者是我們的死者,是人類的死者。”
與默羅一樣,厄尼·派爾也對他所見的英國社會(huì)欣賞有加。1940年12月抵達(dá)倫敦的他原以為自己目力所及,將只看到一片瓦礫。因此,當(dāng)他看到威斯敏斯特橋、滑鐵盧橋等泰晤士河上的橋梁仍舊佇立,車輛往來其間暢行無阻時(shí),大感震驚。
在發(fā)給國內(nèi)的報(bào)道中,他講述了英國朋友歡迎自己時(shí)使用的幽默句子,以此證明他們在面對德國空襲時(shí)的勇氣:“你能來真是太好了,我們彼此間已經(jīng)講了各自的空襲故事太多遍了,大家都不愛聽了。現(xiàn)在我們有了位新聽眾了。”他也向美國讀者描述了圣保羅教堂“為烈焰所包圍,卻安然無恙”,以及倫敦人“從經(jīng)驗(yàn)中發(fā)展出了一套應(yīng)對空襲的絕佳效率”的場景。
派爾于1941年3月回國,過了兩個(gè)月,羅伯特·卡帕與福布斯·羅伯遜來到英國,他們受蘭登公司委托,準(zhǔn)備創(chuàng)作一本關(guān)于英國如何應(yīng)對納粹德國空襲的書,由羅伯遜主筆,卡帕負(fù)責(zé)配圖。這并非卡帕首次將相機(jī)鏡頭對準(zhǔn)戰(zhàn)爭中的后方社會(huì)。1936年,卡帕赴西班牙報(bào)道佛朗哥政權(quán)與共和國間的內(nèi)戰(zhàn)。兩年后,他又奔赴中國武漢。他所拍攝的西班牙與中國軍民堅(jiān)毅抗戰(zhàn)的神情成了這兩個(gè)民族不屈不撓的象征。
行走在倫敦的街頭巷陌,卡帕捕捉到英國人在空襲下正常生活的狀態(tài)。他最喜歡逗留的是倫敦東區(qū)的滑鐵盧路,跟拍普通的英國家庭如何洗菜、做飯、喝下午茶、舉行宗教儀式,展現(xiàn)出他們從容不迫的樣子。此外,這個(gè)地名不禁讓人想起一百多年前那場決定歐洲命運(yùn)的戰(zhàn)役。因此卡帕和羅伯遜把他們的著作命名為《滑鐵盧路戰(zhàn)役》,突出英國社會(huì)的心態(tài)將最終決定戰(zhàn)爭的結(jié)果。
九死一生的戰(zhàn)地記者
卡帕何嘗不明白,只有和士兵們在前線共同經(jīng)歷炮火的生死考驗(yàn),才能贏得他們的信賴與尊重,拍出揭示戰(zhàn)爭本質(zhì)的照片。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時(shí),他用自己的出生入死換來了一張張珍貴的照片,而他摯愛的女友也死在那里。
因此在終于獲得報(bào)道前線戰(zhàn)事的許可后,1943年春,卡帕登上運(yùn)兵船,前往北非,開啟了新一段波瀾壯闊的旅程。卡帕的內(nèi)心充滿了建功立業(yè)的渴望,到達(dá)北非后的第一個(gè)晚上,他夢見“就在突尼斯的城門口,我追上了裝甲師,跳上了領(lǐng)頭的那輛坦克……我成了拍攝到抓獲隆美爾鏡頭的唯一攝影師……在市中心,一顆炮彈爆炸了……我的臉被燒焦了”。
正如這個(gè)夢所反映的那樣,榮耀與冒險(xiǎn)貫穿卡帕整個(gè)二戰(zhàn)生涯。做完這個(gè)夢的第二天,他在小解時(shí)誤入德軍埋設(shè)的地雷陣,嚇得一步也不敢動(dòng),褲子也不敢提,讓司機(jī)請工兵帶著探雷器來解圍。之后,在1942年11月便伴隨美軍登陸北非的派爾開著吉普車找上了他,讓他拍了不少兩軍在埃爾瓜塔爾山脊上戰(zhàn)斗的畫面。
可卡帕還是不大滿意,稱“沒有一張反映戰(zhàn)斗的緊張程度和戲劇性,那是我用肉眼所能感覺到、追蹤得到的”。當(dāng)他在英國拍攝過的轟炸機(jī)部隊(duì)轉(zhuǎn)場到北非、邀請他一起飛行時(shí),從未學(xué)習(xí)過如何跳傘的卡帕欣然應(yīng)允,和他們飛了五次任務(wù)。
參加轟炸行動(dòng)的經(jīng)歷一點(diǎn)兒不影響卡帕繼續(xù)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他接下了另一個(gè)拍攝任務(wù):跟拍跳傘進(jìn)攻西西里島的第八十二空降師,并隨機(jī)返航,成為第一個(gè)向外界發(fā)布盟軍進(jìn)攻西西里照片的攝影師。
諾曼底登陸期間,卡帕認(rèn)識(shí)的一位軍官邀請他跟隨團(tuán)部行動(dòng),他們將在第二波攻擊行動(dòng)中上岸,這樣卡帕既能拍攝到一手戰(zhàn)況,又不至于暴露在過大的風(fēng)險(xiǎn)中,可卡帕最終選擇跟隨第一波沖灘部隊(duì)上岸,“每一次子彈都直追我的脊背”。卡帕拍攝的奧馬哈灘頭的場景成為外界感受這場慘烈登陸的一手資料,甚至導(dǎo)演斯皮爾伯格拍攝《拯救大兵瑞恩》時(shí)仍在借鑒。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前夕的萊比錫,卡帕上一秒還在拍攝一位正在開槍射擊的士兵,下一秒這位士兵便倒在了血泊中。
戰(zhàn)爭就是如此殘酷,活下來全靠運(yùn)氣,無論如何,嚴(yán)守職業(yè)信條、冒著生命風(fēng)險(xiǎn)報(bào)道戰(zhàn)爭的戰(zhàn)地記者,都應(yīng)得到交戰(zhàn)雙方乃至全世界的尊重與保護(hù)。他們?yōu)槲覀兗昂笕肆粝铝藢氋F的歷史資料,傳遞著來自戰(zhàn)場的聲音。
(燦爛摘自“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hào))
- 風(fēng)流一代·經(jīng)典文摘的其它文章
- @經(jīng)典文摘雜志
- 幽默
- 漫畫
- 蚯蚓測試
- 員工關(guān)系課
- 為啥是“高醋矮醬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