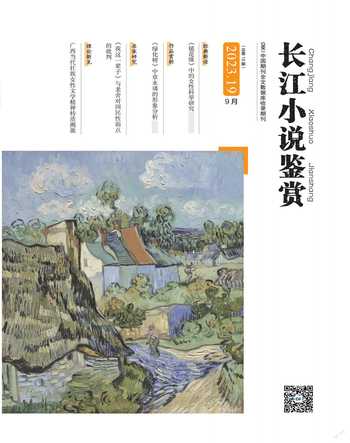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精神特質溯源
[摘? 要] 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多民族共同發展的特點,少數民族作家從自身的成長環境、經歷出發構筑了本民族的文學藝術。廣西當代壯族文學近幾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壯族女性作家也在文藝創作上嶄露頭角,她們的創作深深根植于民族歷史記憶,以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獨特的女性視角展現了深層次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本文從廣西當代壯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出發,以民族記憶與女性主體兩個維度探究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的精神特質。
[關鍵詞] 壯族女性文學? 精神特質? 民族記憶? 女性主體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9-0088-04
一、引言
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中國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壯族女性在深厚的文化遺產和豐富多彩的民族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是在中國文化的浸潤中逐步孕育和發展起來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壯族女性在文藝創作上嶄露頭角,她們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深入人心的敘事角度。在社會轉型和文化多樣性的背景下,廣西壯族女性文學深深根植于民族歷史記憶,展現了壯族女性的主體性意識。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的發展,體現了社會進步對女性作家的影響,同時揭示了壯族女性作家在把握自身角色轉變、表達個人自我、探尋民族文化內涵等方面作出的獨特貢獻。本文從民族記憶和女性主體兩個維度探究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的精神特質,揭示其深層次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
二、民族記憶與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
民族記憶可被理解為一個民族對其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思考、評價以及期望。這一文化現象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傳承、傳統價值觀念以及集體認同,通過多種文化表達方式,如語言、文字、視覺藝術、音樂和儀式等,來傳承和演繹。然而,民族記憶并非靜態不變,而是伴隨著時代演變和社會發展而不斷重塑和調整的。
民族記憶擔負著多重功能,對一個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凝聚力以及創新能力產生深遠影響。首先,民族記憶有助于塑造和深化民族認同感,使個體和群體更強烈地感受到自身與整個民族的聯系。其次,通過回顧歷史事件,民族記憶能夠傳遞重要的歷史教訓,引導群體在未來的道路上避免重蹈覆轍。最后,民族記憶在傳承文化傳統的同時,推動社會凝聚力的形成。
深入探討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與民族記憶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且相互啟發的聯系,彰顯了民族記憶在文學創作中不可替代的價值。
女性主體性在廣西壯族女性文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代表女性作為自主主體存在的力量,抵抗著男權社會的規范和壓迫。這一概念呼應了廣西壯族文學中的民族記憶,因為它強調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積極追求自身生活方式、學習知識技能、提高社會地位和塑造優秀人格的過程。這種女性主體性也與廣西壯族文學的核心精神相契合,同時反對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精神和文化的剝奪和異化,體現了廣西壯族女性在文學創作中更為深刻的價值與意義。
三、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中的民族記憶
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載體,不僅傳承了民族的歷史記憶,還將其注入文學創作之中,在呈現民族記憶方面具有豐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通過作品,作家們傳遞著壯族歷史、習俗和文化;通過作品,作家將民族記憶與個體經歷相融合,展示出多維度的文化魅力;通過作品,作家們傳承和重構民族記憶,體現文學中的女性主體性,以及與民族記憶交織的民族精神。
1.自然景觀與壯鄉村寨
“任何作家的成長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任何作品的創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發生的。”[1]作家的文學作品總是依附于特定的地域環境和文化背景,這其中既包含地域山川和寺觀村鎮,還包含世俗風情形態。在當代廣西壯族女作家的筆下,對廣西山水自然景觀的描述極具鮮明的地域特色,她們作品中的男女老少無一例外都在廣西這個西南邊陲的丘陵山地之間譜寫各樣傳奇。盆地、丘陵、右江、左江、紅水河、柳江、中越邊境、邊陲小鎮、深山壯寨等,這些鮮明代表廣西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觀在當代壯族女性作家文學作品中是常見元素。
作家岑獻青出生于崇左龍州中越邊境,她的散文中就常出現桂西南邊境地區的友誼關、花山等大景觀,桂西南左江流域的“鑿齒”“銀耳環”“白頭翁”和 “艾草”等山石草木,“歌圩”“年粽”“米粉”等風俗特產;梁志玲在小說中描述的那個虛構小鎮“莫那”有隨處可見的大葉榕、三角梅、甘蔗田、芒果林、沙田柚、米粉等百越之地的特產風物。這些物象大多是壯族千百年歷史沉淀下來的,體現出作者的鄉土情懷及對本民族民俗文化的認同心理。陶麗群小說里對壯鄉村寨的農夫農婦、牛馬販子等服飾的細致描繪,也是對壯族風情的精彩再現。如小說《尋暖》對李尋暖的描寫,她的長發、小巧的身材、藍色的褲衣、衣服上精細的花邊、明晃晃的項圈,都反映了壯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特點。藍色的褲衣顯示壯族人喜歡的顏色,藍色通常由手工研磨的靛藍染制成,顯示了壯族人在紡織和染色藝術上的獨特技藝和審美觀。褲腳、衣領、對襟、衣袖口上都繡上精致的花邊,這突出了壯族刺繡的獨特技藝,反映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和審美觀。胸前掛著的明亮的項圈體現了壯族的裝飾品和對美的追求,這也揭示了壯族在裝飾藝術上的獨特風格。
2.民間歌謠與壯鄉風俗
許多壯族女作家通過描寫壯族的傳統節慶活動、婚禮儀式、山歌民謠等元素,將民族傳統和文化記憶融入到故事之中,展現濃厚的壯族風情,為讀者勾勒出一個真實而豐富的民族記憶圖景。
老一輩壯族作家岑獻青的小說中有許多對廣西壯族婚俗的豐富描繪。在岑獻青的筆下,壯族婚嫁風俗與民間歌謠融入故事情節中。在《裂紋》中,正清老漢的女兒阿順出嫁,小說描述了阿順哭嫁的兩段山歌。哭嫁歌的字里行間充滿了壯族文化的豐富魅力,例如,“爺呵娘,娘做房門女做鎖呀,女兒貼在娘身上。爺呵娘,誰知鑰匙掉下地呀,鑰匙掉地被人撿走”[2],歌詞用簡單而深刻的語言道出了女性在婚禮上離家時的憂慮和不舍,以及對家庭和親情的深深眷戀。這種對情感的鮮活描繪,從一個新的角度呈現了壯族女性的內心世界,增加了文化的層次和深度。小說《告別》也生動地刻畫了壯族婚禮風俗中接嫁和哭嫁的環節。小說中的阿秀準備嫁進縣城,本來充滿歡欣與期待,但按照壯族的傳統婚嫁風俗,新郎接親時新娘要哭嫁。對接親與哭嫁場景的描寫生動質樸,極具細節感染力,生動地捕捉了婚禮的氛圍和女性在其中的情感體驗,充分表現了廣西當代壯族女性作家在通過文學創作傳承和重構民族記憶,展現民族文化的魅力和多樣性方面的獨特手法和深刻見解。
陶麗群的創作中常有對壯族喪葬活動的生動描繪。其中,《一塘荷香》通過對廣西右江地區壯族喪葬習俗的展示,向讀者傳遞了壯族地區文化的深刻內涵,包括其獨特的語言形式、行為思想、社群傳統和信仰等。這些微觀的細節呈現出壯族地區的文化特色,生動地反映了壯族文化中的喪葬習俗和祖先崇拜信仰[3]。
對壯族婚葬嫁娶的鮮活描繪不僅展示了個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的情感經歷,也反映了壯族文化對家庭、婚姻和親情的重視和關注,豐富了小說的情感深度。作家們巧妙地傳承并重構了民族記憶,賦予傳統文化以新的意義和生命力,讓讀者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賞壯族的文化和歷史。
3.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中的民族精神
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家通過文學作品反映民族情感的復雜性和深刻性,表達深刻的民族精神,以及對民族歷史的變遷和發展的思考。
3.1在鄉土文化中尋求精神寄托
陶麗群的許多作品都體現了她深厚的鄉土情結。與許多文人透過追溯來尋找鄉土的方式不同,陶麗群的心靈在鄉土文化中從未離去。這是她作品中強烈民族精神的源泉,也是她能夠精準描繪出壯族民間生活與農村生活情境的原因。《漫山遍野的秋天》和《一塘香荷》中,陶麗群繼續將她的文化思考寄托于土地上[4]。無論是不孕的黃天發因為突如其來的孩子而解開心結,還是李一鋤對土地的執著、廖秉德在離家后的堅決回歸,都體現了他們對家鄉和土地的深深眷戀,反映出壯族人民永遠熱愛和忠誠于家鄉和土地。
3.2堅韌與勇敢等民族品質的描繪
岑獻青的《蝗祭》中,吟香的故事飽含了對堅韌與勇敢等品質的塑造。她不僅成為允豐寨里唯一接受高中教育的人,還敢于站出來挑戰黑云洞里從未露過面卻被允豐寨人奉為神靈的神秘權威,而且還敢于在爺爺去世后,獨自翻山越嶺去尋找全新的生活。她敢于放棄已知的安逸和舒適,只為了追求她想要的生活,這種堅韌和勇氣是對壯族人民精神特性的生動描繪。吟香的故事從某種程度上映射了壯族民族命運的變遷。她的決定和行動揭示了當今壯族青年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挑戰和對新生活的追求。吟香的勇氣與智慧以及改變命運的決心,在尋找新的生活道路上,不僅為她自己指明方向,同時也預示著壯族人民未來的可能和希望。
四、女性主體與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
女性主體是一種身份的認同,指的是女性作為獨立的“主體”存在,能獨立思考,擁有自我意愿和決策的能力。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強調女性主體性的自主性和多元性,而中國女性主義研究則關注女性在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轉變和價值觀重建,涉及女性在社會、文化和個體層面的地位和表達。在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中,女性主體不僅是作品的創作對象,更是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表達和思想傳遞的核心,表現出多元性和自主性。多元性體現在女性形象的豐富多樣,涵蓋了不同年齡、職業、家庭角色的女性,呈現出一個多面的女性世界。自主性體現在女性主體對自己生活的選擇和命運的把握。作品中的女性追求自己的夢想,參與社會發展,通過努力和嘗試,不斷突破傳統束縛,實現自我價值。
廣西壯族女性作家在描繪壯族女性角色時,常帶著濃厚的同情心。她們通過對歷史環境、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源泉的全面理解,生動描述壯族女性的生活場景、心理特質和命運走向。黃夏斯榕的《玉佩褲帶》以三代女性的命運為線索,揭示了女性解放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外婆是傳統中國女性的典型代表,身處男權文化之下,被其父親作為賭注,“輸”給了“我”的外公,婚后因生女受虐。甚至,外婆的婆婆重男輕女,竟然想要殺害女嬰。相比外婆,母親作為覺醒的女性,深知只有教育才能改變命運。在母親的影響下,“我”逐步成長為女性疾病研究專家。小說中每一代人的命運揭示了社會和女性的轉化:從無意識的順從者,到有意識的斗爭者,再到女權的積極倡導者。母親通過上學,開啟了她的革新道路,最終深知“女人需自我救贖”。而“我”秉持母親的這種開拓精神,從中專生逐漸升級為研究生,成功展示了一個女性有能力救贖自我,甚至救贖更多的女性。
陶麗群的《母親的島》和《尋暖》也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追認與救贖。母親與李尋暖同為被拐來的媳婦,母親雖終其一生養兒育女,侍奉公婆,但心里對被作為“物品”交易而來的命運耿耿于懷,終于靜默聚集力量,尋找到離開孤島的機會。母親的逃離之路,實則是一場女性力量突破了傳統束縛,實現自我和個人救贖的旅程。而李尋暖的反抗則更為激烈,她對花重金購買她且愛惜她的陸卒子毫不動心,對于自己被當作“商品”和“工具”心存芥蒂,她寧可和其他男人發生關系走上覆滅的道路,也不愿意與陸卒子相安無事地過日子[5]。
總的來說,小說中的每一代人都在挑戰和改變“女性依賴男性,為男性而活”的傳統觀念。作家特別揭示了封建宗法權力、落后的婚姻觀念以及商品異化對壯族女性身心健康的損傷和對個人尊嚴的褻瀆,她們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
五、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精神特質溯源
民族記憶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和經驗的集合,通過代際傳承和文化表達,形成獨特的民族認同和文化傳統。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通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情感,展現壯族人民的歷史變遷、文化傳承和民族特質。這些創作不僅弘揚了壯族人民的優秀傳統,也喚起人們對民族歷史的回顧和思考。此外,在塑造和表達女性主體方面,她們強調女性的自我意識、價值追求和情感體驗。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被動接受角色安排,而是通過自主行動和情感抒發,展現女性的多樣性和多維性。通過女性主體維度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刻理解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性別平等、女性權利和女性自我認知等主題。
首先,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品在傳承和重構民族記憶方面展現了強烈的意識。通過作品中的歷史背景、文化符號和人物情感,作家們成功地將民族記憶融入創作,使作品更具代表性和傳承性,不僅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內涵,還加強了壯族人民對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的認知。
其次,作家們在塑造女性主體形象時注重多樣性和自主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受限于傳統的角色定位,而是通過情感、行動和成長,展現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價值追求。這種創作使作品更具現實意義,呼應了當代社會對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的關切。
此外,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作品在情感抒發和社會關懷方面表現出色。作家們通過情感的傳遞,使作品更具感染力。作品反映的女性在家庭、事業和社會中的抉擇和堅持,引起讀者對女性命運和價值的深刻思考。
參考文獻
[1] 覃莉.關于“文學發生的地理基因”的思考[J].世界文學評論,2011(1).
[2] 岑獻青.裂紋[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
[3] 楊一.鄉愁、土地與女性——壯族作家陶麗群小說作品評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7).
[4] 魏霞.文學地理學視域下新時期以來壯族女性作家小說研究[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2020.
[5] 張柱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空間的開啟——以壯族女作家陶麗群的小說為例[J].賀州學院學報,2019(12).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李榮玲,碩士研究生,廣西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基金項目:2023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課題“廣西當代壯族女性文學精神特質研究”(項目編號:2023KY1820),項目主持人李榮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