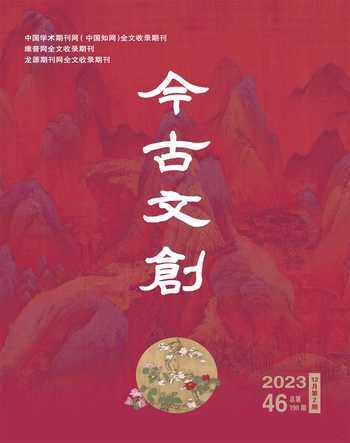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今昔物語集》中“蛇” 與“女性” 的關(guān)聯(lián)研究
江維
【摘要】平安時期的《今昔物語集》在日本說話文學(xué)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收錄了多篇動物故事。本文從動物“蛇”與“女性”關(guān)系這一角度,揭示該作品中“蛇”與“女性”二者結(jié)合后產(chǎn)生的新角色,主要有女子化蛇、蛇女(龍王之女)以及蛇難的受害者這三種角色。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前代蛇女形象的影響、推廣傳播佛教以及宣揚(yáng)其因果報應(yīng)思想的需要。
【關(guān)鍵詞】《今昔物語集》;蛇;女性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6-002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08
《今昔物語集》成書于平安時期,是日本現(xiàn)存最大的佛教說話集。該書內(nèi)容不僅局限于上至天皇、皇帝,下至普通平民百姓的人類世界,還包含了一些超自然存在,以及虎、牛、蛇等動物世界。目前關(guān)于該作品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形象分析、句義語法分析以及影響研究等。其中關(guān)于《今昔物語集》中的蛇形象研究多集中在其蛇女形象分析,但是對“蛇”和“女性”這兩者的關(guān)聯(lián)研究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今昔物語集》,并從其中的“蛇”與“女性”出發(fā),從作品抽出“蛇”與“女性”相關(guān)的故事,去探求這部作品中“蛇”與“女性”的關(guān)聯(lián)。
一、《今昔物語集》中“蛇”與“女性”故事
《今昔物語集》中涉及“蛇”與“女性”的一共有六則,主要分布在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以及卷二十四中。按照故事情節(jié)可分為三類,一是女子化蛇;二是蛇女與龍;三是女子遇蛇難。
(一)女子化蛇
卷十三第四十三則中女子對紅梅情有獨(dú)鐘。但后來女子總是郁郁寡歡,不久就去世了。而后紅梅樹下就出現(xiàn)了一條小蛇。父母猜這蛇應(yīng)該就是他們死去的女兒,便請來兩位圣僧在紅梅樹下說法。小蛇聽后不久就在紅梅樹下死去了。后來父親夢到女兒在高僧帶領(lǐng)下兩人駕云而去。
卷十四第三則中,蛇女清姬原本為人,遭負(fù)心漢安珍背叛之后,被執(zhí)念困擾無法解脫,于是瘋狂追趕安珍,最后化身成蛇把自己和安珍燒死。后來安珍托夢給高僧,請求他虔誠抄寫佛經(jīng)超度他和清姬。最后兩人脫離蛇身分別升天。
卷十四第四則中,女子得到千兩黃金,臨死前囑托人將黃金埋在自己墓穴里。死后化蛇在寺廟里作惡。后在大臣的幫助下,女子脫離蛇身。
這三則故事中女子化蛇體現(xiàn)的是,女子因生前種種執(zhí)念而墮入蛇道。刻畫出蛇與女性的結(jié)合后產(chǎn)生惡毒、作惡等形象。女子因為生前對紅梅執(zhí)念死后墮入蛇道;清姬對愛欲的執(zhí)念,使得她死后化蛇,并開始作惡;卷十四中的女子因為對金錢的執(zhí)念,死后轉(zhuǎn)生為毒蛇。由此大致可以推出,《今昔物語集》中女子生前若對某一事物充滿執(zhí)念,死后便會化蛇。
同時,女子化蛇并非就是此類故事的結(jié)局。一般而言,書中還會給出脫離蛇身的方法。即供養(yǎng)佛經(jīng),通過佛經(jīng)的力量來脫離蛇身,從而實現(xiàn)再生為人。墮入蛇道的女子通過夢示等方法,告訴在世之人并借助他們的力量來供養(yǎng)佛經(jīng),從而達(dá)到脫離蛇道的目的。這類女子化蛇的故事宣揚(yáng)了佛經(jīng)中清心寡欲的思想。生前因為對世間的各種執(zhí)念,錢財、愛欲以及景色的留戀不舍都會是墮入畜生道的業(yè)障,如果墮入了畜生道,也只需要虔誠誦讀、供養(yǎng)佛經(jīng)便可脫離畜生道。通過此類故事達(dá)到了宣揚(yáng)佛教思想的目的。
(二)蛇女與龍
卷十六第十五則講的是一個信奉觀音的貧苦少年救了一條小蛇,而后小蛇化成女子模樣將少年帶回龍宮,蛇女的父親,也就是龍王熱情招待了少年,并賜給少年金餅,少年得到金餅后擺脫了貧困的故事。
這一則故事則是將蛇女與龍結(jié)合起來,體現(xiàn)出蛇與龍的關(guān)系,在這則故事中,蛇在某種意義上就等同于龍,換而言之,蛇是化龍前的形態(tài)。關(guān)于蛇與龍的關(guān)系歷來就被反復(fù)研究。在《今昔物語集》中龍的出現(xiàn)大都伴隨著蛇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的多為龍如果要脫離蛇道便需要虔誠持誦佛經(jīng),依靠佛經(jīng)的力量脫離三熱之苦。這則故事雖不是著重描寫蛇女與龍的關(guān)系,但通過文章中的描寫,可以推出:在這類故事中,蛇女是龍的幼崽,即在化龍前的形態(tài)是蛇女或蛇郎。
同時,通過文本分析也可以知道:此類故事中的蛇女并非單純意義上的動物形態(tài),而是具有幻化為人以及暢通來往龍宮與人間的能力。故事中的蛇女在得到少年的救助后化身為少女來到人間報恩,能夠自然暢通地帶領(lǐng)少年來往于人間與龍宮。此時,對比前文女子化蛇的故事,這類故事中的蛇女形象則是美麗、善良的化身。
(三)女子遇蛇難
卷十六第十六則中,女子從小誦讀觀音經(jīng),一天用死魚換得活螃蟹,并將螃蟹放生。后來其父在田間干活時看到一條蛇在追逐蟾蜍,對前者承諾若將蟾蜍放生便將女兒嫁給它。女兒叮囑父親讓蛇三日后再來,父親照做打發(fā)走了蛇。等到第三天大蛇來的時候,女子便躲在小屋里誦讀觀音經(jīng)。等到天亮出門一看大蛇被許多小螃蟹咬死了。
卷二十四第九則中,女子采桑葉喂蠶時被大蛇纏住后陷入昏迷,而后被大蛇產(chǎn)卵在體內(nèi)。父母請當(dāng)?shù)孛t(yī)為她醫(yī)治,歷經(jīng)千辛萬苦才將女子治好,但不過三年后這女子又被蛇給纏上去世了。
在這兩則故事中,女子是以一個受害者的角色出現(xiàn)。前者在觀音經(jīng)的庇護(hù)下,成功逃脫蛇難。后者體現(xiàn)的是因果報應(yīng),女子最終也沒有逃離蛇難。故事中的女子身上都有善良、勤勞等特質(zhì)。山城國的女子拿死魚換活螃蟹,并將活螃蟹放生,體現(xiàn)了女子的善良以及對生命的尊重。在得知父親將自己許給毒蛇時,也并沒有責(zé)怪父親,而是安慰、開導(dǎo)父親。第二則故事中的女子生前采集桑葉也是其勤勞的表現(xiàn)。在第一次救治后小心謹(jǐn)慎,雖然最終沒有逃脫因果報應(yīng),但是我們也無法抹去該女子身上的勤勞特質(zhì)。
在此類故事中女子遇到蛇難,有的女子借助佛經(jīng)得以逃脫蛇難;有的女子卻因為因果報應(yīng)而丟掉性命。《今昔物語集》中借助此類故事既宣揚(yáng)了佛法;又弘揚(yáng)了佛教的因果報應(yīng)思想。遇到蛇難,只要誦讀佛經(jīng),在佛經(jīng)的保護(hù)下可以規(guī)避掉蛇難。同時,借助此類故事在經(jīng)濟(jì)落后的古代弘揚(yáng)因果報應(yīng)的思想也會更加得到民眾的信服。
二、形象及故事敘述特點
(一)形象特點
化蛇的女子基本都是由于生前執(zhí)念,才墮入蛇道。體現(xiàn)的是女子生前本來是善良的,但化蛇后更多的是在作惡,即“蛇”與“女性”結(jié)合后體現(xiàn)的是“惡”的一面。同時通過對比與前代中的蛇女可以得知,這一時期的蛇女形象也比以往更加豐滿,為其后的蛇女形象奠定了基礎(chǔ)。
《古事記》中肥長比賣的故事也是日本最早的有史料記載的蛇女故事。肥長比賣渴望愛情,蛇女身份暴露之后卻也無能為力,只能在月光下追逐著自己的愛人。江戶時期上田秋成的《蛇性之淫》借鑒了《白娘子永鎮(zhèn)雷峰塔》的故事后,基于日本本國的蛇女形象進(jìn)行的再創(chuàng)作。其故事中能看到作惡等特點。這點與《白娘子永鎮(zhèn)雷峰塔》中善良、溫婉的白蛇形象截然相反,和《今昔物語集》中女子化蛇的形象卻十分吻合。即女子與蛇結(jié)合后產(chǎn)生的蛇女體現(xiàn)的是“惡”的形象。
而“蛇女”與“龍”的故事凸顯的則是蛇女、龍王的善良,以及少年信奉觀音經(jīng),并由此擺脫貧困。強(qiáng)調(diào)觀音經(jīng)的作用,其目的是宣揚(yáng)佛教。《今昔物語集》中有一則《元明天皇始建元興寺》,故事中宰相奉命去別國帶回佛像,但中途佛像上的佛珠被龍王竊取,宰相只得請求龍王歸還佛珠。龍王表示:龍子龍孫以前有九苦,自從得到了這顆寶珠,九苦便全除。于是宰相便為其抄寫金剛般若經(jīng),爾后龍王一族方脫離蛇道,免除苦難并將佛珠送還。將這兩則故事連起來看得話可以推斷出蛇女就是化龍前的苦難,即沒有佛經(jīng)的話,化龍之前是需要經(jīng)過墮入蛇道這一過程的。
在女子遇蛇難的故事中,女子體現(xiàn)得更多的是美麗、善良以及機(jī)智聰明的形象。面對蛇難借助佛經(jīng)制服毒蛇,并成功脫離蛇難。毒蛇化身為蛇郎來娶女子,這與《古事記》中的蛇郎“水乞型”類似。唐植君(2022)在分析記紀(jì)神話中的人蛇婚姻時指出,八岐大蛇與蛇郎“水乞型”從這兩則故事整體來看,兩則故事結(jié)構(gòu)都是“求水(豐收)約定嫁女→蛇如約來娶女→設(shè)計殺蛇→女回家(再嫁)”,從故事情節(jié)細(xì)節(jié)來看,內(nèi)容幾乎一致,只有殺蛇之人身份不同。同理,在《今昔物語集》的這則故事中,也可以從故事整體來分析這則故事的結(jié)構(gòu):“救蟾蜍并約定嫁女→蛇如約來娶女→設(shè)計殺蛇→女得救”。從這也可以看出《古事記》等前代作品對后世的影響。
而在卷二十第九則女子遇蛇難的故事中,體現(xiàn)的則是因果報應(yīng)。這與前文提到的第一則遇蛇難中的蛇男不同,這則故事中的蛇更為突出的是其動物性,身為動物的蛇在女子體內(nèi)產(chǎn)卵;而《山城國女人信觀音得免蛇難》更加突出的是蛇的神性,即它有能力幻化成人。
(二)故事敘述特點
《今昔物語集》中記載了大量的蛇與女性關(guān)聯(lián)的故事。在此類故事中大多數(shù)的女性都是善良、美麗的化身,然后將“蛇”和“女性”聯(lián)系起來。女子化蛇的故事結(jié)構(gòu)一般為:生前執(zhí)念→死后化蛇→夢示→供養(yǎng)佛經(jīng)→脫離蛇身。在此類故事中,作者一方面借助此類故事弘揚(yáng)佛教清心寡欲、六根清凈的思想,勸誡大眾要斬斷因感覺帶來的欲望和妄念等消極的負(fù)面因素。
蛇女與龍的故事中,作者則是借助蛇女、龍王等神異角色來弘揚(yáng)佛經(jīng)。此類故事的結(jié)構(gòu)為:少年貧困、信奉佛經(jīng)→救助蛇女→蛇女報恩→少年脫貧。正如前文所說的,這類故事中更多的是展現(xiàn)民眾的善良以及佛經(jīng)的重要性。在弘揚(yáng)佛經(jīng)的同時,勸誡民眾善良、樂于行善。
女子遇蛇難這類故事中,故事結(jié)構(gòu)則可以細(xì)分為兩種。一是救蟾蜍并約定嫁女→蛇如約來娶女→設(shè)計殺蛇→女得救;二是女子勤勞勞作→遇蛇難→得救→再遇蛇難喪命。這兩類故事中蛇難都是推動故事發(fā)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故事發(fā)展中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這類故事承襲了前代蛇故事的特點,佛教說話故事在吸收、承襲的過程中,積極地將佛教因素融入其中。突出佛經(jīng)在這過程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同時借此宣揚(yáng)其因果報應(yīng)的思想,啟迪民眾誦讀佛經(jīng),勿行惡。
《今昔物語集》通過以上女子化蛇、女子遇蛇難等故事宣揚(yáng)佛教,告誡民眾要虔心持誦、供養(yǎng)佛經(jīng)。同時教化民眾生前要積善,即使現(xiàn)世作惡沒有得到報應(yīng),但是也會有因果輪回報應(yīng),轉(zhuǎn)世也會得到相應(yīng)的報應(yīng)。
三、形象及特點的成因
(一)前代蛇女故事傳說的影響
在生產(chǎn)力相對落后的時代,日本本土的蛇文化是將“蛇”作為一種信仰出現(xiàn),人們將蛇的神異性與夸張的想象力結(jié)合下,更為凸顯蛇的神性。如《常陸風(fēng)土記》中就記載了古代的人們認(rèn)為:蛇會借助神的身體在人前現(xiàn)身。
而后在“蛇”進(jìn)入文學(xué)作品后,與不同的意象相互交融,產(chǎn)生了不同的形象。“蛇”與“女性”的融合的話,正如前文提到的《古事記》中的肥長比賣、而后基于肥長比賣在滋賀縣興盛起來的比良的八荒故事等。
其中肥長比賣的故事凸顯的是蛇女的愛而不得。但從故事內(nèi)容也看,此時人們對蛇的看法也從前面的強(qiáng)調(diào)蛇的神性開始逐漸發(fā)生變化。不再一味地凸顯蛇的神性,目光逐漸下移到蛇的動物性。隨之人們對蛇的恐懼也就更為凸顯。也就是由最初的蛇信仰的崇拜到開始正視“蛇”這一動物恐懼的轉(zhuǎn)變。因此在肥長比賣的故事中,本牟智和王子在得知少女原來是蛇的時候,害怕得慌忙逃竄,這才會有肥長比賣苦苦追逐愛人的畫面。這一形象在《今昔物語集》中蛇女形象中也有所反映,尤為體現(xiàn)在其女子化蛇中。作品中女子化蛇里大部分的蛇女都有癡戀、貪念等特點。卷十三第四十三則中的女子之所以死后化蛇是由于身前留戀這人間的梅花;道成寺蛇女是貪戀情欲;第十四卷第四則中女子由于留戀錢財而墮入蛇道。
因此《今昔物語集》中的蛇女形象也受到了前代蛇女形象影響。但我們也可以看出相比前期的作品,《今昔物語集》中的蛇女形象也要更加豐滿。
(二)推廣佛教的需要
《今昔物語集》編纂的目的之一便是宣傳佛教,弘揚(yáng)佛法。而“蛇”與“女性”結(jié)合的許多故事都是女子墮入蛇道或者女子遇蛇難,而解決這一困境的方法便是依托于佛教。通過信奉、供養(yǎng)佛經(jīng)達(dá)到脫離苦難的目的。
正如前文說到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人們對蛇的關(guān)注逐漸由“蛇信仰”轉(zhuǎn)變?yōu)槠鋭游镄浴6译S著佛經(jīng)等的傳入也加速了蛇的世俗化。佛教經(jīng)典中蛇屬于“惡”,佛教中所宣揚(yáng)的六道輪回,人死后根據(jù)生前的善惡,輪回于六道之中。而這一點也在《今昔物語集》中得到充分地體現(xiàn)。其中尤為突出的便是人生前作惡,死后轉(zhuǎn)生為動物。
將“蛇”與“女性”結(jié)合產(chǎn)生負(fù)面形象后,一方面可以推動人們對蛇認(rèn)識的世俗化,另一方面則有力地推動了佛經(jīng),乃至是佛教在日本的發(fā)展。將故事的主人公定位為動物以及女性的身上,不僅僅增加了這類故事的真實性,尤其是更為貼近民眾生活,使得讀者更加容易接受此類故事以及認(rèn)同故事背后所傳達(dá)的觀念。
(三)弘揚(yáng)因果報應(yīng)思想
女子化蛇這一類型就特別突出了因果報應(yīng)的思想。隨著佛教的傳入和發(fā)展,為了宣揚(yáng)其教義思想,很過佛教故事也隨之傳入日本。經(jīng)過本土化的改造后產(chǎn)生了適應(yīng)日本本土的故事,而這也促使了其在日本的傳播發(fā)展。
在這一類型的故事中,女子因為各種執(zhí)念,比如因為對紅梅的執(zhí)念、對金錢的執(zhí)念等而墮入蛇道。以及女子遇蛇難的《醫(yī)師診治與蛇交的女子》故事中,女子也是因為前世的因,才導(dǎo)致今世不斷遇到蛇難,雖然被醫(yī)師及時救治逃過一劫,但沒有設(shè)法減輕罪孽,最后還是遇蛇難而喪命。
在這類故事中突出了前世與今生的聯(lián)系。在變身故事的基礎(chǔ)上,加入佛教的因果輪回報應(yīng)思想。通過有情物從人間道向畜生道流轉(zhuǎn)以及從畜生道流轉(zhuǎn)回人間道的故事,突出佛經(jīng)的作用,并在此基礎(chǔ)上突出業(yè)因果報思想,勸誡民眾生前行善,積累善根。
四、結(jié)語
至此,大家可以簡單了解《今昔物語集》中“蛇”與“女性”的關(guān)聯(lián)。二者的聯(lián)系既體現(xiàn)在蛇與女性結(jié)合后產(chǎn)生的蛇女形象,也體現(xiàn)在女子遇蛇后產(chǎn)生的各類故事中。“蛇”與“女性”的關(guān)聯(lián)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女子化蛇后產(chǎn)生蛇女形象,女子生前雖然是善良的,但因為執(zhí)念墮入蛇道后產(chǎn)生的蛇女形象卻是邪惡的。二是蛇女與龍故事中,作為龍的幼年形態(tài)的蛇則具有善良、美麗以及知恩圖報的特點;三是借助女子遇蛇難這類型故事強(qiáng)調(diào)佛經(jīng)的作用,在百姓中起到弘揚(yáng)佛法的作用,同時借助這類故事來弘揚(yáng)因果報應(yīng)的思想,強(qiáng)調(diào)要行善,切勿作惡。其中的女子形象是美麗、善良的美好形象。
日本本土的蛇信仰,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發(fā)生變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沖擊下,人們對蛇的目光開始由最初的崇拜開始轉(zhuǎn)向其動物特性上。佛教中的蛇是淫欲、貪戀的代表,這個也隨著佛教的傳入體現(xiàn)在當(dāng)時文學(xué)作品中。《今昔物語集》中的蛇,尤其是蛇女便是這影響的突出表現(xiàn)。
基于此,結(jié)合日本本國前代的蛇文化影響、宣揚(yáng)佛經(jīng)以及傳播佛教因果轉(zhuǎn)世報應(yīng)等思想,《今昔物語集》中產(chǎn)生了大量的“蛇”與“女性”相關(guān)聯(lián)的故事。
參考文獻(xiàn):
[1]蔡春華.中日文學(xué)中蛇形象[M].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
[2]唐植君.記紀(jì)神話與昔話中蛇郎故事結(jié)構(gòu)[J].日語學(xué)習(xí)與研究,2022,(04):70-78.
[3]王貝.中日變身譚思想基礎(chǔ)與影響因素研究[J].山東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2018,(05):29-35.
[4]曾琪之.中日文學(xué)中蛇女形象發(fā)展歷史的對比研究[J].漢字文化,2022,(02):132-133.
[5]周作人.今昔物語[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
[6]徐微潔.漢日動物形象特征比較研究——以十二生肖動物為視角[J].浙江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1,(05):1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