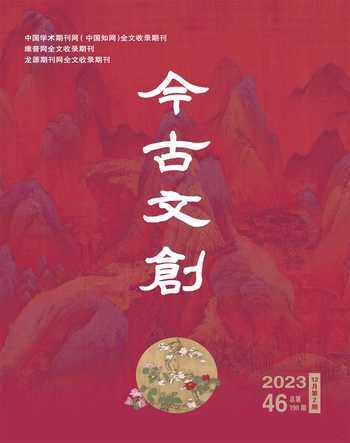福柯權力空間下 《年輕的好男兒布朗》中的人物生存與發展
【摘要】《年輕的好男兒布朗》是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經典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依據福柯的權力空間理論,本文主要分析小說中清教思想籠罩下村莊代表的社會空間,森林代表壓抑扭曲的人物心靈空間以及小說人物在權力空間下重塑自我失敗而導致的個體生存悲劇。布朗生活的薩勒姆小村作為故事發生的舞臺,充斥著濃厚的宗教氛圍,擁有監視、規訓、威懾與懲罰的權力機制,人物的心靈空間不斷受到壓迫而變得扭曲,由此滲透出霍桑對狂熱宗教和偏執教派權力統治對人的天性壓抑及精神摧殘的批判,體現出作家對個體生存與發展的憂思。
【關鍵詞】權力空間;清教思想;生存
【中圖分類號】I71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6-004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13
一、引言
納撒尼爾·霍桑是美國19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家,霍桑的作品大多探討靈魂的罪惡意義,探尋人類內心的善惡問題。《年輕的好男兒布朗》是霍桑短篇小說中極為重要的一篇,被認為是霍桑思想及其藝術手法高度結合的作品。小說描繪了年輕的布朗因無法抵制魔鬼的誘惑,在新婚妻子費絲的苦苦哀求之下仍然拋棄她去赴魔鬼的邀約,并描述了布朗在赴約林中的夢幻故事。長期以來,國內學者大多從該小說的象征隱喻及精神分析的角度,以原罪思想和神話原型對該小說進行探析,但是很少從空間的角度與權力結合對該小說的社會空間、心靈空間進行詮釋,并探討小說人物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因此,本文將從福柯的權力空間視角出發,探討小說中清教思想的嚴酷統治,狂熱的宗教教條及偏執教派對人物生存的影響和精神的摧殘。薩勒姆村莊作為充斥著濃厚清教文化的社會空間,對人們進行監視和規訓,擁有威懾和懲罰的權力機制。在此社會空間下,人物的心靈空間不斷被壓抑、扭曲,最終在權力空間的壓抑之下導致人物的生存悲劇。從權力空間視域角度出發,可以進一步對文本進行多元化解讀,探討霍桑對于加爾文清教主義的矛盾思想,并關注人類在空間維度中的生存和發展。
二、村莊——宗教思想充斥下壓抑的社會空間
在福柯看來,空間是各種權力關系交鋒的場所,他致力于揭示空間場域背后隱藏的各種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福柯提出了‘權力空間’這一批判思想,認為空間是知識話語與權力運作的具體場所,權力空間作為一種強力意志和指令性話語,存在和作用于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6]92英國哲學家杰里米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建筑(panopticon),監視者可以對囚禁者進行全方位的監視。囚禁者只能被觀看,而不能觀看,他們在不知是否被監視的情況下,不敢輕舉妄動,身體上和心理上都時刻處于全方位被監視的緊張狀態。
小說中描繪的社會空間,即村莊,代表了時刻監視,壓抑人物的權力場所。霍桑由于家族背景,深受加爾文清教主義影響。在了解他的祖先關于驅巫案的殘暴行為之后,他對此感到羞愧,對宗教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看到了宗教狂熱和宗教教條給人們帶來的不良影響,甚至對人性的摧殘。在薩勒姆地區一帶,人們對宗教思想極為尊崇,視其為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威。人們處于清教思想的嚴酷統治之下,思維和日常行動都受到一定影響。
小說以清教思想濃厚的薩勒姆村莊為故事舞臺背景,開篇即以一種神秘的色彩描述布朗不顧新婚妻子費絲的苦苦哀求,仍要在傍晚時分與她分別,去完成他神秘的差使。小說并未對村莊進行過多的直接描述,但是從人物的思想及行為可看出宗教倫理浸潤的村莊的壓抑特性,體現出村莊對人們時刻進行的監測和規訓。
布朗的妻子費絲(Faith),她的名字取得恰如其分,代表信仰和忠誠,費絲不僅是布朗世俗中的妻子,也代表著布朗的精神依托及對宗教的信仰。布朗在赴魔鬼邀約的路途中,偶遇一位與他模樣相似的年長者,年長者提及曾與布朗的先輩們多次為赴魔鬼之約而經由叢林,半夜過后又快活返回,并向布朗坦言他們曾經做過的惡行。“你那當警察的祖父當初在薩勒姆的大街上神氣十足地鞭打著那個教友派女人往前走的時候,我幫過他;在菲利普王之戰中,又是我給你父親拿來了北美油松柴,還是在我的壁爐里點燃后,給一個印第安人的村子放了一把火。”[4]2583而布朗認為,在教會制度如此森嚴的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做出如此惡毒之事,因為村莊中的所有行為都處于監視者的監視范圍之下,若這種事情只要稍微有些謠傳,那么他們早已被驅逐出新英格蘭之外了。薩勒姆村莊中權力的威懾及懲罰作用立即凸顯出來,村莊這一社會空間隱含著規訓與懲罰的權力機制。“可是,要是我和你繼續走下去的話,我該怎么迎著那個好老頭兒,我們薩勒姆村的教長的目光呢?無論在禮拜天還是演講日,他的聲音都會讓我發抖呢。”[4]2585當布朗遲疑是否要繼續赴魔鬼邀約的旅程時,村莊中的宗教意識及思想使他感到畏懼,因為做出任何違反道德或不良之事后,布朗都難以直面教長的目光,這種威懾的力量籠罩著整個村莊,不斷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著道德約束。古蒂克勞伊斯老太太是一位非常虔誠,被人們奉為楷模的老婦人,她從小便教過布朗教義回答,直到現今還是他道德和精神上的規勸人。趙永琪提出“在一個為話語所統治的社會中,人的思想、意志以及行為是通過知識來進行道德判斷和規訓的。因此,知識就是權力。任何人只要占據了一個生產主流話語與主流知識的位置,都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權力,亦可對其他的社會群體進行控制與規訓”[7]3。
由此可見,村莊從該社會空間最基礎的思想教育開始,對人們進行潛移默化地影響,以便對社會群體更好地進行管控和監測。而這種恒久性的宗教思想加注在人們身上,使人們如囚禁者一般處于有意識的監控狀態之下,受到壓制性的規訓而感到恐懼,從而將那些戒律內化成一種自律,以達到權力對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規訓作用。
三、森林——人物心靈空間壓抑扭曲的表現
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同時也可以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薩勒姆村莊清教思想濃厚,村民在權力體制的規訓之下對自己有著嚴格的道義要求,但人們長期處于壓迫規訓的狀態之下,心靈開始變得扭曲。森林這一空間意象可以看作是布朗心靈真實狀態的寫照。在布朗離開村莊之前,一切都還是正常現實的平鋪直敘,讀者只是對其將要進行的差使感到略微神秘,并沒有體現出其他扭曲的形態。然而,在布朗轉身進入黑沉沉的叢林后,一條陰沉黯淡的小路,如同邪惡籠罩一般,他所經過之處兩旁的樹木就淹沒不見了,這種詭異的環境加上布朗奔赴邪惡目的的旅程使人對此感到意外。布朗離開妻子走進這魔幻的森林去追逐邪惡,此時的森林空間與它原本自然的形象大相徑庭。森林,作為一個美化環境,凈化心靈的場所,不僅沒有給布朗帶來心理上的慰藉,反而在此空間內為布朗鋪上一條踏往邪惡、赴魔鬼邀約的道路。此時,森林這一意象,隱喻出的是人們逃離制度森嚴的村莊后,盡情釋放心中的罪惡之處。在這個“內部之處”,布朗一邊因內心的負罪感而感到痛心,一邊又為與魔鬼相聚的吸引力而躑躅不前,充分體現了布朗內心隱秘已久“惡”的一面。
如果將村莊視為外部空間的話,森林則是人物真實世界的內部空間。小說結尾處提示,布朗是不是在森林中睡了一覺,僅僅是做了一個荒誕怪異、同鬼巫聚會的噩夢呢?任曉晉認為,“霍桑用夢中的森林之旅象征著一個人的心靈之旅。這次的林中遠游不僅深入到了密林深處,更深入到了人的內心世界,深入到了一個正經歷著成長的痛苦的年輕人的心靈世界。霍桑把布朗的人生經歷濃縮在一場林中噩夢中,這其實對應了一種人生如夢的世界觀。”[5]25
然而,布朗所經歷的這場森林遠游,不僅折射的是其成長所面對的困惑與痛苦,更是在薩勒姆村莊權力壓抑下試圖釋放自我的體現,森林空間只是清教思想籠罩的社會空間的一種延續。“如果一種機構試圖通過施加于人們肉體的精神壓力來使他們變得馴順和有用,那么這種機構的一般形式就體現了監獄制度。”[3]259正是在村莊這一社會空間下,令人窒息的管控制度給人們帶來精神上的壓力,才有了森林旅途中教長、牧師、費絲、善良人士都前來參與魔鬼聚會的場景。
整個森林旅途可以通過布朗面對信仰的嚴峻考驗以及他受到的幾次心靈震撼和打擊來闡釋。在他認出他的精神導師克勞伊斯老太太時,他不可置信地看到她與那位代表罪惡的老布朗是好朋友,并接受了蟒蛇形手杖,以更快的速度前往魔鬼的圣餐會。布朗以為她一心想要上天堂,怎么轉身卻去見了魔鬼?他開始退縮,不愿意為了這差事再繼續前進,而此時等待他的是第二次致命打擊,他在路邊辨別出了教長和古金副主祭的聲音,他不敢相信平日從容地參加授予圣命和教士會議的兩位導師,竟然也去參加魔鬼的聚會。他們寧愿放棄授予圣命的宴席,也不愿錯過此次夜里魔鬼盛大的集會。緊接著第三次致命打擊使布朗徹底顛覆了他的認知。他絕望地發現自己純潔的費絲也來參加聚會。在絕望得發了瘋以后,布朗直沖聚會地點。在那里,播放著平日議事廳莊嚴的圣歌,他看到了平日熟識的貴婦,美麗的少女,德高望重的圣者,虔誠的夫人。而魔鬼最后——揭示這些平日圣潔之士的罪孽和秘密行徑時,布朗全身戰栗,用盡最后一絲力氣向費絲發出呼喚“仰望天國,抵抗邪惡”。
森林空間的旅途在這短暫如夢的時間中結束,不管這是一個荒誕怪異的夢,還是布朗親身經歷的鬼巫聚會旅程,映射的都是他心靈空間的壓抑、緊張、混亂情緒。而薩勒姆村莊眾多村民前往魔鬼聚會也體現了無論是圣人還是惡人,在長期受到監視管控的情況下,原罪開始展現出來。森林旅途是人物心靈扭曲壓抑的結果,是社會思想體系延續的另一空間,體現了權力體制對人物生存的影響和身心的殘害。
四、布朗之死——權力空間下的個體生存悲劇
布朗在赴魔鬼之約后,認識到人們人性扭曲、罪惡的一面,經歷了從信仰村莊固有的清教思想再到懷疑的巨大心理變化。當他看到虔誠人士赴魔鬼之約后回到村中,仁慈的老教長散步思考著他的布道詞,布朗走過他身旁依舊感到畏縮顫抖。副主祭老古金在家做著禮拜,他那神圣的祈禱詞透過窗戶也能依稀讓人聽見,時刻使人警醒。當布朗看到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基督徒古蒂克勞伊斯太太,向一位送牛奶的小女孩講解教義時,布朗一把猛地拉開小女孩,仿佛從魔鬼手中把她救出來一般,不讓她的心靈受到毒害。他本以心愛的妻子費絲為信念,在他面臨魔鬼誘惑時,作為他唯一的道德約束力,以至于不被魔鬼的誘惑所吞噬。由此可見,費絲對于布朗來說,不僅是信仰的寄托所在,同時也時刻在監督約束著布朗的身心。村莊中各種講解布道,教義的行為,也為權力的無孔不入提供了可能,這并不是粗暴殘忍的壓制方式,而是一套標準化,符合社會情境的溫和形式,來操控管理該空間內群體,揭示出這種權力與知識的隱性運作形式。
盡管其他人依舊做著禮拜,背誦禱詞,以正常的心態度日,布朗卻再也無法正常面對周遭的一切,甚至表現出心理失常。每當安息日,會眾們唱起神圣的頌歌之時,他卻充耳不聞,因為一支罪孽的贊歌沖擊著他的耳膜,把祝福的旋律全淹沒了。當教長講著宗教神圣的真理,圣徒般的生活及未來的福祉時,布朗聽后面色蒼白,擔心屋頂會轟然塌下,壓倒在這些褻瀆神靈的人頭上。
由于布朗再也無法恢復到健全的狀態,整日憂郁愁悶,生活在格格不入的社會當中,他無法對各種祈禱,思想凈化形式予以認同和妥協,而是表現出極為排斥與厭惡的態度,但又苦于無法在權力森嚴的體制下做出反抗,只能默默忍受著規訓與控制,最終在愁苦中死去。“如果思維和行動的可能性是由主體不能控制的,甚至不能理解的一系列機制決定的,那么這個主體從它不能在解釋事件時成為可以引證的根源或中心這個意義上說就是失去了中心地位。”[2]298薩勒姆小村中人物時刻受到監督,受到知識權力的隱性控制,只有在森林旅途中再現被壓抑的主體身份。布朗正是被那種未知感所刺激,努力去追求生存的真相,這趟心靈旅途揭示了村莊中的權力機制,這一切在布朗再次回到村中現實生活時,喪失的信仰及自主性身份解體使他認清了清教主義思想原罪論的極端性和偏執教派的權力機制,他對村中一切感到反感,從以前的好男兒布朗變成了一個疑神疑鬼,憂郁的人。他無法在權力壓制下看到抵制的可能性,布朗主體地位的喪失最終導致了他的生存悲劇。
在《規訓與懲罰》當中,福柯提到將高度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身體上,“尤其是身體本身被權力關系所投資的方式,并開始了權力的檢驗。福柯宣稱,社會并不是一個充滿景觀的空間,而是處處充滿著監視的社會,他充分地構建出了這種現代的權力譜系關系”[1]192。
在小說中,薩勒姆村莊也存在森嚴且明確的權力關系,精細地規劃出了馴服人們的監測體制。布朗在強大的社會監視下生存,產生了馴順的身體。而他最終認識這種體系的存在后,并未像其他人一樣選擇默認接受管控,他以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與外界產生了沖突,但沒有找到抵制的方式,也不愿繼續沉淪于這種權力監視之下,最終無法再次融入這個社會。與此同時,他心中也產生了一種自我沖突,他認清了權力機制的真實本質,但卻不愿意向此妥協,最終通過死亡來追尋精神上的解脫。
五、結語
綜上可知,通過對村莊這一社會空間的塑造,人們對宗教思想的尊崇猶如法律權威,整個薩勒姆村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之下。宗教文化在此社會空間內擁有巨大的道德約束力量和控制權,村莊中主導的思想觀念和嚴密的監視體系掌控著人們的生活,最終到達制造出馴順肉體的目的。在此強度的規訓之下,人們前往森林中赴魔鬼之約,布朗展現出罪惡的一面,認清了人們虛偽表面下的邪惡之處。森林中的魔鬼聚會是人們在權力監控下扭曲壓抑而釋放出的真實形態,這一內部空間充分展現了布朗及村民壓迫下的本我形象。布朗從森林中回來后,信仰的失落及認清清教主義思想的極端和偏執教派的嚴密管控使人變得壓抑扭曲,而薩勒姆村莊中其他偽善的“圣人”卻能重歸平靜的生活,繼續在這種嚴密監測的體系下生存。面對這種吞噬個體“真正自我”的權力空間體系,布朗無法尋求身體和精神上的救贖,他心中上帝的缺失以及自身主體地位的喪失使他郁郁而終,最終在此權力空間之下形成了個體的生存悲劇。
參考文獻:
[1]Wegner,E.P.“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th Century[C].Ed.Julian Wolfreys.Edinburgh: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2002.
[2]喬納森·卡勒.牛津通識讀本:文學理論入門[M].李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3]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4]納撒尼爾·霍桑.霍桑短篇小說集[M].胡允桓譯.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5]任曉晉,程寶燕.林中的噩夢成長的歷程——《小伙子古德蒙布朗》新解[J].外國文學研究,1998,(04).
[6]鄭佰青.西方文論關鍵詞——空間[J].外國文學,2016,(01).
[7]趙永琪,陶偉.權力空間的研究進展:理論視角與研究主題[J].世界地理研究,2017,(04).
作者簡介:
陳佳朦,女,漢族,江西萍鄉人,南昌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