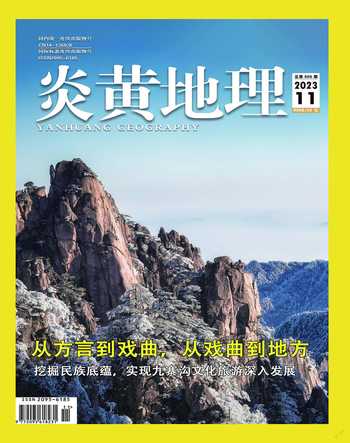鄂爾多斯青銅器文獻綜述
王錦華

鄂爾多斯青銅器研究始于19世紀末,是一門世界性研究課題。在研究形式上包括國外的圖錄匯編、國內專業著作論述、博物館展覽出版圖冊及大型類書收錄。在專題研究內容上,學界開展了包括鄂爾多斯青銅文化與周邊諸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具體造型和紋飾在內的多項研究。此外,學界也注意到了北方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關系,草原絲綢之路是近年熱議話題。
在19世紀末,我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出土了一批與中原器物形制迥異,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風格的青銅器。因鄂爾多斯高原原屬綏遠省管轄,曾將其泛稱為“綏遠青銅器”。這種青銅器廣泛分布于北方長城沿線地帶,大都出自墓葬,以小型器物居多,常與金銀飾品一起出土。經考證,這類器物是由生活在鄂爾多斯及周邊地區的早期游牧人所造,從商周延續至兩漢,各階段風格又有所不同,是北方民族文物的典型代表。
在為這批器物定名時,學界有不同的看法。1985年,烏恩在《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中,將陸續發現于鄂爾多斯、陜北、晉西黃土高原、冀北及遼西地區的青銅器暫稱為“商周之際北方青銅器”。1988年,田廣金、郭素新認為:“該類型青銅器以鄂爾多斯、陜西北部和山西呂梁為中心分布,并在鄂爾多斯地區建立起商晚期—兩漢時期的完整發展譜系。”兩位學者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中將其命名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目前學界采用的通行稱謂是“鄂爾多斯青銅器”。
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形式
受歷史原因所限,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始于國外學者,研究成果主要表現為描述性的畫冊或圖集。瑞典學者安特生在1932年發表的《動物紋中狩獵巫術的含義》中提出“鄂爾多斯青銅器所見紋飾是當地氏族部落的圖騰象征”。A.薩里莫尼(A.Salmony)在《盧芹齋收藏的中國—西伯利亞藝術品》一書收錄300多件動物紋牌飾。由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美國華盛頓沙克勒和佛利爾美術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瑞典遠東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機構都藏有鄂爾多斯青銅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國內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多集中于征集的傳世品和零散見世的出土品。1959年,和林格爾縣范家密子鄉西畜子村出土了一批銅器。1962年,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速機溝出土了一批銅器。1986年,田廣金、郭素新出版了《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這是首部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主題的研究性專著,書中上編對“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進行了分類和分期,論述各時期的器物組合和文化特征;下編整理1980年以前對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墓葬遺址進行發掘的考古報告。因該書多著錄傳世品,學界對書中部分觀點仍有不同看法。
2008年,“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鄂爾多斯召開。會議就“鄂爾多斯青銅器研究”“中國北方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鄂爾多斯青銅文明與華夏青銅文明研究”“歐亞草原之路研究”四個課題展開研討,并于次年出版《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奇朝魯編成《鄂爾多斯學研究2017年論文集》,其中收錄有甄自明的《鄂爾多斯歷史、文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該篇論文重點介紹了鄂爾多斯研究會多年的學術成果,并指出了當時研究的薄弱環節。
除被收藏于故宮博物院等國內大型博物館外,鄂爾多斯還設有專題性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該館建于1982年,是“目前收藏鄂爾多斯青銅器數量之多,品種之全,檔次之高的世界之最”。鄂爾多斯博物館選取館內外各式青銅器主編了《鄂爾多斯青銅器》和《馬背上的青銅帝國》,并分別于2006年和2021年出版。另外,該館依托通史陳列與專題展覽,出版了《農耕、游牧、碰撞、交融—鄂爾多斯通史陳列》和《漫漫絲路,澤遺百代—草原、海上絲綢之路文物精粹》兩書。2013年,楊澤蒙的《早期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瑰寶——鄂爾多斯青銅器之最》選取了27件代表性極強的鄂爾多斯博物館館藏文物,概述各文物“最突出”的特點。
鄂爾多斯青銅器是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的關鍵證據,學者在研究文物的同時,也將其與鄂爾多斯歷史、北方民族歷史和草原絲綢之路緊密關聯。在多個相關領域的研究著作中,涉及鄂爾多斯青銅器的有以下幾本:《鄂爾多斯文物考古文集》論述了舊石器時代至元代的考古遺跡與遺物,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于1981年編寫完成第一輯,王志浩于2004年編寫完成第二輯;1989年,梁冰編著的《鄂爾多斯歷史管窺》;1995年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的《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族》;2007年趙新民、楊道爾吉編著的《鄂爾多斯史話》;2009年鄂爾多斯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寫的《鄂爾多斯大辭典》;2011年張占霖主編的《鄂爾多斯文化·文物卷》等。
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專題研究
鄂爾多斯青銅文化與周邊諸文化的關系
從考古學上講,類型學分析和對比鄂爾多斯青銅文化與周邊諸文化的屬性是追溯鄂爾多斯青銅器淵源的重要一環。鄂爾多斯青銅文化與周邊諸文化主要有以下三種關系。
1.同一地區不同時段青銅器物的源流傳承關系
1988年,田廣金、郭素新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研究》研究基礎上,利用朱開溝遺址的新材料比對了鄂爾多斯青銅器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張家口地區夏商階段遺存、朱開溝文化遺存、呂梁地區夏商階段遺存以及陜北地區夏商階段遺存的親疏關系,得出鄂爾多斯青銅器源自朱開溝文化,并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交流密切的結論。2002年,林沄的《夏代的中國北方系青銅器》認為北方地區的青銅器在夏代已初具規模。
2.不同地區同一時段青銅器物的交流融合關系
學者對鄂爾多斯青銅器與北方系青銅器的從屬關系、鄂爾多斯青銅器與歐亞草原文化的互動關系作出討論。其中,烏恩對青銅短劍、動物紋樣和帶飾的研究為確立北方文化本土起源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1978年,烏恩的《關于我國北方的青銅短劍》從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區分出了以丁字形銅柄曲刃劍為代表的青銅文化,并提出北方地區曲柄劍至少在商晚期就已經出現,以及我國北方地區Ⅱ型短劍與中原柳葉劍并行,且早于卡拉蘇克文化“凹格短劍”和塔加爾文化“十字形柄頂短劍”“獸形柄頂短劍”的觀點,有力地駁斥了“中國青銅文化北來說”的謬論。1994年,烏恩在《略論怪異動物紋樣及相關問題》中論證了“鳥喙獸身”紋樣的淵源,區分出“鄂爾多斯青銅器動物紋”與“斯基泰野獸紋”的異同,認為在戰國偏晚時期,鄂爾多斯及周邊地區受到了斯基泰——阿爾泰風格的影響,怪獸形象也由此而來。2002年,烏恩在《論中國北方早期游牧人青銅帶飾的起源》中評析當時學術界關于青銅帶飾起源的爭議,論述了夏家店上層文化、毛慶溝文化、桃紅巴拉文化和楊郎文化出土材料的相關性,最終認為中國北方在青銅時代就已出現青銅帶飾的雛形,境內外相似的帶飾造型是公元前5—前3世紀歐亞大陸間頻繁互動的文化證據。
3.同一地區同一時段不同器物的親疏遠近關系
1982年,蓋山林在《陰山匈奴巖畫動物紋與鄂爾多斯青銅器動物紋的比較》中討論了巖畫和青銅器的動物紋在構圖、風格和手法等方面的相似性,指出兩者在確定各自族屬的研究中可互為佐證。
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具體造型
1.實用器物
鄂爾多斯青銅器多為實用器,按照用途可分為兵器和工具、裝飾品、生活用具及車馬器四類,雕刻技藝有浮雕、圓雕和透雕三種。學界針對某類器物或某類紋飾展開研討,復原、建構早期游牧民族生活。另外,學者也對部分有爭議性的器物進行深入研究。其中,腰帶飾品和青銅短劍是出土最多的器物,受到的關注度較高。
帶扣、帶鉤和牌飾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的腰帶飾品,俗稱“西番片”。1983年,烏恩的《中國北方青銅透雕帶飾》論述青銅帶飾的文化淵源,指出鄂爾多斯及其周圍地區是青銅透雕帶飾的發源地。2015年,郝建斌、王文靜的《民俗之美——談鄂爾多斯青銅牌飾的裝飾規律》從藝術學的學科視角分析了青銅牌飾的藝術表現形式。2016年,張美玲的《鄂爾多斯青銅器腰帶飾品的裝飾藝術研究》以“腰帶飾品”為研究對象,認為鄂爾多斯青銅器對北魏鮮卑拓跋族、遼契丹和元代蒙古族等民族產生了重要影響。
青銅短劍劍身扁平,多呈柳葉形,劍柄裝飾性較強,朱開溝遺址出土的短劍約屬商代前期,是我國出土最早的青銅短劍。1980年,林沄的《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詳細論述了東北地區銅劍的形制和特征,對族屬進行了探討。2012年,楊澤蒙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之再認識》中指出青銅短劍除用于搏斗實戰外,該類型短劍還是匈奴人歃血為盟的“徑路刀”前身。次年,夏侃也以《鄂爾多斯青銅器之再認識》為題,深入分析了“薩滿”和“徑路”,“青銅匙”與“鮮奶祭”,“銅鏡、鈴鐺”與“祭祀”三組關系,提出了青銅杖首與中華民族敬老習俗有關的新觀點。
近年來,對鄂爾多斯青銅器部分有爭議性器物的相關研究也在深入進行。1998年,王克林的《騎馬民族文化的概念與緣起》對田廣金在《鄂爾多斯青銅器拾零》收錄的“青銅騎馬造像”進行辨認。林沄考察了收藏于賽克勒博物館、東京博物館的兩件垂飾,隨后在2003年發表的《所謂“青銅騎馬造像”的考辨》中考證該飾件實為“猴子騎馬”垂飾。2009年,韓金秋在《鄂爾多斯龍首鑣芻論》正名《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一書中的“龍首匕”為“龍首鑣”,并從“首、柄、端”的結構和器物整體形制的角度提供進一步解釋。
2.薩滿用具
學界將紋飾過于繁縟,裝飾過于豪華的器物歸為特殊器物。2014年,張亞聰的《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北方草原動物紋樣研究》把“虎咬馬”“虎咬鹿”的圖像與薩滿教的教義“萬物皆有靈魂”相聯系。2014年,陸剛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造型藝術研究》提出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神性主題與北方民族的宗教觀相契合。2019年,陸剛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造型主題與北方早期薩滿宗教觀的內在聯系》中提出薩滿教崇信的神靈是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創作動力。
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紋飾解讀
學界對鄂爾多斯青銅器某些圖像的模糊定義展開討論,并從考古類型學、美學及藝術學等角度研究紋飾的內涵與技法。同時,學界也開始關注北方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關系,草原絲綢之路是近年的熱點話題。
2009年,林沄在《歐亞草原有角神獸牌飾研究》中認為新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出土的三件牌飾之形象非馬非虎非怪,將這種流行于歐亞草原地區的虛幻動物視為“有角神獸”,同時指出“鉤喙有角蹄足動物”的另一衍生形象——“相背跪伏的成對動物”被誤認作了“鷹喙馬身獸紋”和“雙怪獸紋”。2020年,陸剛在《怪獸不“怪”——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鷹喙馬身造型及文化內涵解讀》中認同了林沄的“神獸”定義,并以圖像學的研究方法佐證了這一觀點。2012年,王飛虎的《陰山虎巖畫初探》參照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陰山巖畫進行斷代,利用圖像學理論比較鄂爾多斯青銅器和巖畫的虎圖案。該文重點關注鄂爾多斯青銅器虎圖像的四肢演化規律,認為分布在內蒙古中南部和甘寧地區的鄂爾多斯青銅器虎圖案是虎紋發展的巔峰。
2010年,楊澤蒙詮釋了青銅器的虎紋紋飾,在《由鄂爾多斯青銅器動物紋中的虎造型看中華生肖觀的起源》中提出早期北方民族對中華民族十二生肖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后的十余年,學界以馬紋、鹿紋、蛇紋、鳥紋、虎紋、牛紋等動物紋飾作為研究對象,研究集中于游牧民族審美藝術與中華民族生肖觀的互動。
2016年,范尊的《草原文化的象征符號》由今談古,通過實地調查,在北方匈奴文化的背景下從“圖像邏輯”層面分析了動物圓雕造型和搏噬紋牌飾的意義,總結出鄂爾多斯青銅器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所承載的思想體系,并運用符號學原理作出了對“鄂爾多斯青銅器代表游牧世界秩序”的新解讀:整個游牧民族認識世界和反映世界的法則及集體意識都體現在這種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上面。范尊還通過民族學研究方法探討了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所能傳達給后代游牧民族的思想體系及價值觀念。2021年,甄自明《鄂爾多斯高原上的歷代草原絲綢之路》在世界史視野下,首次梳理了漢、唐、元、明、清各代絲綢之路的脈絡,強調了鄂爾多斯青銅器與鄂爾多斯高原戰略地位的研究對于復原草原絲綢之路壯烈畫卷的重要性。
鄂爾多斯青銅器已進入學界視野近百年。田廣金、林沄、烏恩等人打下了堅實的研究基礎,楊澤蒙、甄自明、王京琴在前輩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探索。近一個世紀以來,鄂爾多斯青銅器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一門顯學。鄂爾多斯博物館是國內研究鄂爾多斯青銅器的主要陣地。
總的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國內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多集中于征集的傳世品和零散見世的出土品。20世紀70年代以田廣金先生為領頭人開始進行大規模發掘。此后,考古學者對青銅器物的形制和紋飾展開專題研究,揭示了青銅文化的多重文化內涵。學者在研究文物本體的同時,也將其與鄂爾多斯歷史、北方民族歷史和草原絲綢之路進行了關聯。目前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較為全面,遍及考古學、文物學、宗教學、民族學、美學等多門學科,但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保護與修復,文創產品的設計研究較少。另外,針對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學術性著作也不多,這主要是由于歷史條件限制,一部分文物仍流落于海外,所以對傳世品的研究難以建立起完整準確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隨著我國考古力量的壯大,鄂爾多斯青銅器研究必將再創輝煌。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