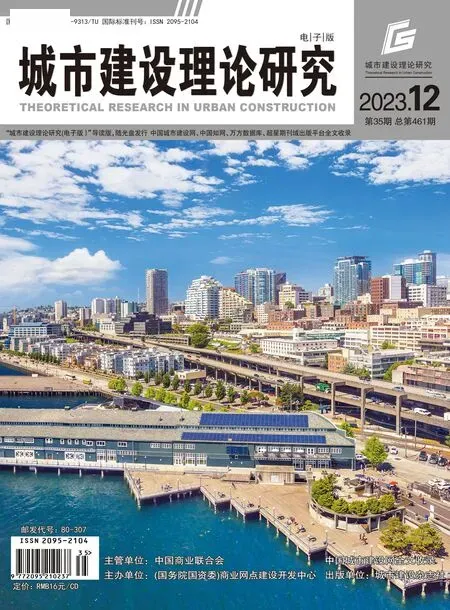彈性城市評價指標研究評述
粟立帆
廣東博意建筑設計院有限公司 廣東 佛山 528311
1 前言
“彈性城市”是當今城市規劃領域中的熱點問題,其評價指標體系更是該領域研究的核心之一[1]。為了使彈性城市更具有系統性,建設彈性城市,必須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標準或指標體系來指引[2]。國外彈性城市的評估國外彈性城市評價研究開展較早,2001年由崗德森和霍林(Gunderson and Holling,2001)提出的通過定性的指標來評估系統在面對外來壓力保存并更新自己以保持發展的能力。其后,彈性城市的評估迅速擴展到城市的各個領域。國內彈性城市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仍未構建。為彌補國內研究的空白,將國外彈性城市指標類型進行梳理,以期進一步認識彈性城市指標體系,分析現有問題與不足,預測彈性城市指標發展的趨勢,為我國制定彈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提供借鑒。
2 彈性城市與彈性城市指標
2.1 彈性城市
“彈性”(resilience)的概念最早來源于物理學,之后由美國學者霍林(Holling)提出應用于生態學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彈性最基本的概念是指簡單系統在被干擾后恢復到原有平衡狀態的能力。后彈性概念被運用于復雜系統并強調其系統內部的自組織和適應能力,如彈性聯盟(2010)認為:彈性城市為城市系統能夠吸收消化外界干擾,并能保持原有主要特征、結構和主要功能的能力;科瓦連科和斯諾特(Kovalenko and Sornette, 2013)認為彈性城市分為四個等級,其中工程彈性是彈性城市研究的初級階段,其后依次是生態彈性,活力彈性,動態彈性[3];福爾克(Folke,2013)總結出國外彈性城市研究發展脈絡,發現彈性城市的研究經歷了由工程彈性擴散到生態彈性、社會彈性,再到生態社會彈性的發展過程。
2.2 彈性城市指標
依據彈性城市評價指標的評價對象和彈性概念內涵,可以將現有相關研究分為彈性城市專項指標和綜合指標兩類。
專項指標的評價對象常選用具有代表性的單一的物理組件(如基礎設施),考察單一系統由平衡狀態到受壓狀態到恢復平衡狀態的變化[4-5]。基礎設施系統,特別是電、水、路網、醫療等服務部門,是該類重要的研究范疇。
綜合指標評價對象涵蓋了城市各個子系統(社會、經濟、生態、工程),考察復雜系統在收到外在沖擊時的適應性變化[6]。該類指標綜合考慮城市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的關系,將社會、生態、經濟、人文等系統結合考慮,全面系統分析影響城市彈性的內在驅動力,從而評估城市應對發展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的能力。
3 彈性城市專項指標
依據指標的復雜程度,可將彈性城市專項指標分為函數模型指標,復雜網絡指標,模糊物元指標。
3.1 函數模型指標
該方法基于對彈性城市理論的解讀,首先篩選城市工程彈性的構成要素,然后從工程彈性系統要素之間的關系出發,建立彈性評價函數模型。隨著人們對基礎設施系統研究的不斷深入,開始有學者發現評估彈性的吸收恢復能力應以時間作為主要函數。歐陽和萊昂納多(Ouyang and Leonardo Duen~as-Osorio,2014)利用時間彈性評估模型來分析系統演化的方式和不同災難影響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許多基礎設施系統都是在不斷進化的,一些危險出現的頻率、強度和系統的恢復性、反應性、魯棒性都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在這一思想下,提出了變化中的動態彈性指標模型,其數學表達式為曲線P(t)和TP(t)可用被用來測量不同性能指標的水平。至此,彈性評價函數模型由靜態指標向動態指標邁進。
3.2 復雜網絡指標
復雜網絡系統通過運用圖形理論法高度概括了復雜系統的重要特征。圖論中的圖是由若干點及連接兩點的線所構成的圖形,該圖像用點代表事物,用連接兩點的線代表相應的兩個事物間具有關聯性,以此來描述事物的相互作用關系。復雜網絡理論已被證明是一個魯棒性的理論框架來研究網絡系統的拓撲結構和各種現象發生時在系統中產生相互關聯的單位,被應用于生物、技術和社會網絡。最近更是延伸至的多層次、相互依存的網絡案例研究。
3.3 模糊物元指標
模糊數物元法是處理現實世界中客觀存在模糊現象的一種數學方法,模糊集合中的指標不具備普通數學集合非此即彼的特點,而是無需明確認定某一元素是屬于或不屬于該集合,具有亦此亦彼的特點。基于模糊理論的量化技術允許相互依賴的系統元素構建模型,評估的變量不需要準確或過多的數據。
美國西北國家實驗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2012)對于城市整體的基礎設施的彈性進行評估,制定了城市基礎設施系統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在明確城市主要基礎設施要素的基礎上,將魯棒性、響應時間、恢復時間、性能描述、恢復水平、性能損失、適應能力、亢余能力、敏捷性等作為主要的評價指標;具體的評估方法有,首先通過評估現有的基礎設施系統的屬性來確定用于改善系統彈性需求的要素;其次評估替代要素對增加系統彈性的影響力,最后利用模糊規則法來評估這些替代要素的主要性能。模糊物元法能夠客觀的描述評價對象,解決不同指標評價單位不相容的問題。
4 彈性城市綜合指標
彈性城市綜合指標,根據評價目的,可以將其分為系統型彈性指標和策略型彈性指標兩大類。
4.1 系統型彈性指標
系統型彈性指標力求提高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系統的彈性性能,強調彈性能力水平高低的評價(表1)。

表1 城市系統型彈性指標一覽表
4.2 策略型彈性指標
策略型彈性指標將“彈性”作為過程,側重于行動,即通過解決脆弱性而增加城市彈性,強調指標體系對彈性策略制定的直接指導作用。2009年,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亞洲的12個城市背景開展了名為亞洲城市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網絡聯盟(ACCCRN)活動。該活動希望通過城市的彈性策略,改善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ACCCRN的開發和實施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選擇城市范圍,確定城市的合作伙伴;
被選中的城市必須具備經歷快速城市化過程,且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有能力與ACCCRN進行合作來識別關鍵利益相關者、弱勢群體。經過篩選后最終選擇了印度、 印度尼西亞、 泰國和越南的12個“二線城市”。
第二階段:分析城市水平和脆弱性,共享學習并與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對話;
該階段首先理解各個城市的脆弱性,尤其是弱勢群體水平;識別潛在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分析氣候變化對關鍵行業的影響。城市系統、氣候變化、脆弱群體的相互關系如。
第三階段:制定統一的彈性框架并付諸實踐;
為了使市級規劃者和專業人員慎重對待城市的氣候彈性,需要確定一個統一的框架來指導彈性實踐。該階段明確了城市氣候彈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生態系統、代理社會團體、基礎設施、氣候災難。根據以上四部分,可以幫助:理解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確定哪些系統是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如何對這些系統產生影響;確定誰是最具弱勢的群體、地區、部門及其影響;識別組織產生脆弱的不同因素;評估至關重要的生態服務和功能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壓力的;評估關鍵的組織和群體的適應能力;制定彈性的發展策略。在這一框架的統一指導下,各國的研究小組開始制定應對當地氣候災害的彈性城市指標。
第四階段復制- ACCCRN將其不斷擴大。
5 彈性指標綜合評價與展望
5.1 綜合指標的評價客觀性有待提高
客觀性是對任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要求,城市是一個巨大的綜合體,任何一點錯誤都會造成不可預測的損失,因此對彈性城市的評估指標設置必須具有較高的客觀性。
專項指標因其系統相對單一,發展時間比較早,當今的研究成果顯著,經過了從靜態到動態、從單一到網絡、從具體到模糊的轉變過程;評價所針對的自然災害擾動也從單一向多尺度的多重擾動發展。專項指標因其數據來源相對單一便于指標的量化,可以用相對精確的數據分析結果評價城市彈性。但綜合指標是針對復雜系統制定的,指標內容繁雜,不同類別的數據換算困難,目前多采用主觀評分的方式,極易造成評價結果的主觀化,容易進入“有量無實”的維谷,給評價工作的客觀性造成阻礙。
由此可見,為了使彈性城市評價結果更具有客觀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著重探討綜合指標的量化方法,使不同類別的指標之間進行科學的統一。
5.2 綜合指標的可操作性應加強
建立彈性城市指標體系的目的是對城市的綜合彈性能力進行具體的評價,以達到增強城市抵御外在壓力的應變或者適應能力的目的,所以,評估指標體系應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專項指標評價系統稍顯成熟,現在已經在多領域廣泛應用,具有很強的操作性。而綜合指標中的系統型指標從城市系統(或城市子系統)的角度預測城市彈性,以期實現在世界(或某特定地區)范圍內城市彈性水平的比較及實踐方法的交流。但現實中,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區域條件不一樣,受到的外在沖擊類型及級別并不一樣,運用同一指標體系對不同地區的城市彈性水平進行比較存在障礙,容易導致不同城市的實際彈性能力水平評價不客觀。應因地制宜地進一步制定不同城市的評價指標,確定相應指標閾值和綜合評價方法。
因此可基于已有的系統型彈性指標,探討不同地域條件下的彈性指標體系,保證指標體系對城市彈性政策的有效影響,使之可操作性加強。
5.3 評價視角的綜合化應進一步強化
作為復雜系統,城市內部各子系統的結構紛繁復雜,各子系統間相互影響,只有從綜合視角來衡量城市發展水平,才能準確反映其彈性發展狀態。
彈性城市專項指標這種“以點帶面”的形式很難全面地去評價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從綜合指標的實踐中可以看出,當下各國的彈性機構組織尤為關注指標的系統性,盡管已經開展了多方面的實踐研究活動,但究竟哪些指標能夠較為準確且全面的反映城市綜合彈性系統,暫時并未達成統一的共識,該類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
彈性城市的評價指標雖然已經從專項指標開始向綜合指標轉型,其綜合性已經在逐步加強,但仍有不足。從綜合化視角展開指標體系的研究將是未來彈性指標研究的重要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