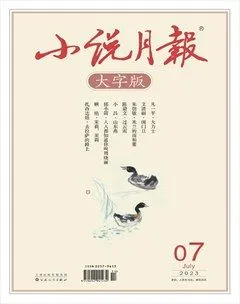去拉薩的路上 On the Way to Lhasa
那時候,甲嘎次仁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有一套出色的狩獵本領。他師傅是貢布(貢布在西藏東南部,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人,憑一把刀跟熊打了一輩子交道。他教會甲嘎次仁一種冒險的捕熊方法。師傅臨死前說過:任何時候都不要冒犯嘉松古莫拉山上那幾只棕熊,它們是嘉松古莫拉山的保護神,惹怒它們會大禍臨頭的。時隔不久,甲嘎次仁卻干了這件蠢事,他上山去惹那些山神了。他想加入公社民兵,書記說他出身不好,父親流落在國外,要加入民兵組織,必須去殺掉嘉松古莫拉山上的棕熊,為民除害,并要他帶回它們的前掌和苦膽。他起先拒絕了,拖了些日子,他終于橫了心,答應了書記的要求。于是,他背上幾天的干糧,腰插一把鋒利的鋼刀,左臂戴上護套,這種護套是用特別的硬藤和牛筋做成,像鋼套般堅硬。手里還拿一根半尺長的粗竹簽,兩頭削尖。他用兩天時間爬上了嘉松古莫拉山的一座側峰,又仔細尋找了兩天,終于發現了棕熊。有兩只,母熊跟剛成年的小公熊在溪邊喝水。它們白天在一起追逐嬉戲,夜晚各自鉆進自己的洞穴里。在一個拂曉,甲嘎次仁悄悄地鉆進了熊穴,這正是它們酣睡的時刻。那只母熊蜷成一團,屁股朝外。他輕輕挨到熊跟前,戴護套握竹簽的左手一下一下去撓它的后腰,它舒適地轉過身,以為是同類鉆進來用嘴在拱自己。當它還沒睜開小眼睛,正張開大嘴打哈欠時,獵人手中堅硬鋒利的竹簽便迅速伸進它嘴里。熊覺得咽喉處一陣刺痛,便狠狠地一咬,竹簽刺進了它的上下腭,張開的嘴再也合不攏了。幾乎同一時刻,他右手的鋼刀直直地捅進熊的心臟,熊喉管呼嚕一聲,全身痙攣,立刻死去。甲嘎次仁的肩膀被垂死的母熊抓破一道,疼得全身冒冷汗。他又鉆進另一洞穴。這時天已蒙蒙發亮,那只剛成年的公熊瞪眼望著鉆進來的獵人。它嗅到了母熊的血腥味。甲嘎次仁嚇傻了,知道只要轉身往外逃走就會立刻被它厲害無比的巴掌按倒在地。熊和人默默地對視著,情緒憤怒到了極點。他忽然揚起刀朝熊扔過去,就在熊閉眼揮掌擋刀的一瞬間,他跳到洞外,飛身躍起抓住預先從崖壁垂下來的皮繩拼命往上攀。崖頂離洞口有七八米高,快爬到頂時,熊在下面抓住了皮繩死命搖晃,他蕩在空中被甩來甩去,又被凸出的巖石撞得頭破血流,幾乎脫了手。他好不容易才有氣無力地爬到頂上,喘著氣看著那頭熊。熊嘴角被飛去的鋼刀劃破一道口子,呼呼地噴著血沫,它瞪著瘋狂的小眼睛,對獵人發出一聲聲吼叫,最后一路朝天嚎叫著向更遠的雪峰那邊逃去。
甲嘎次仁總算用一對前掌和一個熊膽,換來了“為民除害”的獎狀和一支半新的半自動步槍,成為公社基干民兵。他隱瞞了另一只棕熊逃走的事。
也許就因為他干了這件蠢事,才得到報應。幾年后他進了監獄,在里面待了四年,刑期未滿便越獄逃了出來。為了躲避警察追捕,他離開公路,走在一條舊時代從東部康巴地區通往拉薩的古道上。途中有個沉默的男孩總是跟著他,他便收留了這個十二歲的小流浪漢做伴。三天后他發現這孩子原來是啞巴,但有非常靈敏的聽覺,耳朵還能微微扇動。甲嘎次仁叫他普。普就是男孩子的意思。后來一個叫桑的姑娘也跟了甲嘎次仁,他們三人一同前往拉薩。
道路彎曲著向前伸展,周圍是一片荒涼的草地,一側有綿綿群峰。
“已經過了嗒喇山。”甲嘎次仁說,“前面好像有牧場。”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上公路搭車了。”桑說,“他們不會在半路上攔住你。”
“我知道該怎么走。”甲嘎次仁赤裸著上身,短頭發,個頭并不很高但身材十分結實,他老愛瞇起眼。普也跟著他赤裸著上身。
“他們不會從這條路迎上來。”桑又說了句。
“你什么也不懂。”甲嘎次仁提高了聲音,“你這個傻瓜。”
“你說我是傻瓜。”
普閃動著明亮的大眼。他已習慣跟上大人們的步子,還有精力去聽聽他們說話。
“你說我是傻瓜。”過了一會兒,桑又重復道。她那發育得成熟誘人的乳峰在襯衣里一起一伏。她背著簡單的行囊,系在上面的小銅鍋松動了,她氣惱地取下來提在手中。
“別以為沒事,被逮回去的犯人我見得多了。”他回過頭問:“這一路你沒察覺到一點什么嗎?”
“沒有。”
“瞧,你不過是一頭只長奶子不長心計的母驢。”
“咚!”甲嘎次仁后腰上挨了一鍋,打得他踉蹌幾步,剛直起腰,肚子又重重地挨了一下,他痛得捂住肚子跪倒在地。
桑看看四周,一片空曠,連一只野兔也看不見。她蹲在甲嘎次仁身邊摸摸他的臉,說:“你別老罵我。”
“哦咔,你這個羅剎女。哦,你不是羅剎女?打得我屎都快出來了。”他撐起身,捂著肚子走到那邊的草洼地里。
高深的藍天上,只有一只鷹在盤旋。
三個人坐在荒涼寂靜的草地上歇息。周圍沒有燃料,熬不了茶。那天甲嘎次仁帶著普路過桑的家鄉時,她說不上為什么,一下就愛上了這個身上帶著幾道醒目的傷疤的家伙。到晚上他來撥動她家的門閂,他一點也不老練,弄得門閂嘩嘩響。她哥哥提桿槍把他捉住了。當知道這個流浪人也是獵人后,他才高興地用酒款待了他,同時又警告他不許碰自己的妹妹。她哥哥醉沉沉地睡著后,甲嘎次仁就拉著桑跑了……
普炯炯有神的目光向遠方凝視了一會兒。桑也回過頭來順著他的視線望去。
“那上面有人,”桑說,“在山頂上。”
“幾個?”甲嘎次仁并沒有抬頭。
“一個。”
“那就是他了。”
“他是誰?”桑問道。
“我不認識。”
“他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你去問他好了。”
“會不會是警察?”桑又問普,“不是吧。”
普搖搖頭。
“嘿嘿!”他笑笑,“警察。”
“好遠,遠得連打呼哨都聽不見。”桑再一次回頭望去,輕聲說:“但愿不是我哥哥找來了。”
遠處,在連綿群峰中最高的一個山頂上站立著一個人,看上去是一個極小的黑色剪影。
甲嘎次仁知道那人已經在后面跟了兩天,等到第三天就該出現在他面前了。這是東部地區特別是瀾滄江一帶康巴人古老的習俗。
他極其敏銳的感覺里再次嗅到那般甜絲絲的氣味。這氣味已經跟他很久了,他不喜歡它,里面有種不吉祥的東西。
一股清涼的風從荒原上刮過,荒原干干凈凈沒有揚起一點灰塵。風帶著呼呼的聲音和涼爽的氣息一直飄向天的那邊。
傍晚,他們走到一個牧場里歇息下來,牧場有四只黑色牛毛帳篷,幾只牛犢般大小的牧犬一直咆哮不停,它們被鐵鏈拴在帳篷外的木樁上,見了陌生人就狂躁兇猛地把木樁扯得東搖西晃。兩個小女孩跑出來,緊緊夾住了它們的脖子。
甲嘎次仁打聽到一家帳篷里的主人收藏著一些好刀。他鉆了進去,從脖頸上一串綠松石項鏈里取下兩顆,想跟主人換把刀。瘦小的男主人把綠松石放在掌上,湊近火塘邊細細地觀看,他想了想,搖了搖頭,還給甲嘎次仁。甲嘎次仁又取下一顆扔過去,主人這才滿意地收藏在懷里。他從角落的一只牛皮囊里抱出七八把長刀,擲在火塘邊上,由甲嘎次仁自己去挑選。看了這些刀,甲嘎次仁才明白了人家并沒有讓他吃虧。除了一把帶皮鞘的英式步槍的長刺刀以外,其余的刀都很精致、貴重,每把刀都上了油,保護得很好。甲嘎次仁挑了半天,最后撿起一把外形粗劣,看起來又破又舊的腰刀,刀鞘由兩塊厚竹片合在一起,纏了些牛筋和鋼絲,刀把包的是羊皮。他把刀抽出刀鞘,刀身射出清冽的寒光,他用指甲蓋彈彈,聽聲音十分滿意,最后將刀口放在門牙上輕輕刮了刮,握在手中說:“就這把。”
“你到底挑走了我最好的一把。”
“啊哈!你后悔了。”
“不!”牧人笑笑,“不,你眼力好,沒說的。”
為祝賀買賣成交,牧人取出一瓶白酒,咬開蓋放在矮土臺上。他倆相對而坐。牧人說他女兒要出嫁,胸前還缺幾顆綠松石。他邊說邊招呼甲嘎次仁:“來,喝酒。”
“你是獵人?”過了一會兒,牧人又問。
他點點頭。
“看得出,你身上的傷疤。你挑刀的時候,也看得出。你去拉薩手上沒帶貨?”
“我想在拉薩找個工作,在那里住下來。”
“是啊,這年頭,山上沒什么東西可打了,都往拉薩跑。第一次?”
“嗯。”
“離拉薩不遠了,你拿刀干什么?”牧人忽然問了一句,“這邊更沒什么可捕捉的。”
甲嘎次仁只顧喝酒。片刻,他說:“我是從監獄里逃出來的,”
牧人搔了搔額頭,將酒瓶遞過去,甲嘎次仁又灌了幾口。
“怪不得你臉色陰森得像魔鬼。他們在追你嗎?”
“好像是。”
“我可以借你兩匹馬,到拉薩后牽到我親戚家就行。”
“不,不用。”他抹了下嘴,小聲嘀咕,“我鬧不清是誰在追我。”
牧人盯著他,自己仰脖兒灌了幾口酒。“當時,工作組的那個頭對我們哇啦哇啦講話,我不喜歡有人對我哇啦哇啦,就揍了他。判我五年,我沒有說的。”
“咝!”牧人吹了聲口哨,“你拿刀去擋子彈嗎?”
“他會比警察先到。”他撩起帳篷簾子,頭也沒回地說。
“誰?”牧人在帳篷里面問。
“一個仇人。”
甲嘎次仁從牧人的帳篷走出來后,腦子清醒了許多。不遠的地方燃著一堆火,桑在等他,普裹著薄毯蜷臥在火堆旁的草地上。夜晚的空氣透著寒意,天空稀疏地點綴著幾顆星星,起伏的岡坡模糊不清,遠處隱隱地可以望見一條微微泛著白光的河流。牧場十分寂靜。
甲嘎次仁坐在牛糞火堆旁,他只喝了點茶,不想吃桑給他準備的食物。酒喝多了,太陽穴突突直跳。
桑瞅見插在他腰上的刀。她靠攏過去,慢慢抽出刀看了看,用它撥了撥火堆,火塘上頓時飛揚起一陣火星。她把刀扔在他腳下。
“我不喜歡這個。他們人多,還有槍,你的刀沒用。”她憂郁地說。
“桑,聽我說,”他搔搔頭發,“這不是我的錯。我們什么事也不會有。”
“我不信!不信不信!”
“別吵醒了普。”
“第一次見到你時,你不是現在這樣,你唱歌,說笑話,像神仙一樣快活。那時,我真高興。”
“桑!”
“你還是一個人像鷹一樣遠遠地飛吧,我不會拖累你,我也長了一雙腳。嗖!”
甲嘎次仁一拳把她打在草地上躺著。
夜深沉。帳篷那邊的牧犬叫了兩聲,大地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黑暗中傳來他倆的絮絮細語。
“嗯,我信。”桑溫柔地回答。
“這才是我的小夜鶯。”
“啊,親人!”桑抓住他頭發使勁搖晃,同時伸出自己的腦袋,兩個額頭碰得咚咚響。
半夜時,甲嘎次仁醒了過來,他好像感到有一點不對頭。他周圍的黑暗中總像有什么東西埋伏著。四周是那么黑,黑得叫人心里不踏實。他想一定是那個人跟來了,一個陌生的仇人,來替他父親報仇的。
二十多年前,甲嘎次仁的父親殺死了綽號叫“長臉”的盜馬賊頭目岡欽。他父親年輕時曾在巴塘(巴塘,四川省西部與西藏交界的一個縣)一帶做過藏戲藝人,后來加入了岡欽一伙,游蕩在康巴一帶。甲嘎次仁一直沒弄清究竟為了什么,那個岡欽大盜跟父親干了起來。母親從來也不告訴他。父親一夜帶著渾身的血告別妻兒,說暫時要去外面躲避一下。他去了印度再沒回來,從此斷了音信。記得父親往往一邊喝酒一邊唱。甲嘎次仁記住了父親愛唱的那段戲文:“你這把音色優美的胡琴,里外弦調音時你調不準,歡歌起舞你還不奏樂的話,扯下你的皮子作木瓢你可別后悔。”父親出走以后母親帶著他躲到一個偏僻的村莊里定居下來。那時一想起父親他就想唱這段戲文,可剛一出口就被母親捂住嘴。母親怕因此暴露身份招來仇人。到后來,有一天他自己在山上牧羊,張開嘴想唱時,竟唱不出了,不知是忘了詞還是丟了調。
臨近黃昏,天氣變得涼爽,風鋪天蓋地刮來,田野上的天空滾過一卷卷黑色的濃云,遠處傳來低沉的雷聲,甲嘎次仁他們走進了一個村莊,在村口發現了一家小酒店,甲嘎次仁便拉著普興沖沖地闖了進去。
酒店里光線昏暗,蒼蠅繞著屋中間的柱子飛來飛去,幾個剛從江對岸過來的農民在喝酒。甲嘎次仁和普找了個角落坐下。甲嘎次仁很高興,他好久沒進酒店了。他發現掀著門簾的里屋有一個女人正抱著一只粗酒壇往壺里倒酒。不管周圍的人怎么樣看他,他仍操著濃重的昌都口音唱起來:“未經她的邀請,我就來看女主人,她的酒還沒沾唇,我的心已酩酊大醉。”那些喝酒的農民一個個斜視著這位行跡放蕩的流浪人,但沒一個人敢上前跟他交手。女主人滿面春風地提著酒壺出來。她果然楚楚動人,長著一對迷人的酒窩。閑聊時才知道女主人也是康巴人,嫁到這里已經七八年了。
喝了幾杯,普碰碰甲嘎次仁,指指門外,意思是說桑還沒回來,天要下雨了。
“她能找到這兒。”他轉身問女主人,“大姐,我們能在你這兒住一夜嗎?”
“行,能安下你們兄弟倆。”
“還有桑。”
“姑娘?”
“是的。”
“好吧。”她進了里屋。
“聽見了嗎,她說好吧。”他對普說。普戳戳自己的肚子。
“大姐,你這兒有什么吃的?”
“我們只賣酒。”她在里屋回答。
“我弟弟說他餓得直想啃自己的拳頭。”
“餅子行嗎?”
“行啊。”他大聲說。
那幾個農民憤憤地看著這個滿不在乎的外鄉人。甲嘎次仁跟普喝酒,他眼睛盯著昏暗的房梁,一連喝了幾大杯,拉過酒壺又要往杯里倒,普搶過杯子咿呀叫著比畫自己的臉。
“你說我醉了,臉像一塊紅布?”他奪回杯子,把普推到一邊,重新斟滿。“別管我。唉,你這個小魔鬼,肚子里不知藏了多少秘密從不往外倒,這不行,我看見你的眼睛就受不了。你,我,還有桑,我們要在一起過日子。我們再不跟過去那樣,像毛驢一樣活著。”
女主人端了一盤油餅和一碗牛肉炒土豆片出來。
“我這兒還有些白酒,喝嗎?”她問。
“謝謝。”甲嘎次仁握住她軟綿綿的手臂貼在自己額頭上。
昏沉沉的天空驟然之間下起了暴雨。剛剛落下噼噼啪啪幾聲大雨點,很快便嘩嘩地響成一片。外面幾個躲雨的人鉆了進來,站在門口興奮地談論著。
天空抖開一道雪亮的閃電,幾乎同一時刻大家看清有一個人影闖進酒店。一聲“咔嚓”的巨雷,仿佛天要爆炸,地要撕裂,遠處有個女人發出刺耳的尖叫,酒店里的燈泡也隨著雷響忽閃了幾下。
人們驚魂未定,只見一位年輕的康巴漢子,在另一個角落里坐定,自己取了只杯子放在桌上。他面孔有些消瘦,神色剛毅,咄咄逼人。他全身濕淋淋的在滴水,寬邊禮帽翹起的一角帽檐下滴滴答答的水珠流到他的肩頭,白襯衣粘貼在他身上,胸脯前方凸出兩塊緊繃繃的肌肉。額頭垂下一綹暗紅色的絲穗,長睫毛下那雙眼睛透出一種陰沉的冷光。
“大姐,拿酒。”他聲音很輕。屋外的雷雨轟鳴震耳,但他的話每個人都聽得十分真切。
“瞧瞧你這一身水,快把我的酒店淹了。”女主人不得不用很大的聲音壓住外面的雨聲。她殷勤地撩起圍裙替他擦了擦臉上的水珠。他用手擋開,拍拍她發燙的臉頰,又指指空杯子。
甲嘎次仁被那聲響雷震醒,從坐在他對面的普的愕然的眼神里看到,那人終于來了。甲嘎次仁捧著腦袋,沖著普古怪地咧嘴笑了笑。甲嘎次仁這才想起,這半天了,桑去討飯還沒有回來,他知道她能找到這兒,但他不希望她這個時候回來。
“大姐,倒酒。”他望著普說。
“呀呀呀,我真像羊毛捻子一樣忙得團團轉了。大哥,你們都是康巴人,大家應該坐在一起熱鬧一番。來來來。”
“別著急,大姐。”甲嘎次仁并不十分慌亂地說,“我們會很熱鬧的。”
普站起身,繞過桌子挨著甲嘎次仁身邊坐下,那個陌生的康巴人端著酒杯從甲嘎次仁背后走來,在普剛離開的位置上與他面對面坐定。陌生人腳下一雙綠色帆布膠底鞋破爛不堪,露出被水泡得發白的腳趾。他腰間掛著一排子彈帶似的皮囊夾。東部的男人們大都喜歡掛這種東西,可以塞下厚厚的鈔票和一些貴重的小物品。一把漂亮的銀鞘長刀很耀眼地插在腰間。那股氣味就是他身上的呀,甲嘎次仁心想,可是來到對面時卻又嗅不到了。
外面的雨勢不像剛才那樣兇猛了,但仍然密集地傾瀉著。屋檐下的雨點接連不斷,叫人心煩,打不起精神,總是有陣陣困倦的睡意襲上心頭。有幾個等得不耐煩的人抱頭沖進了雨幕。
“這雨下得真痛快。”陌生人喝了一口酒,望著窗外說,他聲音聽起來很柔和。
“酒也不錯,頭道酒。”甲嘎次仁說。他感到陣陣熱氣撲面而來,那是陌生人的身體隔著濕衣服透出來的熱氣。
“我很久沒進酒店了。”
“可別喝醉了。”
普將頭靠在甲嘎次仁的懷里。他愛憐地摟緊那瘦小的肩膀。
“是你弟弟?”陌生人問。
“誰見了都這么說。哪點像?”
“嘴巴,還有腦袋。”
“你眼力不準。”
普眼神孤獨地望著陌生人。
“桑經常揍他屁股。他昨天又挨了她一鍋。”甲嘎次仁又說。
“這里的人不好,”陌生人低下頭,“他們只給了兩勺糌粑就把那姑娘往屋里拖。”
“她不是只小貓。他們會嘗到厲害的。”
“對。”他笑了,“她懂得保護自己。這里的男人……咝——她是你的女人?”陌生人的眼光明亮起來,向門口看去。
“嗨,你們餓了吧?”桑響亮地喊道。她提著盛滿食物的皮口袋,渾身濕淋淋地走進來。她驚訝地看了陌生人一眼,隨后便坐到他身邊,抹去臉上的雨水,把口袋放在桌上,轉過臉向他問候:“辛苦了,大哥。”
陌生人揚揚眉毛,目光溫和。
“我跟你一樣濕。”桑說,“你在跟我們?”
“不是,同路。”
“我還以為是我哥哥追上來了。”她問甲嘎次仁:“他長得不像我哥哥嗎?”
“有點。”
“他也愛這樣。”桑學著陌生人的樣子挑了挑眉毛,“這下我們四個人可以玩牌了,你肯定能贏。”
甲嘎次仁看見桑紅色襯衫的銅扣被扯掉了,胸前被撕破一塊,露出了白色的胸脯,上面還有道被抓破的血印。
“鍋沒砸癟吧?”甲嘎次仁說。
“鍋嗎?”桑晃晃背后,銅鍋還系在行囊上,“用不著,我怕他們的腦袋不禁打。”她挺得意地笑了笑,問陌生人:“你叫什么名字?”
“占堆(占堆,藏語為降伏怨敵的意思)。”
桑看看甲嘎次仁。他仿佛沒聽見,正專心致志地伸出無名指,把一只落進杯子里的蒼蠅拈了出來。
氣氛有些沉默。
“前幾天,在公路卡子上,聽說在堵一個逃犯。”占堆說。
“你說在公路上?”
“他們有你的照片,拿照片對照著來往的人。”
“哦,是這樣。”
“他們好像也知道你走這條路。”
“那你怎么樣,你并不希望我重新被抓回去,是嗎?”
“你是警察?”桑湊近占堆問。
“不,他不是警察。”甲嘎次仁說。
“你不該逃出來。”占堆說。
“為什么?”桑很驚奇,“他是人,不是關在圈里的羊。他什么都告訴我了,因為揍了工作組幾拳,就要關五年?哦哇!”
“還有,別的那些,更早以前的呢?”占堆問她。
桑看看甲嘎次仁。他抬眼惡狠狠地望著占堆,半晌,才慢聲慢氣地說:“她不應該知道得更多,那都是過去的事,咱們誰也沒見過,不是嗎?”
“沒見過,這不錯。”占堆說。
女主人端上了茶、酒和牛肉,還有一小碟辣椒水。
“我能在這里住一夜嗎?”占堆問。
“我丈夫是個膽小鬼,幸好他不在。”女主人說,“跟民工隊去縣里修電站,半個月才回來一次。現在就我一個。”
普不明白這個臉上泛著紅暈的女人為什么喋喋不休。
“能住下。”女主人轉身進了屋。
吃到一半,桑忽然歪過頭問占堆:“他以前給你惹過麻煩?”
“桑!”甲嘎次仁喝住她,“我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你騙我。”
“他說得對,”占堆只顧低頭吃東西,“過去的事,你不應該知道很多。”
桑默默望著專心吃喝的陌生人。普坐在另一側,他望著夜幕降臨的窗外。
大家都不說話,只有單調的嚼食物的聲音和外面淅淅的雨聲。
女主人抱來一些薄墊毯給他們,還有一條破舊的羊毛被。他們各自找一個角落鋪在地上。這一夜,大家心事重重,再也沒說一句話。看來,占堆拒絕了女主人的暗示,他已經進入夢鄉,發出輕微的鼾聲。
甲嘎次仁感到一陣迷惘,這就是那個岡欽的兒子嗎?看起來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壯實。他到底什么時候動手?噢,這當然是他的事。
天快亮時,他做了個噩夢,一雙手從地縫里伸出來求救,一個聲音在喊叫:“別殺呀,你真蠢!”那雙手像是父親的,又像是占堆的,它又有痛感,原來是自己的。等看清時,手變得毛茸茸的,又粗又大。
這是一個月牙形的山口,山頂光禿禿的全是些巨大渾圓的石頭,山口下面一點有座寺廟廢墟,旁邊有幾棵枯死的干樹。能看見山腳下一條細長彎曲的公路消失在那邊的山彎后面。公路上不時有一團團移動的灰塵,那是汽車在行駛。從山口只需要三四個時辰就能到達公路。
山腳下昏暗的陰影悄悄爬上來,又是一個金燦燦的黃昏,夕陽就要隱落到山后面去了。
占堆獨自躺在一塊石頭上,他仰面朝天,拉下禮帽遮蓋住自己的眼睛。這個長期流浪在異鄉的年輕人,照例掏出那只小錄音機貼在耳邊,除了甲嘎次仁和桑熟悉的東部民歌外,占堆還愛放一個女人唱的歌,既無伴奏也無伴唱,音色喑啞卻十分動情。占堆告訴桑唱歌的這人是他的情人。這會兒里面的電池快沒電了,放出的歌飄忽不定,走調兒,占堆就關了機子。
占堆用帽子蓋著臉,像是睡著了。半晌,他才說:“他們找到你了,那些警察。”
甲嘎次仁在搭灶,他放下石頭,站起身慢慢巡視著北方。
“不可能。”他說。
“下午的時候,陽光照在我臉上,怪燙的,”占堆說,“我一回頭就看見了。不是在我們后面,是在對面山上。閃了一下,是鏡子反光的那種亮。”
“望遠鏡。”
“不過,他們最快也得明天中午趕到這兒。他們被江擋住了,這一帶沒渡口。”
甲嘎次仁哼了幾聲,聳聳肩,又繼續干自己的活兒。普攙扶著桑走來。桑的腳扭了,她說這一下下山可要受罪了。
“我坐在那兒揉腳的時候,好像發現山坡那邊有個人影,翻過去又看不見了。”桑歇了會兒,想起了什么。
占堆舔舔干裂的嘴唇,勾起小拇指在眼皮底下搔了搔,臉上顯出幾分疑慮。
甲嘎次仁手中的柴差點沒朝占堆劈頭蓋臉砸過去。他咬咬牙,壓住心中的怒火。
“也許是我剛才看花了眼,我覺得汗水糊住了眼睛。”桑說,她看柴火只剩了一點,向甲嘎次仁要過刀,撐著扭傷的腳去廢墟后面打柴火。普也跟了過去。
“叫他出來吧,”甲嘎次仁憤憤地說,“這里有熱茶。”
“誰?”
“你的朋友。”
“朋友?”占堆莫名其妙,但立刻又好像明白過來,“你疑心太重。”
“桑看見了。”
“她說看花了眼,你聽見的。”
“我一點不在乎。”他勾起下巴,瞇著眼朝占堆兇狠地笑笑。
“我只是不想讓桑看見。別的,我才不在乎。”
“她不會知道,她是個好姑娘,這是我們男人的事,不是嗎?”
“所以,我一點不在乎。”
桑和普抱著大捆的干柴走來。她跪在灶前添了些柴。她知道剛才這兩個神情冷漠的男人說了些什么。她答應了甲嘎次仁,所以什么也不再問了。火焰旺盛起來,耀眼的紅光照亮了四周,熱浪烤著他們的臉,火燎燎地,使他們感到了一種朦朧的醉意。
甲嘎次仁盤腿而坐,摸出那副像破布片般軟綿綿的撲克牌,熟練地唰唰抽洗幾下放在地上。
“正好四個,玩幾把。”
“怎么玩?”占堆問。
“我教你,很簡單。”
“我想我能學會。”占堆似乎很有興趣。他將牌撮在手中,笨拙地一張張握成了扇形。他第一張牌就出錯了。
這氣味越來越不對,甜絲絲的就像嘴里含了血一樣。甲嘎次仁將贏過來的牌放在自己腿下。他憤然想到:我還沒殺過人哪,我吃的苦頭夠多了,這是在逼我這么干。直到現在他也沒弄清是誰更跟他過不去。
“殺掉!”他甩下一張牌,大聲叫道。
“嘿嘿!”桑得意地亮出一張牌。她又湊過身去看看占堆的牌,說:“哦,你贏了。”
“是啊。”他還是沒搞懂該怎么玩。
甲嘎次仁把自己手中最后一張牌湊到占堆鼻尖底下,又湊給桑。
“哎么么。”桑無可奈何地對占堆伸出舌頭,“還是他大,我們輸了。”
“是嗎?”
“這是大魔王,”她對占堆說,“現在該誰受罰?”
普捂住自己的鼻子。
“你嗎?好吧,我替你,我喜歡受罰。”桑轉過去面向甲嘎次仁。甲嘎次仁往后挪了一段距離,從一只小布袋里掏出幾顆干胡豆。
“怎么個罰?”占堆不明白。
“他要把豆子彈進我嘴里。”桑解釋道,“我喜歡這樣。”
她張開嘴,仰天閉了眼,長長的睫毛不安地顫動。甲嘎次仁揀起一顆豆子,用大拇指把豆子彈了出去,豆子準確地飛進了桑的嘴里,大概一直飛進了食道。
“啊!”她瞪圓了眼緊張地憋了口氣,把卡在食道里的豆子咽了下去,忽然大笑起來,“天哪,你會殺死我的!”
桑跳起身撲過去,盡情地勾住甲嘎次仁的脖子,兩人在地上咯咯笑著滾成一團。普偷偷望了占堆一眼,他驚訝了:占堆坐在旁邊,嘴旁綻出了一絲甜甜的笑意。
天黑了,沒多久,除了甲嘎次仁,大家都和衣躺在溫暖的灶火邊。他捧起桑的頭枕放在自己腿上,一個人坐著,低下頭默默地看著桑。她一聲不吭地看著他的眼睛,又看著滿天的繁星。他們長久地互相凝視著。
“你頭發長了。”許久,桑輕聲說,并伸手摸摸他的頭發。
“長得太慢。”他說。
“你要留得長長的。我早就為你準備了一副穗子。”她從懷里摸出一副紅色的絲穗。
“你先放好。”
“嗯,到時我替你編上。”她說。
桑終于明白,有些事情只屬于男人們,她無法知道,更無法去改變。
“我真困。”她含著一絲凄涼的微笑慢慢合上了眼皮。過了許久,才發出均勻的呼吸聲。甲嘎次仁將她的頭從自己腿上輕輕地移到一邊。他站起身,長長吐出一口氣。“這下,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對自己說。
一彎新月從山背后升起。他往灶里又添了些干柴,起身向黑暗走去。離開了灶火,在深夜的寒氣中他不由得打了個寒戰。他來到寺廟廢墟后面一塊斜坡空地上,那里立著一塊兩人多高的大圓石,它往下傾斜著,似乎隨時都會滾下山去。他背靠圓石一動不動地站著,清新的空氣使他頭腦格外清醒。遠山近嶺黑黝黝的看不清,什么地方閃爍著一群極小的黃色星光,夜色溫柔。他想起家鄉一句古老的話:就在今夜呀,正是他們情奔的好時機。
那甜甜的氣味彌漫在夜空里,甲嘎次仁心里忽然恐懼地顫動了。
他來了,一步步走上來,在甲嘎次仁下面兩步遠的地方站住。禮帽朝前壓得很低,像第一次出現在甲嘎次仁眼前的樣子,雙腿叉開,兩手按在腰刀上。
“你要講很長嗎?”甲嘎次仁問。
占堆像石頭般紋絲不動。黑夜的空氣漸漸凝重了。甲嘎次仁幾乎不相信他耳朵聽見的故事,但是占堆一字一句,十分認真地講述著。
那個剛毅的女人終于把辛辛苦苦養大的兩只鷹從手中放了出來。兄弟倆外出三年又一無所獲地回去。母親重新把他們趕出家門,找不到他們父親的仇人就再別回來見她。兄弟倆十分苦惱,仇人沒找到,卻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愛情。哥哥說他不想再過那種流浪的生活,那姑娘教會了他開拖拉機。弟弟苦苦請求,哥哥不肯,他要到那姑娘身邊去,她叫仁增旺姆。弟弟扯住他的衣角,跪下請求他別這樣。他竟然對弟弟說:“夠了,即使找到他我也不想和他拼刀子,我又不認識他。”弟弟再也不能忍受,跳起來把哥哥打翻在地。兄弟倆分手了,一個去找自己的情人,一個去找父親的仇人……
該死的弟弟。甲嘎次仁閉上眼,手中握緊了腰刀。
“我和弟弟分手不到一個月,”占堆說,“我沒想到這么快就碰上了你。”
“呸,你這只狼。”
新月下的朦朧中,甲嘎次仁看見占堆的臉忽然間扭曲得變了形,他飛快地抽出了青光閃亮的鋼刀指向甲嘎次仁。這一切來得那么突然,甲嘎次仁傻呆呆地站在那兒,他分明看見占堆驚駭的大眼閃著絕望的兇光。他像一只準備與蛇搏斗的公貓弓起了身體,喉嚨里發出古怪的聲音:“站著,別動,別動。”
甲嘎次仁拔出刀時,占堆喊叫一聲朝他頭頂刺來。他舉刀剛要去擋,猛然感到一團沉重的黑色物體向他壓來,刀被打飛出去,接著肩膀一陣撕裂的劇痛。他就地一滾,避開了占堆沖過來的身體。媽的,到底還是有一個躲在我背后。他感到身體已經受了重傷。突然,他摸到了掉在地上的刀,他死死抓住中間的一段刀刃,刃口深深割進了他的掌心。他把刀舉過頭頂奮力揮舞,刀尖不知戳進到什么地方去了,進得很深,一股灼燙黏手的熱血立刻噴到他手上,又流到胳膊肘邊。他清楚地看見占堆的一只耳朵在脖子上甩來甩去。
只有天上的神靈知道,這里在進行一場慘絕人寰的廝殺,但是,神靈在沉默。
普跳起來,揉揉眼皮。他聞到一股焦臭的煳味,原來是自己蓋在身上的破衣服的一角被炭火燒著了。他伸出腳胡亂地踢了幾下,把火星蹍滅后,看看四周,發現少了兩個男人。他驚慌失措地原地轉著圈兒,巡視著黑夜里的曠野,終于呀呀地叫喊著滿山遍野地亂跑起來。
甲嘎次仁變成了血人,衣服被撕成了縷縷碎片,連著幾條從骨頭上脫離下來的肉。緊握刀口的指關節已經僵死,刀口已經割進了骨髓,再也松不開了。他大口大口喘著氣,肚子右側流出的一堆腸子使身體往下墜。
萬籟無聲。月亮被一塊移動的浮云遮住。遠處傳來汽車的轟鳴,一定是趕早的司機上路了,聽聲音是往拉薩方向去的,可過了一會兒那聲音又消失了。
離甲嘎次仁不遠的一處高地上,躺著一個黑糊糊的龐然大物。原來自從那只公熊挨了獵人的一刀逃離之后,便永遠記住了獵人身上的氣味。十年來,它懷著強烈、持久的報復心理默默地嗅尋追蹤。它總算報了仇。此刻,它那僵硬的身軀像是一座黑色的墳墓,靜靜地聳立在山岡上面。
“喂!朋友。”甲嘎次仁嘶啞地喊了一聲。
“我不行了。”聲音離得不遠,但什么也看不見。過了一會兒,那邊又響起聲音:“我沒想到,它,一下子沖來了。”
“本來,沒你的事。它是來找我的。”甲嘎次仁每說一句話,嘴里都噴出一些血泡,那氣味果然就是這種嘴里含著血的甜絲絲的感覺。
“朋友。”他又叫一聲,“不能死,你的故事還沒講完。”
黑暗中,傳過來一陣斷斷續續的低吟:
“完了。仁增旺姆還在等我,我一點也動不了。”
甲嘎次仁慢慢地朝前摸去,空空的,但他知道占堆離他不會很遠。他忽然想起父親留在他腦海里的那段唱腔。他知道他現在能唱出來了,就使盡最后一點力氣,將身子翻過來仰面躺著,咽下一口血水。面對著幽深凄寂的夜空,一首蒼涼高亢的曲子由低到高響了起來:“哎——你這把音色優美的胡琴……”
占堆也用一種纖弱柔和的聲音為他伴唱起來:“嘿——哎——”
“里外弦調聲時你不調,歡歌起舞你還不奏的話……”
“嘿——哎——”
“等扯下你皮子做木瓢,你可別后悔。”
“嘿——哎。”伴唱驟然頓住。一陣長長的靜默。月亮重新浮現出來……
普順著聲音找去。月光下,他看到一幅終生難忘的景象:占堆死了,他下半身血肉模糊。半個臉和一只耳朵被扯了下來,胸前露出了幾根白骨。甲嘎次仁爬過去跟他頭對頭躺著,右手還握著那把刀。
“啊!啊!”普撲通一下跪在甲嘎次仁身邊。
甲嘎次仁頭已經不能轉動,只是睜著眼,胸脯在平靜地起伏。他斜視了普一眼,用一絲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你還是……做啞巴的好。”
當天下午,前來追捕的三個警察疲憊不堪地趕到了。岡坡上躺著一只黑色的死熊。地上一大片凝固的血中散落著一些碎布片、頭發和一只摔破的袖珍錄音機。他們驚愕了。這時,天上盤旋著一大群黑色的蒼鷹。他們爬到山口邊的一塊石頭上,舉起望遠鏡朝下望去。
兩個緩緩向下蠕動的人影拖著兩具尸體。坡道陡峭,碎石松散,每走一步腳下就蹬掉一些碎石,嘩嘩朝山底滾去。
整個山谷只聽見碎石滾動的嘩嘩聲。
【作者簡介】扎西達娃,著有《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等小說,是20世紀中國魔幻現實主義、先鋒小說的代表作家,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