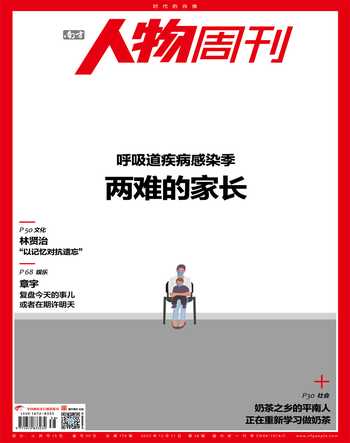“兒科荒”背后人手緊待遇低,老難題探尋新解法

2023年12月2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關情況。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介紹,當前,國家衛生健康委會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疾控局持續開展冬季呼吸道疾病監測和研判,對做好醫療資源調劑、優化就醫流程、發揮中醫藥作用等工作進行部署。
根據監測,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均由已知病原體引起,都有相應的成熟治療手段,未發現新病毒或細菌導致的新發傳染病。
多病原體疊加高發的特征使得這輪呼吸道疾病感染潮成為新冠疫情后醫療系統面臨的又一次重大考驗,除了繼續落實和完善分級診療制度、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對一般性感染的診療能力和重癥識別轉診效率,兒科醫療資源長期短缺的老難題再次引發廣泛關注。
12月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關于指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做好冬春季呼吸道疾病健康服務有關工作的通知》,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兒科診療服務提出了多項要求:各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全面向兒童開放,不得拒診;加強綜合醫院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支持力度;每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至少有1名全科醫生完成兒科專病診治工作的培訓,至少2名護士完成兒科治療的培訓,加快提升基層開展兒科和應對冬春季呼吸道疾病的診療服務能力。
“免疫落差”?
進入11月,北京各醫院兒科診室一直處于爆滿狀態,大興醫院、友誼醫院的門急診候診時長甚至達到24小時以上,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的輸液中心叫到近兩千號。
北京某綜合性大學醫院的兒科醫生戴佳每天的接診量都在120人次以上,即使是夜間急診,整個門急診的接診量也是2019年時的兩三倍,由于看病的患者過多,科室每天會輪流派一名病房值班的醫生來支援門診。
北京以外,天津、遼寧、上海、廣東等多地醫院的兒科病區也在滿負荷運轉。廣東省婦幼保健院番禺院區日均急診量達到八百余人,超過了2023年3月廣州的春季流感高峰。中山大學附屬醫院各院區門急診接待量爆滿,排隊等候幾個小時是常態,住院床位也預約了幾十張,等著空出來收治肺炎的患兒。但總體上,廣州的醫院比北京從容許多,至少在候診大廳里,每個人都有座位和輸液架。
每年春季和冬季流感易發的時期,兒科診室都會有問診的高峰期,但今年這一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持續的時間尤為漫長。廣州某三甲醫院的兒科住院醫生安楊幾個月來都在高強度地工作,“從八九月份開始,耐藥的支原體感染一直存在,中間緩過一陣,但是乙流和甲流又開始了,而且有可能疊加,癥狀還會比較重一些。”
安楊管理的病房常年處于飽和狀態,如果發現有必要住院治療的患兒,門急診的醫生會先詢問病房有無床位,若暫時騰不出來,醫生會給予急診輸液和對癥治療,同時建議去其他醫院咨詢床位住院治療。實際上大多數來到門急診的患兒,經醫生評估癥狀較輕的,可以口服藥物治療并觀察療效。病情嚴重一些的患兒則考慮用使用靜脈給藥。安楊和同事們發現,這一輪肺炎支原體的特點之一是耐藥率高,“兒科治療常用的阿奇霉素,口服效果不好,靜脈效果也大不如前。”
“還是會用阿奇霉素,兒科使用阿奇霉素時間長,臨床觀察藥物作用及不良反應的經驗多,如果濫用喹諾酮類、四環素類藥物,可能更得不償失。”安楊說,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23年版《兒童肺炎支原體肺炎診療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除了阿奇霉素代表的大環內酯類抗菌藥物,還推薦了新型四環素類和喹諾酮類,但也反復強調了它們的副作用:新型四環素類可能影響牙釉質發育和造成牙齒黃染,8歲以下兒童不建議使用;喹諾酮類可能影響軟骨發育和增加肌腱斷裂的風險,18歲以下兒童不建議使用。“現在可以做肺炎支原體部分耐藥基因檢測,出結果快,但一般還是會先用阿奇霉素觀察療效,發現存在臨床耐藥現象結合耐藥基因檢測情況決定是否選用其他抗生素治療。”
倫敦大學學院計算生物學家在給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的聲明中說,為減緩新冠疫情的傳播而實施的封控措施阻止了季節性病原體的傳播,使人們減少了對這些微生物建立免疫力的機會。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及了類似的說法——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造成了免疫落差(immunitygap),疫情期間其他病毒和細菌的傳播急劇減少,或導致一些兒童對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其他引起感冒的病毒等缺乏免疫防御能力。免疫落差是長期低接觸某種特定病原體而導致的保護性免疫力不足,這使得更大比例的人口易感染該疾病。
上述說法仍存在爭議,安楊對此也不置可否,他認為這與流行的微生物本身有關,每隔幾年會有一次大流行年,“也許今年的支原體比較特殊。”他自身感受到的特殊之處是,支原體肺炎易發于5至14歲的兒童,但今年各年齡段感染的人都有,他之前也疑似感染,持續咳嗽兩三周,自己吃了一周藥,使用了霧化機。他沒有確診,因為沒時間去做檢查。

“大醫院迷信”
理想情況下,三甲醫院不應該是肺炎病人看病的首選,“先去社區醫院,口服抗生素,一部分人慢慢好,一部分人好不了,再去選擇大醫院,經過門診治療,再篩選出重癥患者。”但兒科的分級診療普遍更難,安楊幾乎沒有看到過拿著社區醫院就診記錄來看診的患者。
“其實只要按指南來,用藥都差不多,就看他們能不能及時判斷重癥。”只要不延誤重癥病情的判斷,安楊覺得社區醫院的治療和三甲醫院區別不大,“重癥表現得比較明顯,血壓低、氣促、胸片有明顯的白病灶。”肺炎支原體感染的重癥率較低,在人流密集的中山醫院附屬第三醫院,每天轉去ICU(重癥加強護理病房)的重癥患者是1至2名。
兒科的“大醫院迷信”一部分源于現實情況,兒科高度依賴臨床經驗,看診思路和成人差別大,家長會更信賴接診量更大的醫院;其次,大醫院的醫療資源更加充足,有些基層醫院條件受限,沒有后夜診、沒法做檢測、沒法拍片。“復雜一些的病,當地二級醫院看完會直接推薦給我們。”安楊說,久而久之,很多人會跳過一二級醫院,直奔三級醫院。
廣東省婦幼保健院番禺院區新生兒外科主任醫師朱小春認為,家長對孩子的重視也是他們選擇大醫院的原因。不久前,朱小春的一位朋友的孩子高燒不退,已經在當地縣醫院看了最好的兒科醫生,并致電朱小春咨詢病情,仍然不放心,還要驅車幾百公里專程來省婦幼保健院看病。花了幾千塊錢做病原微生物宏基因組檢測(mNGS),測出來感染了一個很少見的支原體,“其實意義不大,還是支原體感染,阿奇霉素耐藥后,換用了四環素,燒退了一些。”
隨后,朋友又提出“孩子精神狀態不好”,先后看過呼吸科和神經內科,神經內科醫生建議他先停藥幾天,再根據精神狀態考慮是否做腰椎穿刺。朋友停藥三天,帶孩子去長隆歡樂世界玩了一圈,告訴朱小春“孩子好了”。朱小春以此總結:“很多時候是家長的緊張導致了醫生被動性地過度治療。如果醫生不這樣做,家長又會怪你。”

小兒呼吸科醫生高潔遇到過不少一來就要求驗血的家長,她反對過度檢測,患者的癥狀如果非常典型,會直接進行經驗性的治療,節省時間。但她也理解家長的訴求,“他會覺得已經排了8個小時的隊了,要檢查一下,如果不做就回去了,排隊這么的長時間就是沉沒成本。如果是我,我拿一個檢驗結果心里也有底。”
安楊發現這一輪肺炎支原體感染,最大的特點是“家長普遍比較焦急”,“住院前很著急,住了兩天又急著出院,有一點好轉就在問什么時候能出院,小孩要上學呀,落了課程了,落了期中考了。尤其是剛上小學或者剛上初一的孩子,家長特別擔心缺課時間久,孩子不僅學業跟不上,還難以融入班集體。”
根據指南,肺炎的療程是7至14天,但即便是重癥住院的孩子,因為醫院床位緊張,也不會住滿一個療程。可是這不代表孩子能去上學,“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后期,氣道會處于比較敏感的階段,很容易再次受到其他細菌和病毒的感染。”對于這一輪感染高峰,安楊的建議除了勤洗手、戴口罩等公共衛生常識以外,還有“不要那么著急去上學”。
兒科忙是常態
這波感染潮的持續對門急診值班的兒科醫生造成了直接壓力,但對于剛工作三年、還在擔任住院醫師的安楊來說,影響并不大,“三甲醫院的兒科病房普遍都是飽和的工作狀態,什么時候都沒有(空)床,不是這個病,就是那個病,總有一個要收治進來。”
安楊選擇兒科出于很現實的原因,“考研分數不高,找個好就業的專業先上”。兒科醫生緊缺是常態,無論大醫院還是基層醫院都缺。《2015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兒科醫生總數從10.5萬下降到10萬,平均每1000名兒童只有0.43位兒科醫生,與全國平均每千人配備2.06名醫師的水平相比相距甚遠,因此兒科在招生和就業上條件更為寬松。
但兒科的綜合吸引力仍然不強,安楊直到工作后,才深刻體會到為什么師兄師姐們勸大家別讀兒科。對于新人醫生來說,兒科要學習和熟記的內容太多,其他醫生只需要精通一部分內容,兒科則要求再細分,而且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器官生長發育程度不同、生理特點不同,導致診斷指標和用藥劑量都不一樣,“很多藥物沒有明確的兒童劑量,大多數還是經驗性地用藥。”
安楊還需要從零開始學習如何哄孩子,“一開始跟小孩互動,很難做出比較幼稚的行為,后來慢慢好一些,有的孩子比較喜歡搞怪的聲音,要用小孩的語氣跟他們解釋問題。”面對實在聽不進話的孩子,只能在他哭鬧的情況下看診,安楊現在對哭鬧的忍受度有了大幅提高,“在我旁邊隨便鬧,我沒感覺。”

有時候患兒的配合度會直接影響到診療。安楊會趁患兒睡著的時候偷摸去做肝脾觸診,因為他們哭鬧的時候整個腹壁是硬的,“根本沒法摸”。
做一些更復雜的檢查前會給患兒使用鎮靜藥,但檢驗醫生不愿意承擔用藥的風險,需要安楊帶著鎮靜藥陪患兒做檢查——排隊、檢查、等結果,耗費大量的時間,而病房里還有其他患兒的問題需要處理,工作時間無限延長。每周,安楊只有半天到一天的時間休息。
在安楊所在的兒科科室,按照工作職責劃分,一個主治醫生只搭檔1-2個住院醫生,要管十幾張床位。缺人是顯而易見的,但醫院沒有招人的打算,全靠“規培生”支援——新進入醫療崗位的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醫學類專業畢業生都要接受3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畢業生規培期間收入不高,是醫院低成本緩解人手不足的主要方式。
盡管工作時間不長,安楊已經清楚地知道兒科難以為醫院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醫院也得考慮收支,有什么動力招兒科醫生呢?”
“如果能夠選擇,怎么選?”
“醫生就是練出來的,苦出來的。”朱小春在廣東省婦幼保健院已經是主任醫師,但他依然非常忙碌,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的下午,他看完了所有來掛號的病人,但還是不斷地被想要加號的病人打斷訪談。有位家長帶著患兒下午4點后趕去影像科,影像科已經在做收尾工作,護士讓他明天再做檢查。朱小春聽說以后,打電話跟影像科協調,“患兒是外地的,來一趟不容易,能幫一把是一把。”
通常一個半日的看診有36個號,朱小春最多時能加到45個,“能看就給人家看。”上午11:45掛號系統關閉,他還繼續加,一直看到13:30,掛不上號的病人不算工作量。
兒科是“啞科”,小孩無法準確描述他的生理情況,加大了兒科看診的難度,醫生要有經驗,也要有耐心。朱小春每次出診都要看好幾個“肚子疼”的患兒,小孩說不清楚哪兒疼,就說肚子疼,到處都疼,“你要精準地找到病因,如果是手術并發癥,要當機立斷地送到手術臺上,不然可能出現嚴重的并發癥。有的時候診斷過程中還有很多推理的部分。”

一個喊肚子疼的孩子說他被兩個同學打了一拳,朱小春首先讓他做檢查,看是不是打傷了內臟,但并未發現明顯的問題。細問之下,發現孩子有點腹瀉,最終排除了其他原因,基本斷定是因為腹瀉所以肚子疼。“不能局限在他的話里,有時候就是湊巧。”
兒科每年會出現周期性的問診量爆滿,內科是季節性流感高峰,外科就是暑假——每年夏天,來泌尿外科割包皮的患兒擠滿了兒科診室。作為兒外科的主任,朱小春需要平衡科室的工作強度,2022年他從心腎外科調了一個主治醫生去支援泌尿外科,今年他實在找不到人手了。有的醫生要下鄉義診,要去轉運中心值班,院里沒有招新人,他只能排上自己。
“全國只有八千多名小兒外科醫生。”朱小春說,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兒科待遇太差了。11月下旬,他去縣城義診,一家醫院的外科醫師主任說他們院的小兒外科醫生不愿意干了,“小醫院外科都在一層樓辦公,乳腺外科挨著小兒外科,乳腺外科多輕松啊,風險小,績效高。如果治療同樣數量的病人,小兒外科會累死,辛苦程度的差別一目了然,但績效是差不多的。如果能夠做選擇,怎么選?”
探尋新解法
“兒科荒”由來已久,1998年醫學院的本科教育取消了兒科專業,代之以臨床醫學專業,到研究生階段才細分兒科專業。1999年,全國兒科專業停止本科招生,直至“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2016年才恢復兒科學專業本科招生。
2022年,國家衛健委印發關于貫徹2021-2030年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的實施方案。方案指出,到2030年,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執業(助理)醫生要達到1.12名、床位增至3.17張。
一名受訪醫生認為,為了吸引更多人選擇兒科,已經降低兒科的考研和執業醫師考試分數,醫院對于兒科醫務人員的招聘條件也比成人科室要寬松,但實際效果并不好,兒科仍然缺人,因為問題的癥結并未被解決。“像兒科和急診科這種又累又苦、錢又少的科室,如果要吸引人才、扭轉人才斷層的局面,最直接的刺激肯定就是加強對科室的資源投入,提高科室醫務人員的收入。”
在“兒科荒”的背景下緩解“兒科看病難”,分級診療的推廣尤為重要。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發布,明確了分級診療的概念,提出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模式。2020年6月開始實施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30條再次強調,“國家推進基本醫療服務實行分級診療制度,引導非急診患者首先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
根據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近五年來,各級醫院的診療量占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的45%左右,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占50%左右,其中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的診療量在24%左右,這一比例與發達國家80%以上的就診量發生在醫院外醫療機構相比仍有距離。
為了促進分級診療的推行,大醫院會與基層醫院形成公立醫療機構聯合體。朱小春介紹,廣東省婦幼保健院與一百多家單位建立了醫聯體,給予技術支持和醫療資源補充,“我們會下鄉鎮給醫聯體的專科聯盟講課,通過線上的方式遠程會診,讓輕癥病人留在基層,也讓必須轉診的病人及時轉診。在我們的病人做完手術穩定后,也可以轉到基層醫院,實現雙向轉診。”
全科醫生吳天龍在深圳羅湖區文華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社康”)工作了13年,他認為社康與上級醫院的聯動是一種良性的雙向互動,“我們有機會去上級醫院做亞專長的培訓,例如去深圳的兒童醫院三個月脫產學習,學常見疾病處理。同時我們也是深圳人民醫院的規培基地,醫學院學生在我們社康泡上半年,能學習到兒科接診和很多公共衛生服務的技能。”
文華社康有12名醫生,都是全科,吳天龍感覺基本能滿足社區需要,“現在很多社區居民都會首選在社康看病,不會動輒跑到大醫院。門診量比以前翻好幾番。”往常會看基礎性的呼吸道疾病也是社康醫生的必備技能。吳天龍一天要看六七十個病人,平均8到10分鐘一個病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兒童,絕大多數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深圳社康的分級診療走在全國前列,在2022年12月的發熱高峰中,社康發熱診室“扛下”65%的診療量。為了調動老百姓去社康中心的積極性,深圳市要求基本醫療保險二檔、三檔參保人,應當選定本市一家社康中心作為門診就醫的定點醫療機構,并不斷致力于醫院、公共衛生機構與社康的信息協同,實現檢驗結果互認、醫療資源互通。
最關鍵的還是“理順內部的利益機制”,深圳市衛健委副主任李創曾總結,“讓大醫院的醫生有動力下轉病人;社康中心的醫生有動力上轉病人。病人最終能自覺地選擇社康中心。最終達到這一目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安楊、戴佳為化名。感謝陳洋、張明萌為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