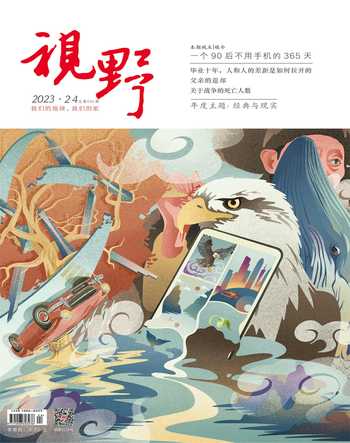使我們變得疏離的,從來不是網絡
[英]奧利維婭·萊恩

“在這個被預先構造出來的世界上,將私人事物轉化為公共事物的行為能夠產生強烈的反響。”沃納洛維奇曾這樣說過。
每天醒來時,在我的眼睛還沒完全睜開前,我就會把手提電腦拽到床上,立刻登錄Twitter,它是我每天看到的第一樣和最后一樣東西。這個不斷滾動的頁面中的大部分信息來自陌生人、機構和朋友。
在這個轉瞬即逝的社群里,我是一個沒有實體的、不斷地變化著的存在。我在源源不絕的消息中瀏覽著國內和市內的動態:隱形眼鏡藥水、書的封面、一則死訊、抗議的圖片、藝術活動開幕、關于德里達的笑話、馬其頓森林里的難民、“恥辱”的話題標簽、“懶惰”的話題標簽、氣候變化、丟失的圍巾。
這一連串的信息洪流、態度和觀點在某些日子里(可能是大多數日子里)比現實生活更多地吸引了我們的關注。
而Twitter只是通往互聯網這個無盡之城的一扇門。一天又一天,時間在點擊鼠標中過去了,大量的信息奪去了我的注意力,我就像是一個不在場的、熱心的見證人一樣看著這個世界,像背向窗戶的夏洛特小姐一樣看著出現在她的魔法鏡子里的真實世界的倒影。
過去,在那個已經完結了的紙書和報紙的世紀里,我也曾習慣于把自己埋進一本書里的閱讀方式,而現在的我正盯著屏幕,盯著這個令我全神貫注的銀色的愛侶。
我像是一個永遠在監視著一切的間諜,像是又一次回到了青春期,一頭扎進沉迷的深淵里,踩著搖動的洶涌的水波和變幻的碎浪向前移動。
我閱讀著那些關于囤積、折磨、真實的犯罪和國家的不公的事情,閱讀著聊天室里人們用有拼寫錯誤的對話討論著的瑞凡·菲尼克斯死后薩曼莎·馬希斯所經歷的事情,抱歉這聽起來有點傲慢,可你確定你看過這個采訪了嗎?
縱身躍入,隨波逐流,由無止境的鏈接構成的迷幻黑洞,隨著點擊的動作,我越來越深地陷入到過去,跌跌撞撞地踏進當下的恐怖里。
科特妮·洛芙和科特·柯本在一片沙灘上舉辦的婚禮,沙子上的一個血淋淋的孩子的尸體:這些會引發各種情緒的圖片將無意義的、驚駭的和令人渴望的意象全都重疊在了一起。
我想要什么?我在尋找什么?無數個小時過去了,我都做了些什么?相互矛盾的事情。
我想要知道外面發生的一切。我想尋求刺激和鼓舞,想與世界保持聯系,可我又想保留我的隱私和私人空間。我想要不斷地點擊點擊再點擊,直到我的突觸神經鍵爆炸,直到我被過剩的信息淹沒。我想要用數據和彩色像素自我催眠,讓自己變得空白,克服所有日益加劇的關于“我究竟是誰”的焦慮感,徹底抹去我的感受。
同時,我又想保持清醒,參與到與政治和社會相關的問題中去。
此外,我還想表明自己的存在,列出我的興趣和異議,告知世界我還在這里用我的手指思考著,即便我幾乎已經喪失了語言這門藝術。
我想要去看,也想要被看見,而出于某種原因,透過扮演著中介角色的屏幕,這一切變得越發容易了。
網絡確保人們可以發生聯系,并且在匿名性和可控性方面做出了美好而狡猾的承諾,可想而知它對于一個長期承受著孤獨的痛楚的人會顯出怎樣的吸引力。
你可以尋求陪伴,卻不用承擔被暴露的風險,而你的渴望和那種希冀或匱乏的狀態也不會被人發現。
你可以去觸碰外界,也可以躲藏起來;你可以潛伏在屏幕后面,也可以展露精心設計和改造過的自己。
從很多方面來看,互聯網都讓我感到安全。
我喜歡在網上和人接觸:積極的致意一點一點地積聚起來,Twitter上的“喜歡”,Facebook上的“點贊”,還有那些被設計出來并編入程序的、用來維持關注和提升客戶自負心的小策略。
我愿意成為那個傻瓜,公開我的信息,把透露出我的興趣和支持取向的電子痕跡留給未來的公司,讓他們將其轉化成任何一種他們會使用的貨幣。
事實上,這種交換有時看起來對我也有利,尤其是在Twitter上,將表露出我的興趣和支持取向的推文分享給他人是一個促進陌生人間發生對話的訣竅。
在我上Twitter的頭一兩年里,它給人的感覺像是一個社區,一個歡樂的地方。事實上,它成了一條生命線,要不是有它的存在,那時的我不知會陷入怎樣與世隔絕的境地。
然而,在其他時候,這整件事看起來都是瘋狂的。我在用時間去交換某種根本無形可觸的東西:一顆黃色的星星,一粒魔法豆,一種親密的假象。我為此放棄了自我身份的所有碎片,放棄了我表面上還占據著的肉身以外的一切。
而只要有幾條鏈接被我錯過了,或是收到的點贊太少,孤獨就會重新浮現,我的內心又會充斥著因沒能建立聯系而生的挫敗的無望感。
虛擬排斥所觸發的孤獨感與真實生活中的遭遇一樣令人痛苦,幾乎每個上網的人都曾在某個時刻經歷過這種突然襲來的難受的情緒。
事實上,心理學家用來評估排擠和社會排斥給人帶來的影響時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一種名叫“虛擬傳球”的游戲。在這個游戲中,被試者會跟電腦生成的兩名玩家玩拋接球的游戲。按照程序的設置,在前幾次投擲中,虛擬玩家會正常地拋接,但是后來,互動會停留在兩個虛擬玩家之間——這種體會跟處在一段對話中的你的虛擬自我、你的化身突然被排斥在外時所引發的即刻刺痛感是一樣的。
可當我能夠從對話中抽身,接著又被“觀看”這種令人上癮的行為所拯救時,我還在乎什么呢?電腦提供了一種愉悅的、流動的、沒有風險的凝視,因為沒有一樣被我觀看的東西意識到了我這個觀察者的存在和我那起伏不定的注意力,盡管我留下了一連串標示著我的訪問路徑的本地終端數據。
徜徉在被互聯網點亮的林蔭大道上,停下來掃一眼人們用自己的興趣、生活和身體組成的展覽,我能感到自己與波德萊爾產生了某種血親關系。
他在散文詩《人群》里為漫游者,也就是城市中的不受約束的、無關政治的流浪者奠定了一份宣言,用夢一般的句子寫道:
“詩人享有這無與倫比的特權,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成為自己和他人。就像那些尋找軀殼的游魂可以隨意進入任何人的軀體一樣。對他來說,一切都是敞開的。”
有時,我拉動著頁面時瞥見了鏡子里自己的臉,這張臉毫無生氣,沒有靈魂,被屏幕的光線照亮。
也許我的內心會被我看到的東西吸引住,從而感到焦躁不安或是徹底被激怒,但從外表看來,我就像一個半死不活的人,一具被機器吸走了全部注意力的孤獨的軀體。
幾年后,在觀看斯派克·瓊斯執導的《她》時,我在華金·菲尼克斯飾演的西奧多·通布利的臉上看到了一模一樣的表情。
這個在真實的親密關系中受到巨大挫敗并對此心生戒備的男人愛上了他的操作系統。
讓我產生認同感的并非那一幕幕他和電話一起旋轉的畫面中的令人疑竇叢生的快樂,而是影片開頭的一個場景:他下班后回到家,在黑暗中坐下,開始玩一局電子游戲,狂躁地上下移動著他的手指,操縱游戲里的化身登上一個斜坡。
他臉上全神貫注的表情令人感到悲哀,他那癱坐著的身體與巨大的屏幕相形見絀。他看上去是那么無望、可笑,完全與生活脫節,而我立即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個21世紀的遺世獨立的、對信息產生依賴的標志性形象。
到了那個時候,人類也許能和一個操作系統發展一段浪漫關系,這一想法已不再顯得荒謬不堪。數字文化正在以超快的速度發展著,快得讓人很難跟上它的節奏。
前一分鐘某件事情還是科幻小說里的帶有明顯的滑稽可笑意味的想象,下一秒它就成了一種隨意的日常行為,成為每日的生活機理中的一個部分。
在到紐約的第一年里,我曾讀過詹尼佛·伊根的《惡棍來訪》。小說里的部分情節被設置在不遠的未來,涉及一名年輕女性和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之間的一次商業會晤。
在交談了一會兒后,對話所需的精力開始讓這女孩感到不耐煩起來,于是她問那個男人她能否直接“打字”給他看,盡管他們是肩并肩坐著的。隨著信息無聲地在他們兩人的頭戴式耳機里流動著,她看上去“放松得幾乎要睡著了”,她把這種交流稱為純粹的交流。
我能清楚地想起自己在讀到這里的時候感到的震驚,我感覺它雖然有點牽強,卻是段了不起的情節。幾個月后,它似乎不僅顯得真實可信,而且完全成了一種可以理解的需求。
現在這就是我們行事的方式:在公司里打字,給同一張辦公桌上的同事發郵件,避免人與人的接觸,代之以一對一的郵件往來。
這是虛擬空間帶來的放松感,是插上電源后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所產生的安慰。
在紐約,無論我是坐在地鐵里、咖啡館里,還是在街上步行,我都會見到人們都被鎖在他們自己的網絡里。
手提電腦和智能電話的奇跡在于它們讓人們從實體的人際交往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在身處所謂的公共場合時還能一直躲在一個私人的泡泡里,在享受著表面的獨處時還能跟其他人進行互動。
似乎只有無家可歸的人和沒有財產的人過的才不是這樣的生活,但那不包括整天泡在百老匯的蘋果體驗店里的街頭浪蕩兒們。即使他們夜里都沒有睡覺的地方,他們也會一直停留在社交網絡上。
每個人對此都心知肚明。每個人都知道那看上去是什么樣子。
我記不清自己讀過多少篇關于我們變得彼此疏離的報道了,這些報道說我們被捆綁在了自己的設備上,對真實的交往懷有戒心。這些報道還指出,我們正面臨著一場親密關系的危機,因為我們的社交能力正在衰退。
但這就像是在透過望遠鏡的鏡頭反方向看出去。并不是因為我們把社交和情感生活中的太多部分轉交給了機器我們才變得冷漠,疏遠彼此。
這無疑是一個能使其自身永久存在的循環,但發明并購買這些東西的部分沖動源自人們在交流上遇到的困難和對溝通的恐懼,以及交流這一過程偶爾會導致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危險。
盡管那時在地鐵上隨處可見的一則廣告聲稱“擁有智能手機最棒的一點是你永遠都不必再給任何人打電話了”,但這個小機器致命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它會免除其所有者對人群的需求,而是在于它會為他們提供聯系。
更進一步來說,這是一種毫無風險的聯系,其中涉及的溝通需求將永遠不會被拒絕、誤解或遭到打擊,或是要求人們付出超出他們愿意付出的關注度、親密感或時間。
(摘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孤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