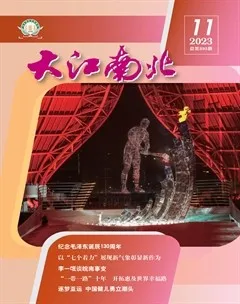新四軍“義務軍醫”羅敏修
“救死扶傷,數十年如一日;愛國進步,盡畢生為人民。”這幅1979年羅敏修去世時懸掛的挽聯,高度概括了羅敏修愛國為民、救死扶傷的一生。更鮮為人知的是,1938年3~5月新四軍在巖寺期間,羅敏修自愿擔負起為新四軍指戰員看病療傷的重任,被葉挺軍長譽之為“義務軍醫”。
羅敏修(1906~1979),1926年考入上海南洋醫學院,1930年獲醫學士學位,先后受聘于慈航、惠生及新中國醫學研究院。當時惠生高級助產校附設有平民產科醫院,是慈善機構,別人上一堂課兩塊銀元,他只收一元。他曾用一首打油體詩《示諸生》表明心跡:“鈴響到講堂,點名呼一場。念完油印句,吸盡石灰香。老旦鬢發白,三花臉自妝。為期諸子懂,辛苦又何妨?”在教學實踐中,他有感于當時的勞動婦女不僅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而且在生育上常常連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告誡學生要呼吁社會,大力提倡新法接生。1933年,他租下上海法租界跑馬廳路87號,創“立德醫院”,開始邊教學邊行醫。
1937年,迫于時局動蕩,羅敏修攜一家老小從上海疏散回徽州,沿途看到逃難的百姓絡繹不絕,十分感慨。幾經輾轉,他在巖寺租下房子,創辦了黃山腳下較早的一家西醫診所“徽州醫院”,并設了產婦科。其親屬也是學生的程振翠、程日芬(即田井,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婦聯書記)也隨之由上海回到徽州,并擔任產婦科助產士,積極推廣新法接生,使這一新事物在古老的徽州大地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當時,在黃山腳下巖寺一帶,羅敏修不僅醫術遠近聞名,而且醫德有口皆碑。病人無論是有錢無錢,有權無權,只要上門求醫,他都一視同仁,認真診治,絕不厚此薄彼。即使是下班后或節假日,甚至是深更半夜,凡請他看病,皆有求必應,從不嫌煩。正因為羅敏修不凡的醫術和“醫者仁心”的高尚品質,早在1937年底,他就被黃誠(中共黨員)聘任為“七政”(第7戰區戰地政治工作委員會)訓練班巖寺工作團義務醫師。
1938年春,巖寺成為新四軍東進抗日的第一站,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陸續匯集到這里整編。剛剛成立的新四軍,正面臨著一邊是歷經九死一生的紅軍游擊隊員傷病急需治療,一邊是缺醫少藥的窘境。在葉挺、陳毅出色的統戰工作和新四軍抗戰精神的感召下,羅敏修自愿擔當起為新四軍義務看病療傷的重任。他努力地發揮一技之長,用實際行動支持抗戰,幫助新四軍。陳毅常到醫院和他談形勢,向他了解當地風土人情,閑暇時還一起下棋品茗。1959年,當地征集革命文物時,羅敏修便將陳毅當年送給他的那副圍棋贈予巖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的翌日,國民黨憲兵團就查抄了徽州醫院,抓走羅敏修和助手程振翠(羅的妻妹,1944年被敵人殺害)。后來羅敏修的家又被查抄了幾次,終因查無實據,最后定性為“中共同情分子”。羅敏修才在當地群眾強烈要求看病的呼聲下,被聯名保釋了出來。此后,他就在特務的秘密監視下看病行醫多年。
歷經自己被抓、家被查抄、親人慘遭殺害的悲憤,羅敏修的思想也完成了由“中共同情分子”向“親共分子”到“革命分子”的轉變。尤其是1945年之后,他不顧白色恐怖和山高路遠,先后多次冒著生命危險。深夜跋涉30余里山路,到黃山游擊隊駐地給游擊隊指戰員療傷治病,用實際行動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貢獻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盡管上海、杭州、合肥的多家衛生醫療單位發出了邀請,但都被羅敏修婉拒,他以百倍的熱情投身到新中國的基層醫療事業中。1952年,他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攜醫療器械,與老中醫金霽時、方建光,西醫沙怡如等,組建了巖寺聯合診所并任所長;1960年以后,又參與了巖寺區衛生院(現黃山市第三人民醫院前身)的組建工作,并一直擔任負責人。他從不以“曾有功于革命”自居,始終秉持醫者仁心的初衷,扎根基層,幾十年如一日,履行著醫務工作者“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天職,為西醫在黃山腳下的推廣作了最大的努力。據其子羅日全回憶說:在他小時候的印象中,父親上班去是給人看病,回家來仍要給人看病。即使他60多歲時,根本就沒有“退休”一詞的概念,仍經常出診,每逢這種時候,母親總會叫我們兄弟中的一個去陪伴。就是在他臥床不起的最后歲月里,還常常在床邊給人看病,且從未見過他收取一錢一物。
羅敏修生前從沒人給他確定過“參加革命”的時間,他也從未享受過“離休待遇”,但他解放初期曾當選為皖南區各界代表大會代表,是歙縣二、三、四、五、六屆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編輯 余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