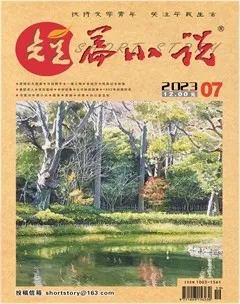奇怪的志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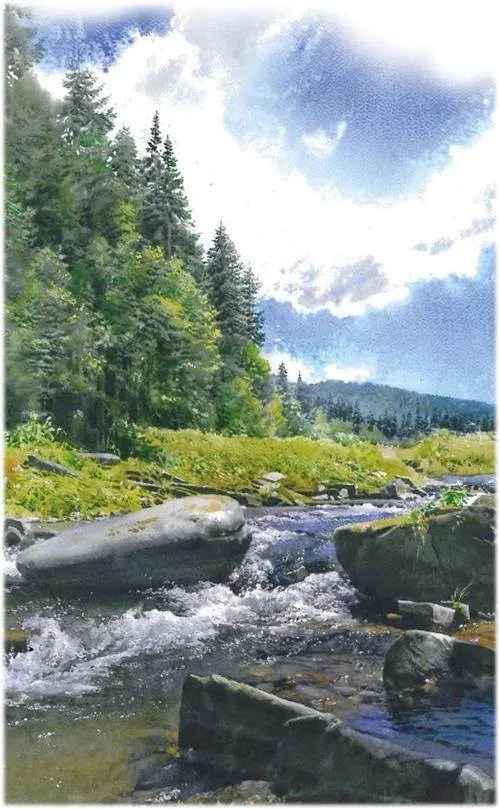

一
從北京坐動車到省會,從省會坐大巴到舍予縣城,再從舍予縣城坐城鄉公交到曉天鎮,再從曉天鎮搭乘既運貨也拉人的小三輪,再步行近兩小時,總算到達了你們所說的地點。
我無法想象,你們會在這樣偏僻閉塞的山里生活了兩年!
我,跟這里有關?
我現在看到的一切,與當初你們所生活的環境應該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畢竟,已是十七年過去。十七年,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十七年,足以讓很多地方很多東西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里肯定也是如此。記得聽你們說過,當年你們從北京到省城坐的是綠皮火車,長達十幾小時,整個路程就經歷了三天兩夜,相對于今天的我,早晨出發,傍晚到達,完完全全的天上地下。
抱歉,你們的手繪地圖沒用上,實在是太落伍了,我根本就沒掏出來,掏出來也沒用,除了一座座山頭還在原來的位置,其他的只怕都面目全非。我只記下你們說過無數次的名字——旮旯沖,輸入手機的導航里,順著導航的指引,沒有找不到的地方。
我沒遵照你們的意見,去找老隊長,說白了,我不想過早地暴露自己。我要在暗處,尋找你們所說的。
這里的山太大了,所有的山都是連著的,像起伏的波浪,所有的人家都在波浪上飄浮,或隱或現,不走到近前根本沒法發現。這里的山太高了,仰著頭才能看到山頂,看到藍天,看到白云。原來,天是這樣的藍,云是這樣的白,還有漫山遍野都是綠,各種各樣的綠,對于色彩,顛覆了我原有的認知,我得重新進行定義了。
旮旯沖像個舊式的搖籃,斜斜地躲在山窩間,要不是一條小路從大路的一邊分個叉伸進去,根本想不到里面還有人家,而且是十幾戶人家。我把背上的畫板反過來,用粗黑的炭筆寫上“我要租房”幾個字,描得粗粗的黑黑的,從沖口的人家開始,一家家地問。他們很奇怪,盯著我畫板上的字看,再盯著我看,問,到這深山溝里租房干什么?他們的話音很繞,尾音長還帶鉤,很難聽懂,但從他們的表情上我能看出意思。我把手中的畫板翻過來,托在手上,在畫板上做了個畫畫的樣子。他們懂了,仍然覺得稀奇,不關心我租房的事了,關心起我的畫畫。可我沒法解釋清楚。
一家家問過去,都只有老人在家,家里空空蕩蕩。有兩家有孩子,孩子能說不太標準的普通話,我就讓孩子翻譯大人的話。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有些長年累月不回來,還有幾家把老人和孩子都接走了。他們想出租,反正房子空了許多,可又猶豫著,不敢租,從他們的目光里就能看出對我的不信任。我理解,畢竟是陌生人,何況是個說不出話的啞巴,什么來路?住到家里,要是出了事怎么辦?要是我,我也不會輕易相信。如今的社會,誰也別輕易相信誰,信了,就往往意味著受騙和上當。
我接著在畫板上寫,我是從北京來的,我是志愿者。他們還是搖頭。又是一家,一個穿著整潔的大爺,能說幾句跟孩子們一樣的普通話,也識字,看了我畫板上的字,立馬答應租,并馬上帶我去看。是他兒子的房子,兩上兩下的小洋樓,夫妻倆和孩子都出了門,一把鎖鎖著。我問房租多少,他說房子反正空著,有人住才有人氣,要什么錢。你是北京城來的客人,是貴人,你能住這屋,求之不得呢。我堅持要給,掏出一千元錢,他推讓了半天,只收了三百。
老兩口幫我一起打掃衛生,樓上樓下,角角落落,全部打掃得干干凈凈,連門口也清掃了一遍,雜草拔得一干二凈,像是自個的兒子回來了似的。邊打掃,大爺便自我介紹,姓涂,曾經是民辦教師,有兩個女兒,第三個是兒子。
房子打掃好了,涂老師老兩口子又要我到他家吃飯。去就去吧,正好不會燒飯,最好以后都在他家吃,付錢給他,也省了事。涂大媽逮了只雞殺,我不讓,非要殺,又不知從哪拿出一截發了黃的肉,說是腌肉,香得很,放在腌菜壇里埋著,不會壞。時間不長,香噴噴的六個菜就上了桌,涂老師又拿出一瓶迎駕貢酒,三個酒杯,都滿上。我不喜歡酒,可面對老人的熱情,就端起了杯,喝酒的機會,大爺一直在說,我偶爾在紙上寫出想問的問題,讓大爺回答。
我想出各種問題,試探著套涂老師的話。這里十幾年前來過外地人嗎?是做什么的?都做了些什么?住在誰家?我一步步向你們靠近,焦點是了解你們的當年。涂老師記得很清楚,對你們的印象非常深刻,說了些你們的事。說你們是大好人,當年就住在老隊長家,不但莊子上的人都記著你們,那些已經成人的孩子也都記著你們。
聽到這些,我的心暖暖的。或許,這就是回報吧。可命運的眼睛瞎了嗎?它為什么看不見這些?
我喝多了,從小到大,一直不愿意沾酒,第一次喝這么多。還有很多我想問的問題,尤其是關于你們的,關于我的,幾次動筆想寫又畫掉了,不敢問。等等吧,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一路上,我都在給自己打氣,做心理建設,可那些問題太沉太重了,就是不敢亮相。
躺在床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黑暗,什么是靜。這黑暗比閉著眼睛的黑還要黑暗,什么也看不到,把手伸到臉跟前,挨著了鼻子也看不到手。分明是那個叫作黑暗的東西包圍著我,壓抑著我,封鎖了我所有的感覺器官,找不到絲毫的縫隙逃走。北京也有夜晚的,怎么就沒有這樣的黑暗呢?至少,沒這里的黑暗純正。
安靜也是,這與把耳朵塞住的感覺完全不同。小時候,你們只要一罵我,我就用手堵著耳朵,堵不嚴實,就找軟軟的衛生紙堵,罵是聽不見了,其他聲音也聽不見了,但會出現嗡嗡的響。現在不同,不用堵,不是啥聲音聽不見,而是根本沒有聲音。我不信,有意放緩呼吸,把心跳的聲音壓低,集中全部精力找聲音。隱隱約約有了,偶爾冒一兩下的鳥叫,應該是山上的,還有微微的流水聲,遠遠地嘩嘩,像是在夢里,仔細聽,又明明就在身邊。
對黑暗和安靜的好奇及探究,慢慢過去了,還是沒有睡意。見到的幾個旮旯沖人,一個個在我眼前晃,一會兒是他,一會兒是她,是他?還是她?我不敢想象會是他們那樣的,我無法接受。想著,想著,迷迷糊糊地不知道什么時候睡著了,一覺醒來,太陽已經穿過窗戶,照在了床上。
二
我背上畫夾,挨家走,為每一個人畫像,不收一分錢。
他們不相信,不相信我一個從遙遠的北京城來的人,一個啞巴,只是為他們免費畫像。他們從懷疑到好奇,從猶豫到被動地接受,直到接到畫有自己像的畫紙那一刻,才有笑容露出來。旁邊的人說像,自己也點頭稱是。我不用挨家跑了,都看稀奇一樣趕過來,自覺地等,一個個讓我畫。
我畫得很認真,把每個坐到我面前的人,都仔細地看進心里,一顆痣,一道疤,一個眼神,都清清楚楚。他們有太多的問題要問我,是做什么的,來這里干什么,打算待多久,北京什么樣,等等。我沒空回答,我的心思只在畫筆上,專注在畫紙上。有些,我也不想回答,正好就忙著畫畫的機會逃避開。
老隊長也坐在了我的面前。是聽別人叫他老隊長的,其實我已經認出來了,在你們無數次給我看的相冊里,有好幾張照片里面都有他。比起照片上的他,現在的他更老了,身板還硬朗,頭有些勾,頭發雪白,襯得臉更黑了,黑得像墨。
除了兩個躺在床上不能動的老人,全莊其他在家的人,我都畫了,九個老人,五個孩子,沒有一個青壯年。我聽你們說過,你們在這兒的時候,全莊大大小小總共七十二口人,相差了這么多,全都走出了大山?
我等不及了,第二天,我就來到了你們當年教書的小學。變了,肯定變了,與你們所說的大不一樣,至少,在你們的嘴里是平房,而現在是樓房。只是學生不多,顯得冷清和空曠,里外轉了轉,還有些教室空著,沒用。我來到辦公室,亮出已經寫好字的畫板:我是志愿者!
在座的幾個老師很熱情,請我坐,給我倒水,問我從哪來,有什么事,我一一在紙上寫清楚給他們看。他們這才知道,我是啞巴,相互看了看,有些不敢相信。其中一個老師去找校長。校長很快來了,與我握手,沒想到他會一點兒簡單的手語,我們順暢地交流起來,不用費事,就有了相互間基本的了解。
校長答應了我的請求,來教學生們畫畫,一周五天,一天兩節課,義務的,不拿一分錢報酬。校長提出要給,可我拒絕了,我強調自己是志愿者。從和校長的交談中,我了解到,目前在職的教師大多沒有超過十年,時間最長的兩位也沒超過十五年,也就是說,和你們沒有交集。我有點兒失望,本指望能了解到一些和你們有關的事情,看來,是沒希望了。
校長留我吃飯,我拒絕了,說還有事。出了學校,我把學校的周邊走了個遍,一邊走,一邊與你們說的進行對照。家家戶戶的房子變了,大多成了兩層小樓;路寬了,汽車能開到家門口;田地里看不到什么人,有的種著糧食,有的則荒著,長著草;學校正對門的小河還在,河床老高,石頭曬得發白,水細了,躲在石頭縫里悄悄地走。
村莊里的人,是稀的,路上也沒見有什么人,田地里更是。即使是白天,也顯得格外安靜。我很不習慣。在北京,就是把自己關在嚴嚴實實的屋子里,也沒有這樣安靜。還有隨處可見的綠,山是綠的,樹是綠的,草是綠的,怎么看都溫潤安寧,這點,我是喜歡的。
在學校的協助和安排下,我把整個教學分成了兩個部分,一是美術鑒賞和基本美術知識講授,旨在提高學生藝術修養和品位,教學方式是播放視頻資料和PPT,同時用寫字板投影的形式回答學生們的提問,進行交談;二是速寫、素描等實踐,從臨摹開始,再實物寫生,手把手地教和輔導。我沒想到的是,孩子們對我的到來非常歡迎,缺少語言交流只是一開始有些別扭,時間一長,彼此都相當默契。我強烈感受到了山里孩子的求知欲望和好學精神,他們的眼睛里滿是對知識的渴望,再多的知識都能灌輸進去,都不嫌多。至于美術教育他們更是缺乏,沒有正規的師資力量,也沒有正規的教材,而我恰好填補了空白。
涂老師看我每天早早地出門,晚晚地回來,忍了好幾天,終于問我到哪去了,飯在哪吃的。當聽說我是到小學上課的時候,開心地笑了,說,你怎么不早說?校長就是我女婿啊。涂老師親熱地拉我到他家吃飯,我說在學校吃過了,還是拉我,說要和我喝幾杯。
明顯地,涂老師和我親近了許多,趁著他的高興勁兒,我在紙上寫道:我還想聽聽十幾年前來過的他們的故事。
涂老師說,行,沒問題,只要你感興趣,我把知道的都告訴你。那時,我還在學校教書,正式的老師就幾個,其他的全是民辦教師。山窩里太窮太偏太遠了,山外的老師好不容易來了,沒待上幾天就又走了,待不下去。我當時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還犯疑惑,是閑得無聊還是咋的?他們是三個年輕人,從省城來的,兩男一女,剛大學畢業,直接找到學校,要求當義務老師,就是不要錢只上課。我們一聽,高興壞了,缺的就是老師,正兒八經的老師,還不要錢,更好。學校沒地方住,怕他們受委屈,我就把他們帶回來。我家地方小,正愁著沒地方睡,老隊長來了,讓到他家去住,就去了,一住就是兩年。噢,不對,其中一個男的在大半年的時候提前走了,剩下的一男一女待了整整兩年。
聽著涂老師的講述,我仿佛成了你們,經歷著你們的當年,你們的故事。我知道,涂老師講述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遠遠不過癮。何況,最核心的事,涂老師還沒涉及,我想問,可又不敢啟齒。
我讓涂老師哪天帶我到老隊長家去,再聽老隊長講講。涂老師一口答應,說只要我有時間,隨時都行。我開始期待,又繼續畏懼,我不知道是否能夠面對。
這一次,我酒沒喝多,只是頭暈暈的感覺。每天晚上一樣的黑,一樣的靜,我在黑暗和安靜中捕捉鳥的叫聲,還有蟲的叫聲,還有風的聲音,河水的聲音是一如既往的,始終都在。
河水是向哪里流的呢?它帶走了多少人的故事?其中,應該包括你們的。
三
轉眼就是一個月過去,我還沒到老隊長家去。涂老師催了我幾次,我都以忙委婉地拒絕了,不是拒絕,是推遲。去,是肯定要去的,必須要去。去了,才能觸及問題的核心,像一張巨大的黑幕瞬間揭開,一切馬上就能真相大白。
一方面一再推遲,一方面我又焦急不安,我太急于知道你們的事情。青春年少,城市出生長大,天之驕子;農村,偏僻山鄉.貧窮落后,孩子們。像一個個謎,刺激著我,迫切地期待破解。
我有了個辦法,把你們的照片拿出來,讓學生們對著照片畫像。我讓學生把畫像帶回家,請家里人評評,畫得怎么樣。我的目的很簡單,通過他們找回認識你們的人的記憶,或許,會主動站出來,站出來的同時,該是你們的故事浮出水面吧。從外圍接近當年,接近當年的你們。果然有效果,第二天就有學生找我,說他爸爸問,這照片是從哪來的,他認識這兩個人。我欣喜若狂,放學時,我隨他一道去了他家。
學生的父親是個樸實的農民,很靦腆,說話結巴,見到陌生的我有點兒不好意思,還有點兒緊張。我仍然用畫板寫字和他交談。他曾經是你們的學生,因為說話結巴,經常有同學跟著后面學,學著學著就打了起來,被一起罰站。也因為結巴,上課一遇到老師提問,就把頭深深埋下去,從不舉手。
你們不同,不但從不罰他站,還充當他的保護神,教育其他學生要學會尊重,鄙視別人就是貶低自己。還特意把他叫上,共同參與同學們的游戲,和大家一起玩老鷹捉小雞、斗雞、摜寶、跳房子等,在玩樂中,消除同學們之間的隔閡。課余,把他叫到沒人的角落,教他說話的技巧,督促他大聲叫喊和唱歌,克服緊張心理。上課時,主動走到他的身邊,用最簡單的問題指名要他回答,鼓勵他大膽回答,鍛煉他的膽量和口頭表達。也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把你們當作恩人。
他一再追問我,怎么有你們的照片,你們現在在哪?我告訴他,你們是我的恩人,現在在很遙遠的地方,很好。他讓我轉告,有時間一定來玩玩。
我在回答他的時候,差點兒就寫出了父母這兩個字,剛寫了兩筆,又畫掉了,改成了恩人。是的,你們就是我的恩人,父母式的恩人。否則,我不可能有這一次的遠行。我要的就是沿著你們當年的路走一遍,把你們做過的事做一遍,切身感受一下你們的當年,做一回你們。至于你們最最主要的口丁囑和意愿,說實話,我希望忽略掉,雖然很難,也不現實,但我真的想忽略。
在我的生命履歷上,只有你們的存在!
可我又答應過你們,答應了,就必須做到。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我已經無數次違抗你們了,更多的是陽奉陰違。你們要我看書,我偏要去打球;你們要我寫作業,我背著你們上游戲廳;你們要我好好學習,我在課堂上偷著畫畫:你們要我和同學友好相處,我就要和同學打架;我幾乎每一件事都和你們對抗,讓你們無可奈何,讓你們焦頭爛額,讓你們搖頭嘆息。這一次,絕不可以。
老隊長主動找我了。校長看到了我讓學生們對照著畫像的照片,拿著畫作給涂老師看,涂老師拿給老隊長看,老隊長問涂老師,我和你們是什么關系?涂老師說不知道。老隊長急了,就主動來找我。
面對老隊長的問話,我咬著牙,在紙上寫下了這句話:你先告訴我,他們當年是不是在這里抱走了一個孩子?
老隊長的黑臉更黑了,盯著我看了半天,點了點頭。
我再問:那孩子是怎么來的?
老隊長說,是人深更半夜放在我家門口的,聽到哭聲,開門看才看到。那時,家家都窮,自己都糊不飽肚子,沒誰敢收養,他們就收養了。
我再問: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誰嗎?
老隊長搖了搖頭,說,要是知道,他們就不會把孩子帶走了。那孩子,該跟你差不多大了,你認識他們,也應該認識那孩子吧?
我沒有回答老隊長,接著問:那孩子是你們這兒的人,你們隨隨便便就讓外地人帶走?要是他的父母找你們要,怎么辦?
老隊長嘆了口氣,說,那時候,這種情況多著呢。養不活了,又不能看著餓死,就抱到人家門口或者路邊,讓別人撿去。也有后來又來尋找和認親的,但別人家已經養大成人了,頂多作為親戚走動。還有孩子不認親生父母的呢。他們可是大好人,又在大城市,肯定不會虧待孩子。
我無話可問了,一顆始終懸著的心慢慢落了地,踏實起來,安穩下來,說不出的冷靜。老隊長問我,他們現在還好嗎?我寫道:還好。想了想,又補充道,他們到外國去了,很遙遠的一個國家。他們很想念這里,所以委托我來看看。
老隊長還想問什么,幾次要開口又忍住了。
我問老隊長,他們當年住的屋睡的床還在嗎?老隊長哈哈大笑,說,這都快二十年過去了,能還在嗎?你看看這莊子里,哪家不是新蓋的房子,早不像以前那樣了。有把子力氣的,都出了門,掙回好多錢。都不想回來了,就我們這幫老骨頭看著家,等我們走了,這家都沒人看了。
老隊長突然傷感起來,我也受了感染,好半天過去,在紙上寫道:不會的,我這城里人都來了,還不是因為這里好嗎?這話明顯有些虛,站不住腳,可老隊長卻高興了,胡子直翹,合不攏嘴。
涂老師來了,叫我和老隊長去吃飯,說要喝兩杯。這一回,我喝了不少,但沒醉。邊喝酒,邊聽三位老人回憶當年的事。
說你們才來的時候,嫌生活苦,還偷逮過一只老隊長家的雞,躲到后山上撿柴枝燒著吃,當天晚上,聽見老隊長家里的站在大門口罵黃鼠狼不得好死。過了好多天,老隊長家念書最刻苦的女兒早上不愿意上學,還哭,一問才知道,沒有本子和筆了,要錢買,可老隊長掏不出來。本來都是從家帶一個雞蛋到供銷社去賣,再買本子和筆,可生蛋的老母雞讓黃鼠狼給吃了,沒雞蛋可賣了。三個人相互看看,低下了頭,鉆到屋里一嘀咕,拿出兩個厚厚的筆記本和一支鋼筆,非送給老隊長女兒用。后來,是那個女娃娃說漏了嘴,老隊長才知道雞是他們偷吃的。
老隊長還說,兩個男孩子都對那個女娃娃好,為此還鬧過幾次別扭,其中一個先走,好像也是為了這事,賭著氣走的。
涂老師說,你們走后,有寄很多書過來,還有衣服和錢。書是直接寄到學校的,衣服和錢寄給老隊長,讓分給莊上最窮的幾戶人家。
他們說了很多你們的事,酒喝得越多,想起來的事情就越多,好笑的事,好玩的事,感動的事,都有。我仿佛用眼睛在看,看你們就在這里正做著那些事。
四
我得走了,半年時間一晃而過,但我還會回來,你們交代我的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可以做了,也放心去做了,得盡快完成。
我買了兩瓶酒,還有雞魚蛋肉,拜托涂大媽幫忙加工一下。涂大媽和涂老師都責怪我,家里什么都有,為什么要花錢買。你在這里當義務老師,又不掙錢,哪來的錢買菜,以后還得談女朋友,要成家,都得花錢。我說,我總在吃你們的,這回,我要請你們吃頓飯。
我到老隊長家,把老隊長也請了過來,坐上桌,我就在紙上寫,我要回去了,想拜托你們一件事。三位老人,明顯有些舍不得,嘴上卻說,你這么年輕,更應該在大城市做大事,光待在這里,也不是個事。有什么事,你盡管說。幾杯酒過去,我借著酒勁,下了狠心,開始在紙上寫。
我不用說,你們也知道,我都實情相告了。我不忍心瞞著他們,也沒必要隱瞞下去。我把你們在參加一次志愿者活動時,路上翻了車,送到醫院救治了很長時間,但沒救過來的事,都說了。也說了你們的遺言,想把骨灰葬在你們當年相愛和第一次做志愿活動的地方,拜托兩位老人找塊地方,不用大,能曬到太陽,能看到連接山外的路就行。不用像這里祖祖輩輩那樣堆出墳墓,就深埋在地下,上面栽上樹,所有的樹就是印記和墓碑。
關于我的事,我沒說,永遠也不會說。那是屬于我一個人的秘密,也屬于你們。之前的近二十年,因為你們的過于寵愛,對我的所有教育都是失敗的。你們之前所有的話,我都違背了,從現在開始,我不會了。你們交代的事,你們沒交代的,你們一直做的事,我都會一一遵照執行和繼承。
我的志愿者行動,就從你們的第一次志愿者行動的地方開始。
是否血脈所系,不再重要。
三位老人流淚了,淚水順著臉腮一個勁地流,滴在了碗里,滴在了酒里,又端起來喝。他們說,孩子,你放心吧,一定找一塊最好的地方,栽最好的樹苗,你抓緊把他們的骨灰帶來吧。他們叫我孩子,像父母叫自己的兒女,我熱血上涌,說不出的親切和溫暖。
我站起來,離桌,向他們跪下了,磕了三個重重的頭。這是我唯一能感謝的方式。
我又思考上了一個問題:將來的我,是永遠扎根此地,還是像你們一樣,從此開始的志愿者?
旮旯沖,曉天鎮,舍予縣,無論我是否愿意,已經嵌在了我的生命里。后路漫長,先從我的志愿者生活開始吧!
責任編輯/董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