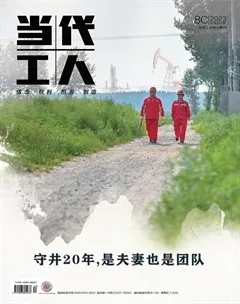風從北吹來

一
陳雪嬌躺在遼河邊一片綠茵茵的草地上,溫暖的陽光沐浴著她,非常愜意。
有風吹來,風里夾雜著野花的芬芳,她從那芬芳里嗅到了薰衣草的微香。按說,這才剛剛入夏,還不是薰衣草花朵綻放的時節——香味是從哪里來的呢?她邊想,邊循著花香將臉轉了過去,這一轉,就看到了站在不遠處一臉燦爛笑容的李江河,他手里正捧著一束如夢幻般盛開的薰衣草。
陳雪嬌愣了一下,眼睛里充滿了驚喜:“你怎么來啦?”“一出門,就看見你開著紅色雅閣往外走,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來河邊了。” 李江河笑著說。“你不是在跟蹤我吧?”陳雪嬌有些不悅。“你怎么能這樣說我?”李江河有些生氣,初來時的燦爛微笑也僵硬在臉上,“我有那么無聊嗎?”
陳雪嬌大概也覺得自己的話有些過分,說:“我不是在和你開玩笑嘛,怎么還當真了?”顯然,她是以守為攻。“是我認真了,怎么連你開玩笑的話都沒聽出來。”李江河聽陳雪嬌那樣說,忙道歉。“好了江河,這束花你是想送給誰的?”陳雪嬌轉移話題。李江河的臉上又綻放出燦爛的笑容來。他雙手把花送到陳雪嬌面前,帶著幾近討好的語氣說:“當然是送給你的。”
陳雪嬌高興地接過花,薰衣草濃郁的芬芳瞬間包圍了她。是的,陳雪嬌最喜歡薰衣草了,但李江河是怎么知道這一點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歡薰衣草?”
李江河的臉瞬間泛起微紅。“有一次我去你的辦公室送文件,看見你電腦的屏保就是一片薰衣草花海。還有,你每次從我身邊經過,我總能聞到淡淡薰衣草的味道……”
“我最喜歡薰衣草了,你的心真細!”陳雪嬌這樣說時,心里有一縷溫暖緩緩升起。但這縷溫暖還沒來得及將她包圍,就稍縱即逝了,因為另一個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市文明辦的高鵬。高鵬挺拔帥氣,不僅人長得英俊瀟灑,氣質溫文爾雅,還畢業于名牌大學,可以說,高鵬滿足了絕大部分女孩兒心中對白馬王子的想象。
“高鵬!”一聲低低的驚叫,將陳雪嬌從睡夢帶回了現實。
陳雪嬌是本市一家都市報社生活版的記者,她是在去省里參加業務培訓時,認識了同在一座城市的高鵬。那是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陳雪嬌只身走在賓館西邊的花園小徑,她苗條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長。忽然,她發現身旁出現了一個更長的身影。望著這個長長的身影,她有些慌亂。還沒等她從驚慌里走出來,那個長長的身影就發出了熱情的問候:“你是都市報的陳記者吧?我是市文明辦的高鵬。”這個叫高鵬的男人,渾厚的聲音充滿磁性的魅力。
陳雪嬌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笑了,說:“早就在簽到表上看到了您的名字,正想認識一下呢!”高鵬也開心地笑著說:“你看,我們這不就認識了嗎?”
兩人并排在樹影斑駁的小徑上走著。高鵬提議:“我們去外邊走一走吧。”高鵬不光高大帥氣,人還幽默詼諧。那個夜晚,兩個人在外面走了很長的路,聊得也很是投機,仿佛有說不完的話。在回賓館的路上,高鵬請陳雪嬌吃了省城最有名的王氏燒烤。此后,在余下的3個夜晚,他們幾乎總是待在一起,談工作、聊理想。在業務培訓結束的最后一個夜晚,二人都有些意猶未盡。雖然互相留了電話和微信,但總感覺還是留下了些許遺憾。
二
回到市里的當天下午,陳雪嬌就主動給高鵬打了電話,但連續打了幾次,都未打通。陳雪嬌想,高鵬也許是在開會,將電話調成了靜音。
倒是李江河,見到陳雪嬌非常高興,像孩子一樣臉上洋溢著抑制不住的笑容。“雪嬌,你走這幾天,我感覺你像是走了很久很久。如果你晚上沒有特別安排,我為你接風!”當時陳雪嬌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只是說先回家看看再定,家里要是沒事再聯系他。
李江河還不到30歲,就已經做了都市報的副主編。他不光熱情低調,文筆也不錯,平日很喜歡寫詩。據說他有一首詩還入選了《詩歌》雜志年選,那首詩的名字是《風從北吹來》:
“風從北吹來,風吹走了生活中沉重的嘆息,最先感覺風的氣息的是滿地的野草,我們無法知道風將吹向哪里,就像無法知道我們什么時候戀愛和生命結束……”
這首詩很長,不懂詩的陳雪嬌認為也不過如此。但懂詩的同事孫浩卻認為,這是一首好詩。詩好與不好,對于陳雪嬌來說都無所謂,因為陳雪嬌認為,稱為詩人的都多少有點兒不正常。可李江河卻意外,不僅非常正常,沒有象征詩人的那浪漫而不羈的長發,他的性格還沉穩得根本不像詩人。
李江河是負責都市報內容方面的副主編,他在排版時非常認真負責,哪怕一個標點符號用錯了都要改過來。這樣一個認真甚至較真的人,竟然會寫詩!還寫出那么優秀的詩!
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江河除會寫詩,還特別會關心人,尤其對陳雪嬌的關心,簡直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比如,早晨陳雪嬌剛上班,李江河就會提前把兩份早點買好,先將一份早點放在陳雪嬌的辦公桌上,然后再回主編室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即使是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陳雪嬌對李江河也顯得很是冷淡。原因是陳雪嬌人稱都市報“一枝花”,而李江河的長相卻不敢恭維:身高不到一米七,皮膚黝黑,唯一達標的就是那雙水汪汪、充滿神采的大眼睛。陳雪嬌有時就想,一個男人為什么會長著這樣一雙眼睛?
不管陳雪嬌認不認可,報社所有人都覺得,如果兩人能成就一段姻緣,也是一樁美事——陳雪嬌長得漂亮,李江河雖既不高大也不帥氣,但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副處級了,在整個北江市也屬鳳毛麟角。從這個角度看,兩人也是郎才女貌。
陳雪嬌之所以當時沒答應李江河,是因為她還想繼續聯系高鵬。到家后,她又給高鵬打了幾次電話,依舊不通。旅途的勞累,加上心情上的沮喪,她想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兒,卻不知怎么就睡著了,然后就做了那樣的一個夢。
三
夢醒后,陳雪嬌又給高鵬打了電話。這次電話接通了,只是高鵬的聲音有些隨意且疏遠,甚至可以稱為冷淡。他懶懶地問陳雪嬌有什么事。
“我到家了。”陳雪嬌的臉立馬紅了,又補充道,“我回到單位就一直打你電話,但總是打不通。”“哦,我回來以后馬上就去主任那兒匯報工作了,剛才又處理了幾份文件。”
電話里,陳雪嬌覺得高鵬每說一個字,都更遠離自己一步,便連忙說沒事,掛斷了電話。隨后,她立刻撥打了李江河的電話。跟前一通電話境遇不同的是,幾乎在鈴響的瞬間,李江河的電話就通了。他關切地問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陳雪嬌說沒事,只是想問問李江河晚上去哪里吃飯。
“你是記者,見多識廣。你喜歡去哪里吃?我一切聽你的。”李江河這帶有幾分寵溺的話語,在陳雪嬌心里立刻蕩漾起一股暖意。“你雖是領導,但收入有限。今天就不‘宰’你了,我們就去廣安路的孫家烤魚館吧。”陳雪嬌說。李江河半開玩笑地回:“好。但是請大牌記者去那么小的飯店,不丟份兒嗎?”陳雪嬌也佯裝嗔怒地說:“李主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拿我們百姓尋開心?”“不敢不敢,記者可是無冕之王,雖然沒有官職,可誰要是被你們‘參上一本’,最輕也得脫層皮啊!”“李江河,你什么時候學會油嘴滑舌了?”“守著你這樣的美女記者,我要是不進步,肯定得被淘汰出局。”
陳雪嬌被李江河逗得很是開心。她笑了一陣兒,忽然又想到了高鵬。她無法理解為什么高鵬一回來就變得那樣冷淡,冷淡得就像換了一個人。在省里培訓時,高鵬是一個多么幽默詼諧的人啊,假如他永遠保持在培訓時的那種狀態,陳雪嬌真想選擇高鵬做男朋友,即便他只是個普通職工,家庭等各方面條件都不那么理想。
也許事情就是這樣湊巧。陳雪嬌和李江河來到孫家烤魚館時,正好在門口遇到了高鵬,以及他身旁一個表情冷漠的漂亮女人。
一見面,陳雪嬌和高鵬同時愣住了。還是陳雪嬌先打破了尷尬:“怎么,你也來這里吃飯?”
高鵬笑笑,說:“這北江市也太小了,上午我們剛培訓結束,沒想到晚上又在這里見到了。”
“是啊,看來這家飯店是真火。平日里,我總到這里吃飯,怎么從沒見過你?”
“我也總來這里吃飯。只是,以前我們并不認識,相信以后會經常見面的。”隨后,高鵬將身邊的漂亮女人介紹給陳雪嬌:“這是白女士,我女朋友。”
陳雪嬌的心顫了一下,但仍很有禮貌地將手伸了過去,說:“認識你很高興,我叫陳雪嬌。”
漂亮女人只是淡淡地和陳雪嬌碰了碰手,上下打量后,說:“我聽高鵬提到過你,他說在省里業務培訓時認識一位美女,看來這個美女就是你了。”
“不敢。我有幸和高鵬一起去參加省里的業務培訓。真為你高興,能找到高鵬這樣優秀的男人。”陳雪嬌回。
“是嗎?”女人的嘴角撇了一下,“我沒看出來他哪里優秀,都快30歲了,在單位還是個大頭兵。”她一邊說著,一邊失望地瞥了高鵬一眼。高鵬頓時就有些掛不住臉,對陳雪嬌說:“要不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坐在一塊兒聊天還熱鬧些。”
沒等陳雪嬌搭話,女人就不高興地說:“干嗎在一起?你沒看人家也是雙出雙入的嗎?你想給人家當電燈泡?”
“還是兩便吧。”陳雪嬌笑笑,轉身跟李江河進了一個小包廂。
李江河把陳雪嬌讓進雅座,說:“今天你是主角,吃什么你說了算。”
陳雪嬌也沒推辭,拿過菜單就點了4道菜,然后把菜單遞給服務員。李江河卻不高興了:“這哪行,為你接風怎么也得6道菜。況且你還沒點酒呢!”
“你知道我從來不喝酒。”
“平常我也不喝,但今兒咱倆都破個例。喝點紅的,度數低。”
陳雪嬌沒有再堅持,她想如果再堅持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菜很快就上齊了,紅酒也拿了上來,是2015年的拉菲。陳雪嬌有些吃驚地說:“咱倆喝這么貴的酒干啥?再說我又喝不出來好壞。”
李江河笑著說:“不管我們錢多錢少,都不要委屈了自己。”一邊說著,一邊為陳雪嬌倒了小半杯紅酒,自己也倒了一樣多,舉起酒杯,輕輕地和陳雪嬌碰了一下杯子,“來,第一杯我們先干了。”
陳雪嬌為難地望了一眼杯里的紅酒,“這么多酒,我一口干不了咋辦?”
李江河寬厚地笑著說:“那就分兩口。”然后他一仰頭,先將自己杯里的酒喝干了。
四
二人邊喝邊聊,氣氛格外融洽。就在這時,高鵬大大咧咧地走了進來。他手里端的是白酒,可當他看到陳雪嬌和李江河杯里的紅色時,立馬提高分貝說:“換酒換酒,哪能用紅酒糊弄人呢?”
“高鵬你別起哄,我其實連紅酒都喝不了。”
高鵬帶著幾分醉意說:“陳雪嬌你可以不喝白酒,但你的這位朋友必須喝白酒!”
陳雪嬌正色,“這是我們報社的李主編,李主編也不喝白酒!”
“你又不是李主編,你怎么知道李主編喝不了白酒?當領導的,哪有不喝白的。”高鵬不依不饒。
陳雪嬌還想阻攔,李江河卻擋在了前面,笑著說:“今天主要是為雪嬌接風,等有時間,我們哥兒倆再另約白的。”
高鵬還想再堅持,這時,和高鵬一起來吃飯的冷面女人走進來,“人家不喝就算了,你這樣死皮賴臉,沒尊嚴。”
聽女人這樣說,陳雪嬌有些不高興。“這跟尊嚴有什么關系?”
女人望了一眼陳雪嬌,說:“這當然跟尊嚴有關系,被人拒絕難道是有尊嚴嗎?”接著補充道:“我見過你,你采訪過我父親白殿奎。”
陳雪嬌一聽冷面女人說白殿奎是她父親,便明白了一切:“原來紅光房地產公司的白總是你父親。怪不得這么高傲!”又冷冷地望了一眼高鵬。
高鵬在陳雪嬌的目光下,顯得有些局促不安。
李江河畢竟是做領導的,他看清形勢后,立即喊服務員結賬,然后和陳雪嬌提前走了。
第二天,陳雪嬌剛到報社,就見高鵬等在她的辦公桌前。“你來做什么?”
“我是專程來找你的。”高鵬殷勤地說。
“我一會兒去采訪。你有什么事嗎?”陳雪嬌淡淡地說。
“雪嬌,我想和你單獨聊幾句,最多也就耽誤你兩分鐘。”高鵬這樣說時,目光里充滿了乞求。
陳雪嬌不想太傷害高鵬,跟他走出了辦公室。她帶高鵬來到報社的接待室,剛一進屋,高鵬就急不可待地抓住了陳雪嬌的手,說:“雪嬌,我們開始戀愛吧。我實在無法忍受那個女人的頤指氣使了。”
陳雪嬌冷冷地將手抽出來,說:“昨天你看到了,我已經在和陪我一起吃飯的李主編談戀愛了。”
高鵬難以置信地說:“他?他怎么配得上你?你長得那么漂亮。”
陳雪嬌笑了笑,說:“他是沒你帥氣,可他身上具備的潛質你有嗎?戀愛的結果是結婚,這需要責任、坦誠,還有不摻雜念、毫無保留,這些你都具備嗎?你能無怨無悔地為我付出一切嗎?李江河就能!”
“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高鵬紅著眼。
陳雪嬌輕蔑地看了一眼高鵬,說:“我還有事要忙。”便徑直走了。
一個周末的早晨,李江河約陳雪嬌去遼河岸邊采野花,陳雪嬌爽快地答應了。
二人開車來到遼河南岸時,太陽剛升起不久,各種野花星星點點的嵌在綠色草叢中,河邊的樹林里,盡是布谷清脆的叫聲。陳雪嬌的老家在豫北農村,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小村子,村里隨處可聞布谷鳥的叫聲。兒時,她最喜歡追著布谷鳥的叫聲,自由自在地奔跑。眼前的景象,一下子把陳雪嬌帶回了童年,她竟不自覺地向著布谷鳥的叫聲跑去。
望著蝴蝶般“翩翩起舞”的陳雪嬌,李江河幸福地笑了,他覺得只要和陳雪嬌在一起,他就是幸福的。于是,他對陳雪嬌喊道:“雪嬌,你等一下我,我會把你這只美麗的蝴蝶抓到手的。”
陳雪嬌“撲哧”一下笑了,說:“不用你抓,我已經屬于你了!”
話音剛落,陳雪嬌包里的手機就響了,她掏出手機一看,來電的是高鵬,便毫不猶豫地掛斷了。李江河問是誰的電話,陳雪嬌毫不掩飾地說是高鵬,然后便小鳥依人般撲到李江河懷里,說:“我想聽你朗誦詩歌,想聽你寫的那首《風從北吹來》。”“好啊!”李江河站起來,聲音高亢地朗誦起來,“風從北吹來,風吹走了生活中沉重的嘆息……”他朗誦的聲音越來越高,激情澎湃。陳雪嬌看到,李江河早已淚流滿面,于是掏出紙巾,輕輕地為他將淚水拭去。
此時,真的有風從北吹來,二人在風中緊緊地擁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