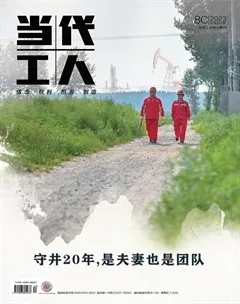生活=手藝=自信

外婆往事
我出生在上海,在工人新村度過了我的成長期。父輩大都是國有企業的工人,我是純正的工人子弟。第一次發現白紙黑字不那么可靠,還要從我家最年長的工人階級說起。
我的外婆是蘇北來滬務工的紡織工人,夏衍名作《包身工》寫的就是她那代人。外婆不識字,性格暴躁,身體強健,一口蘇北話,中氣十足,典型的“蘇北老太”。
我和外婆交流不多,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學校里學了課文《包身工》。我出于好奇,回來印證。那天放學后,我搬了個小板凳,坐在外婆面前把課文念給她聽,她一邊聽一邊笑。我問她當年是不是書上寫的那個樣子,她說打罵什么都是有的,吃得肯定也不算好,但吃不飽是不行的。“不讓我吃飽,打了也干不動啊。”以我外婆驚人的飯量,我倒是有點兒同情老板了。
那天,由《包身工》說開去,外婆開啟了回憶模式。“說被工頭從鄉下騙到上海來,別人不知道,我們肯定不是。我們當年來就是想為自己賺點兒嫁妝,以后是要回去的。結果后來打仗了,回不去了,也沒辦法。”
她又說:“那個瘦得和蘆柴棒一樣的女工,還被工頭逼著上工,這樣的事也沒在她身邊存在過。都病成那樣了,早就被送回去了。要是死在上海,工頭再怎么回鄉下招工呢?要是遇難者家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工頭回去是要被打死的。”這也可以想象,外婆在鄉下的親戚就很多。
外婆是幸運的,如果不是留在了上海,成了國有企業的工人,她那場癌癥多半會要了她的命。這也是她經常念叨的。但她也很惋惜攢下的積蓄,據說是一把金戒指。原來準備回鄉買地過清閑日子的,后來也就沒了。最后留了兩三個,做工很粗糙,卻挺有分量,在她去世后分給了子女。
外婆還有一個故事,我是聽舅舅說的,說是在一次全廠大會上,她作為老工人代表被要求發言。一開始憶苦思甜,還說得挺好,后來說著說著就抱怨這個那個的,旁邊的人趕緊攔住。所幸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個不識字的蘇北老太,對其他一竅不通,沒人在意。
我曾經想,如果夏衍和我外婆坐在一起話當年,也許兩個人會吵起來。以我外婆又暴又倔的脾氣,夏衍一定不是她的對手。畢竟,我就沒見到過她吵架輸給過誰。可惜的是,我沒有見過她在工廠里的英姿勃勃。
生活與生意
我的外婆,一輩子也沒有真正融入過上海,蘇北話始終如一,時不時還會懷念一下早年的夢想——在家鄉買地,過過清閑的日子。
家里真正的工人階級是我的父親。祖父因病早逝后,祖母沒有什么謀生能力,父親是長子,初二就輟學去工廠上班養家了。老爺子是電工出身,技術很精湛,很早就被評為技師,工作很順利。他從來沒有對工廠有過抱怨,但是也并不懷念計劃經濟時的“歲月靜好”。
晚年,他加入了公園老人的行列,對滿腹牢騷的“公園時評家”卻很是不屑。“買啥都要排隊、要憑票,還要送香煙,有什么好?”雖然他也不覺得當年的時光有多值得懷念,因為確實是“要送香煙”的。如果折算成現金,一條香煙可不是筆小數字。
知識分子擔心工人在市場經濟中吃虧而惴惴不安,這在父親那兒肯定也是沒有的。他是一個謙和樸實的人,對手藝很有自信。父親一輩子沒有對誰點頭哈腰、阿諛奉承,不管是廠里的領導,還是后來請他去工作的大小老板。別人對他也是客客氣氣的,確實如父親自信的那樣,手藝保證了他體面的生活。
一些文字把出賣“勞動力”描繪得何其卑微,至少我在手藝自信的父親身上從未看到過。
市場其實對父親而言,也不是什么陌生的東西。即便處于計劃經濟時代,工人群體中的“交易”也是很普遍的。從我記事起,父親就經常做幫人家修理電器、協助裝修等手藝活兒,回報大都是香煙——那個時代貨幣之外的硬通貨。
父親并不是所有的回報都會收。鄰居中有孤寡老人要幫忙,他總是很熱心,且不計回報。不過,該收的也是要收的,這類一概屬于“外快”。我問過他有沒有很摳的,他說有的,“太拎不清的,下次推掉就好了”。
鄉鎮企業興起后,“外快”升級為“私活兒”,回報就變成了現金。“外快”并沒有價目表,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成了約定俗成的行情。父親的師兄弟圈子經常會談行情,是各種信息的集散中心。同事尤其是師兄弟關系,是工人的天然組織,也就是俗稱的“小團體”。雖然“五湖四海,不搞小團體”之類的口號一直到我工作后還時有所聞,但顯然沒有什么用處。
師兄弟、老同事一起聚聚、串串門,怎么管得住呢?賺錢的外快多起來后,師兄弟圈子就更加緊密、牢固了。一來是手頭寬裕了,喝個小酒什么的就比較隨便。二來,這種聚會對于交換各種外快信息頗為重要,哪些企業開價高,哪些“生活”好接,哪些是“坑”,需要多交流。行情越多,就越是要“領行情”。在QQ、微信之前,我們的父輩就已經知道拉群了。
“生活”這個詞很有意思,他們從來不說那是“生意”,也不覺得自己在做生意。我父親一直認為做生意是靠頭腦的,做“生活”則是靠手藝,兩者并不是一回事兒。
但他確實不反感“做生意”。他有個徒弟很早就南下廣東,從打工到辦廠——在我父親看來,辦廠就是做生意了。他對那個徒弟很是稱贊,說他很聰明,“就適合做生意,只當工人可太可惜了”。我打趣父親,問他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他說:“我可不是那塊兒料。”然后還要補刀我,“我看你也不是。”我覺得在父親眼中,做生意其實也是一種手藝,只是需要特別的天賦。
強弱無絕對
我沒聽到過父親對請他去“做生活”的老板有過多大抱怨。他知道行情,并不可欺。最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的長短。父親不善講價,洽談的事都是他的搭檔也是他另一位徒弟包了。他很信任搭檔,長期合作,很是默契。
“生活”越來越多,就出現了中介機制。介紹“生活”原來是幫忙性質,有了中介機制后,也開始有了抽成。父親對中間人抽分子并沒有不快,他覺得幫忙介紹的人情也是要還的,算錢更清楚。但是抽分子要“上路”(上海方言,褒義詞,意為兼顧各方利益又得體)——這是師兄弟交流的重要信息,這也成了一種“行情”。
很多年后我接觸到了經濟學,發現自己早就被父親和他的伙伴們進行了“市場機制啟蒙”。博弈、交易信息的重要作用、各種價格因素,他們都應用自如。對他們而言,“接生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是“友情關注”比不上的天天實戰訓練。
糾紛也是免不了的,主要針對工作質量的爭議。通過中間人調停,一般都能順利解決。沒聽說干活兒不給錢之類的惡劣行為,老板應該是不敢的,這種壞名聲傳得快,下回找誰?
而且,工人也有工人的“套路”,有的“聰明人”很會給“生活”做手腳。比如給人家排線、安裝時留點兒隱患,用一段后毛病出來了,再去賺第二道錢。父親接手過這種“扯爛污”的善后,非常反感。畢竟市場之中,誰強勢、誰弱勢,并不是靠身份的標簽可以區分的。
公權力在很長時間里都沒有參與到這種“接生活”“做生活”的市場交易中。一定要說起作用的話,那就是隔一段時間就開始“不許接私活兒”的勞動紀律教育。
有時候會有一兩個“典型”被拉出來處理,無非是扣工資、批評之類的。我父親從來沒有過這種倒霉經歷,但是他也很不滿,抱怨“靠手藝吃飯,管啥閑事”“管又管不了,沒啥大用”。確實沒啥用,擋不住工人“接生活”的熱情。而且大家也不愿意多事,畢竟發狠擋人財路,工人跑到辦公室“尋相罵”也不是鬧著玩的。
在市場中“接生活”,工人的市場生存能力、環境適應能力和保護自身利益的行動力,比起很多群體都要高明——他們不“端著”,維護自身利益時沒有那么多自我設限,即便是在他們傷透心、險些徹底失去博弈能力的“下崗潮”中。所以,工人的市場處境和群體內部的生態是復雜的,用“出賣勞動力”“弱勢群體”簡單勾勒幾句,就成了“工人階級”的畫像,出發點雖好,結果卻南轅北轍。且網絡泛濫的“同情勞工”,在我看來甚至可以說是善意的冒犯。因為在大家學會微信拉群之前的很多年,我的父輩們已經很熟練地掌握了“群聊功能”。因為,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