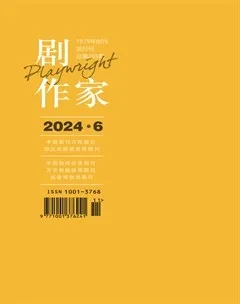走出、拆解、還原:論索福克勒斯悲劇隱性文本的架構與作用
摘 要:古希臘悲劇往往表現一個完整而統一的行動,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常采用人物行動主體性的隱現來生成顯性文本與隱性文本兩重空間,其共同作用于戲劇的完整性。以亞里士多德《詩學》為代表的戲劇研究往往關注文本話語,忽視了故事與事件,難以發現戲劇中隱形空間的建構。通過兩層判斷走出話語建構,故事被拆解形成以實際時間和因果關系排列的事件。依照細節對照與邏輯審視,挖掘出戲劇的隱性文本,進而剖解戲劇由文本顯隱兩重建構的復雜性及其作用于接受層而形成的信息張力。經由隱性空間的挖掘能拓展并延伸戲劇的時空與表現意蘊。
關鍵詞:故事與話語;隱性文本;索福克勒斯;古希臘悲劇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作為整體的悲劇必須包括情節、性格、言語、思想、戲景和唱段,其中情節是悲劇的根本與靈魂,而情節包含三大成分即突轉、發現和苦難,有造詣的詩人通過情節本身的構合達到恐懼和憐憫的效果,組織情節要注重技巧,使人即使不看演出而僅聽敘述也會達到此種效果[1]P64。《詩學》對情節高度重視,卻對戲景重視程度不夠,有將戲劇從現實語境中剝離僅關注文本的“案頭化”意味。依照熱奈特《敘事話語》三分法的劃分[2]P6,情節三大成分特別是突轉和發現,實際上是站在詩人對素材進行安排處理的敘述話語立場而不是站在故事立場上提出的概念。這與亞里士多德為了強調戲劇的認識功能而于《詩學》中展現出來的對創作技法與情節的關注[3]P160及古希臘人稱文藝創作為“寫詩”或“做詩”而不用graphein(“寫”“書寫”)這一現象所蘊含的將詩的產生視為制作或生產過程的觀念有關[1]P29。后世“三一律”的提出是對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誤讀與延伸[4]P65。其對時間一致和地點一致的強調實際上也反映出同亞里士多德對話語即顯性文本空間的重視的一致性。
《詩學》和“三一律”是戲劇研究的重要著作與概念,現今研究均借用其中相關術語與概念。本文不揣谫陋,意欲通過走出話語、拆解故事、還原事件,從時間及因果鏈的角度以古希臘索福克勒斯悲劇為例,探討亞里士多德和“三一律”著眼話語的視閾之外的隱性文本與空間對悲劇隱含意蘊的揭露。
一、隱性文本的挖掘:走出、拆解、還原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關注詩的組織與編排,因而全文的論述基點全部落足于既成的創作文本。文中提出突轉和發現是悲劇中兩個最能打動人心的部分,前者是指行動的發展從一個方向轉至相反方向,后者則為從不知到知的轉變[1]P89。概念中核心成分“一個方向”“相反方向”“知”“不知”,完全基于文本呈現的先后順序,而非以因果關系連接的現實時間順序,譬如《詩學》中提及的《俄狄浦斯》中的發現,其“知”與“不知”完全是以依照閱讀現有文本的順序對信息的判斷。
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判斷與分析是完全基于詩人加工后所呈現文本的顯性信息和順序的。唯一有所突破的點落足在悲劇的“結”和“解”上,他認為劇外事件,經常再加上一些劇內事件構成結[1]P131,這里包含純粹劇外事件構成結的可能性。亞里士多德提出悲劇由結和解組成,若依照此種思路,則悲劇實際上由結和解相加成為了一個大于由六要素構成的僅關注劇內事件的悲劇。如若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包含一個作者呈現的文本之外的空間內容,那么必然涉及顯性信息與隱性信息的討論。可惜的是,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并沒有再次議論悲劇的指涉事件的范圍問題。
讀者閱讀首先接觸到的是作家編制的文本即話語,閱讀順序也必然是依照文本文字連續出現的順序。這樣一種進入文本的方式符合人的思維慣性,也是文學需要對原生素材運用處理技巧進而來影響文學接受的自身原因。運用這種閱讀方式能把握住作者想讓讀者知道的信息,但是卻難以跳脫作者的主觀影響去把握隱藏在顯性信息下作者有意隱藏或予以深意的隱性信息。杰拉德·普林斯提出:“敘事的真正主題是特定事物的表現而不是事件本身;真正的主人公是敘述者而不是他的任何一個人物。同樣的,敘述者的不可信性迫使我們對他的很多陳述予以重新解釋,以認識與理解‘究竟發生了什么’。”[5]P14厘清文本“究竟發生了什么”,進而明確作品的信息顯隱,自然能夠體察作者這個最大的敘事者的文本處理技巧與意圖,進而挖掘出文本深層意蘊。
為便于后文論述,此處提出顯性文本、隱性文本的術語。這兩種概念是相對的,顯性文本指涉既成文本中作者直接表露的人物言語或行為談及或發生的信息;隱性文本則是囊括人物未詳述的、有引申空間的內容。隱性文本信息的挖掘能夠補充、證明甚至是逆轉顯性文本提供的信息,進而揭露戲劇作品的未盡之意或為進入作品提供新的角度。
挖掘隱性文本可以依照走出話語、拆解故事、還原事件的思維方式。首先,走出話語意味著讀者要有兩層判斷,一是對話語的判斷,二是有意識地對話語進行超越,而超越并非全然否認話語。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對詩結構方式的分析僅只停留在第一層判斷,還未達到對話語的超越。在走出話語后,讀者應當拆解話語,挖掘背后的故事,并盡量還原時間鏈和因果鏈。敘事學中常把話語認為是作者對故事處理之后的結果[6]P34,此種觀點僅只是在論述作品生成方式,并非涉及話語與故事的高低關系,更不能推而廣之,泛化到文學接受與解讀層面認為拆解話語是一種倒退與還原。最后,拆解完的故事形成一個個的顯性事件,讀者需要通過自身審視期間因果關系與微小細節,挖掘出因果不匹配、敘事有留白的空間,即為隱性文本。
二、順序拆解下的隱性文本
索福克勒斯的戲劇結構巧妙嚴密,亞里士多德于《詩學》中多次引作分析例證。但由于亞里士多德主要關注話語層,用發生、突轉等概念建構起文本中事件之間的聯系,戲劇中的隱性文本未受到足夠關注。探究索福克勒斯戲劇的隱性文本需關注因果關系、行為矛盾、敘事空白等因素。
在《俄狄浦斯王》中,文本話語力量明顯,索福克勒斯使用“倒敘式結構”,即故事由接近結尾處的高潮部分展開,在情節發展過程中追溯前因[7]P200,經由拆解與還原有利于實現事件發生順序的明晰化。通過拆解故事可以得到“拉伊奧斯家牧人把俄狄浦斯給報信人甲—報信人甲把俄狄浦斯給波呂波斯—波呂波斯收養俄狄浦斯—宴會上有人說俄狄浦斯不是波呂波斯的孩子—俄狄浦斯去皮提亞問神—俄狄浦斯離開科林斯—俄狄浦斯殺拉伊奧斯”的順序事件發展鏈。
在事件鏈間,敘事空白的一處為宴會中此人為何知道俄狄浦斯非波呂波斯的孩子。于宴會上發生這一故事的時間,知道戲劇秘密的知情人只有拉伊奧斯家牧人、報信人甲、俄狄浦斯養父母。首先牧人作為拉伊奧斯的侍從不可能在忒拜王宮活動,排除其泄露俄狄浦斯身份的可能,同時依照戲劇中報信人甲從科林斯來報告俄狄浦斯父死消息時,俄狄浦斯對報信人甲身份的詢問,俄狄浦斯明顯不認識報信人甲,宴會中的自然也不是報信人甲。結合報信人甲對俄狄浦斯提出為什么波呂波斯十分疼愛別人送的孩子這一問題的回答,即“他疼你是因為他以前沒有孩子”[8]P75,戲劇秘密極大可能是從波呂波斯處泄露。同時俄狄浦斯自身言行矛盾之處也使其于顯性文本中的言行可信度降低,譬如在俄狄浦斯回顧宴會事件時,其認為宴會事件“雖然值得驚訝,但不值得我念念不忘”[8]P58,但卻去了皮提亞問神,同時強調“瞞著父母”。假設“他們很生氣,責怪那人信口開河,辱罵了我”[8]P58是事實回溯,而非俄狄浦斯自我編制的內容,那么俄狄浦斯沒有隱瞞父母的必要,結合俄狄浦斯說話的當時,其既懷疑自己身份,又意圖以波呂波斯是自己的生身父親的認知說服自己的語境,這里俄狄浦斯的回憶敘述有敘述不可靠性的可能。
結合波呂波斯“以前沒有孩子”的愛的前提,以及俄狄浦斯宴會事件身份泄露與俄狄浦斯自身言說的嫌疑,俄狄浦斯或許已然懷疑自己身份,加之宴會事件的揭露,他離開了科林斯。實際上福波斯的預言反向告知了俄狄浦斯他不是波呂波斯的孩子,俄狄浦斯自始至終對自己是波呂波斯的孩子有所懷疑,又意欲探究自己的生父,因而在伊奧卡斯特最初安慰俄狄浦斯時他才格外不安。如若他深信自己是波呂波斯的孩子,那么他根本不可能懷疑自己是兇手而“六神不安心亂如麻”[8]P54。同時也是這種懷疑狀態解釋了俄狄浦斯在聽到波呂波斯死后僅只關心自身解脫,而非波呂波斯,以及所謂解脫后內心仍有的惶恐。
《安提戈涅》中部分事件時間鏈為“(日中前)克瑞翁宣布禁令(A)—(日中前)安提戈涅告知伊斯墨涅埋尸計劃(B)—(日中前)克瑞翁向長老告知禁令(C)”—“尸體第一次被埋(D)—(日中前)第一個白班守衛人發現尸體被埋(E)”—“(日中)安提戈涅埋尸(F)—守衛人抓住安提戈涅(G)”。其中存在關鍵的模糊時間鏈即事件D和A、B、E的先后關系。由于時間E中“第一個白班”暗示尸體被埋在下達禁令后第一個守衛人到達之前,同時安提戈涅于劇中只承認了第二次埋尸,那么存在三種可能情況即“D—A—B”和“A—D—B”“A—B—D—E”,前兩種認為事件D并非安提戈涅所為,后一種則認為未知者在B事件和E事件間隙完成D事件,那么未知者來自城邦君民,安提戈涅只是其中的可能者。因而第一次埋尸人有伊斯墨涅或其他城邦人的可能。如若是后者,則戲劇中展現情與法沖突中情的程度更深,第二次埋尸的安提戈涅只能是其中的代表,那么安提戈涅的受罰實際上就是作為民眾意志的替罪羊而承擔了集體的罪責。這樣的隱性文本挖掘,也呼應了伊格爾頓將《安提戈涅》同政治、倫理結合起來的“替罪羊式”解釋[9]P298。如若是前者,則伊斯墨涅性格更加突出,戲劇線索更有明線和暗線的雙線結構之效。戲劇是沒有敘述中介的藝術,人物直接對話某種程度上給了話語人表達的權利而非于敘述中被表達。不同人物的言語行為某種程度上類似于變換視角的第一人稱敘述,都有敘述的不可靠性。事件B中,伊斯墨涅的言語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自從我們的兩個哥哥在同一天里彼此死于對方之手,撇下了我們姐妹兩個之后,我還沒聽到過任何關于他們的消息,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自從昨夜阿爾戈斯軍隊逃走之后我便再沒有聽到什么新的消息,不論是令人鼓舞的還是令人沮喪的……什么大膽的計劃?你想要怎樣?……做力所不及的事實是完全不明智的……我不蔑視神律,但是反抗城邦我沒有力量……如果實在要去,你就去吧!有一點你可以放心:雖然去得魯莽,但在親人的眼里你是真正可愛的。[8]P245~251
此處伊斯墨涅對“沒有聽到任何消息”“沒有力量”的多次強調及對安提戈涅埋尸想法由勸阻到寬慰的前后態度轉變上,伊斯墨涅的話語有力圖擺脫自己的嫌疑、勸誡姐姐不要違反法律而受害、在發現姐姐態度堅決后的理解的解讀空間。同時克瑞翁說“剛才”看見伊斯墨涅在宮中精神失常,“剛才”只能是其審問安提戈涅之前。在不能斷定安提戈涅是否去埋尸的情況下,精神失常,克瑞翁認為伊斯墨涅有罪的判斷確有道理,同時戲劇中歌隊長詢問是否將伊斯墨涅處死以引出伊斯墨涅結局的部分,有給暗線的結束交代的意味。
由上可知,將情節發展結構破除,按照時間順序依次系聯,有助于發現事件間的邏輯不足、順序重置的可能性及敘事的空白,進而生發出具有多重解讀意味的隱性空間。
三、個體觀照下的隱性文本
由于戲劇需兼顧現實演出,文本容量不能過長,因而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往往會在順序記敘下加入插敘、補敘、預敘以豐富劇本體量而不至于占用過多主體事件發展空間。如若依照文本順序依次拆解話語,則有冗雜疊合的情形,因此在順序還原時,可以以某一人物為中心,關注其活動范圍的隱性空間建構。
《特拉基斯少女》由于得阿涅拉的“自殺”情節,常被納入索福克勒斯“自殺—救贖”模式中,被認為是“人類通過與神交換贖回自由的過程在悲劇形成中的反映”[10]P51。本雅明認為悲劇“自殺”式犧牲“不同于舊的以生命履行的義務,就在于它們并不回指上蒼的要求,而指英雄本人的生活;這些犧牲毀滅了他,因為它們與個人的意志并不相符,而只有益于尚未誕生的民族社區的生活”[11]P78。其將悲劇式自殺原因指向“與個人意志并不相符”的命運,但《特拉基斯少女》得阿涅拉的悲劇源頭并不在于命運,而在于自身強烈的主體意志。兩者的區別在于得阿涅拉讓赫拉克勒斯回心轉意的動機,如若這只是“發現—行動”式的自然反應,那這必然指向命運。
以得阿涅拉人生路徑為線索梳理事件鏈為“被人神追求—赫拉克勒斯英雄救美—嫁人生子—赫拉克勒斯外出留下蠟板—讓許羅斯找赫拉克勒特—從報信人處得到消息—戳破利卡斯謊言并得知真相—選擇寬容—用藥讓赫拉克勒斯回心轉意—發現被騙,兒子責罵,選擇自殺”。其間人物行為的矛盾之處在于得阿涅拉讓赫拉克勒斯回心轉意的設置不符合前文鋪墊。
首先得阿涅拉對兩人婚姻并不認可,其認為二人的結合帶給她的是無盡的憂慮,對宙斯的安排帶有埋怨的意味:
最后幸而評判人宙斯判得好,如果真是好的話。因為,自從我被赫拉克勒斯選中,和他結為了夫婦,就不斷地為他操心,可怕的事一個接著一個,一個黑夜帶來了憂慮,另一個黑夜的憂慮又進來擠走了它。后來我們生了孩子,他回來看看他們,好像一個農夫有一塊耕地在遠處,只播種時去一趟,收獲時再去一趟。生活就是這樣,帶他回家又送他離家,一直不斷地派他去為某一個人服勞役。[8]P536
其次赫拉克勒斯并不缺少侍妾,“赫拉克勒斯不是娶過別的女人嗎?誰也沒他娶的多”[8]563。得阿涅拉如若出于溫寧頓—英格拉姆所言的情欲動機[12]P218,就沒有必要經由已然抱有同情的伊俄勒觸發;如若出于劇中所言對青春的妒忌,同樣也不能解釋這個問題。
只有結合得阿涅拉前半生才能把握住問題的核心——得阿涅拉的人生全部是“被推進”的,美貌給她帶來不幸,讓她快速從少女成為少婦,而婚姻生活也長期處于“被通知”“被安排”的地位。因而戲劇中充斥著得阿涅拉對青春和少女的回顧與感慨。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中提到處女的敵視反應,“作為文明的結果,女人破貞不僅意味著永久地屈從于一個男人,而且還產生了對男人的原始敵視反應。這種敵意常常演變成一種病態,對夫妻雙方的性生活造成阻礙”[13]P169。得阿涅拉同赫拉克勒斯的婚姻關系理性約束大于感性情感。
得阿涅拉挽回赫拉克勒斯實際上是實現對伊俄勒的拯救。伊俄勒的美是她悲劇的開始,而得阿涅拉的美也是她人生逆境的開始。伊俄勒是少女青春的象征符號,因而整部戲劇里她沒有具體的言語與行動,得阿涅拉的選擇也就是以挽回赫拉克勒斯的方式實現精神自殺,完成對伊俄勒——少女青春的代表,自然亦是得阿涅拉自己青春的代表——的拯救與凈化,以及對自身的贖罪。戲劇中當得阿涅拉決心使用藥膏時,其言語具有隱喻意味:
我們還是進屋吧,我好交代你口信,還要讓你捎去相稱的禮物,要禮尚往還。因為,你帶了這么大隊的俘虜回來,讓你空著手回去,是不對的。[8]P565
因而將得阿涅拉的選擇視作“發現出軌—做出行動”模式忽視了人物的復雜性,是未觀照到零散分布但邏輯系聯的細節。
依照特定人物的行動順序架構事件,有利于將散于各處的信息綜合成完整的人物思維與行動鏈條,在探討特定問題時,更易把握住零散信息組合而成的隱藏空間與意義。
四、戲劇隱性空間的生成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人可以經歷許多行動,但這些并不組成一個完整的行動,情節既然是對行動的模仿,就必須模仿一個單一而完整的行動[1]P78。戲劇對單一完整行動的模仿,并非選擇順序式一一列舉,作家必然要對事件、故事時間進行打碎與重新編排,選擇最主要的完整渾然的事件構成顯性文本。文學的素材是有限的,文學處理使得文學文本呈現多樣性,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作家先制定一般性大綱,再給人物命名并加入穿插的寫作方式實際上肯定了作家的創制[1]P125。
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很少有所有場次都聚焦在某一個人物上,人物不斷地上場和退場,形成天然的顯性文本和隱性文本。詩人不將人物放置在言語地位時,人物行動和思想很難展現,因而每個人物的背后都存在事件暗角,譬如《安提戈涅》中開場聚焦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克瑞翁的命令、守衛人的行動居于暗角。第一場聚焦克瑞翁和守衛人,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居于暗角。一方面這種寫法是形成一個完全整體所必須的對細枝末節的省卻,但同時這種理解方式有些時候為詩人的寫作考慮不足以提供天然的庇護,劇中詩人未考慮到的細節或難以解釋的內容全部拋給隱性文本。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直言:“事件中不應有不合情理的內容,即使有,也要放在劇外,比如在《俄狄浦斯》里,索福克勒斯就是這樣處理的。”[1]P113但是由于前文多提及的亞里士多德對劇內劇外指設模糊,其依然未關注到由剖解還原事件而得來的作品隱性空間。同時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此種技法無論有意無意,都營造出人物的隱性空間,為戲劇提供更廣闊的解析內涵。
戲劇以對話體為文體特征,戲劇的對話語言一般同時具有敘述說明、場面連接、推動劇情發展、揭示人物性格、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等作用[14]P100。美國當代著名文論家J·希利斯·米勒評論《俄狄浦斯》時認為:“這出劇沒有通常意義的情節,所摹仿的‘行動’幾乎只是人們站在那兒交談或吟唱。劇中所發生的一切全都是通過語言,通過問答形式的對話來展示。”[15]P7讓人物通過言語推動事件,言語必然帶有個人視角的局限和價值判斷的偏差。雖然戲劇人物多為自說自話,但偶爾會出現詩人附身人物的現象,其間作者意志被強制賦予給人物,譬如《特拉基斯少女》中“眼前的事對我們是悲傷,對眾神是羞恥,對所有正在受難的人則是最大的痛苦”[8]P612。由此觀之,戲劇文體形式天然所致的介入性使每個人的話語與事實的對應關系形成了顯性空間和隱性空間。
言語與聚焦人物的顯隱讓戲劇本身形成了一個明暗不斷交替的結構復雜文本。如若立足于編制完成的話語去理解文本,把握住的僅有顯性信息,某種程度上拒絕了文本詮釋的可能性。對事件發生邏輯鏈真實的還原,與既定文本形成對照的張力,其一方面再現作家編制營造的結構與技法,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厘清認知迷霧,避免走向誤讀與誤解。不可否認,讀者接受誤解某種程度上可能亦是作家有意構制的結果,其自然也生成一種全新的表意模式。走出話語、拆解故事、還原事件,以結構主義技法構建原有素材的事件順序與因果聯系,是把握作家敘事全貌的一大技法,也為作品整體分析與意義架構探究提供切入點。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2]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90年
[3]耿幼壯:《永遠的神話——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批評、闡釋與接受》,《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5期
[4]譚君強:《“三一律”的時間整一與戲劇敘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5]杰拉德·普林斯:《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6]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7]安琦:《索福克勒斯悲劇與現代西方悲劇創作》,《學術交流》,2012年第9期
[8]索福克勒斯著,張竹明譯:《古希臘悲劇戲劇全集索福克勒斯悲劇》,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
[9]肖瓊:《誰是悲劇英雄?——〈安提戈涅〉的三種經典解讀》,《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9年第2期
[10]朱偉華:《歐洲兩種戲劇文本形態之比較》,《戲劇藝術》,2004年第2期
[11]瓦爾特·本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
[12]戴斯蒙德·約翰·科納徹,邢北辰:《對索福克勒斯〈特拉基斯少女〉的幾點看法》,《當代比較文學》,2021年第2期
[13]弗洛伊德著,廖玉笛譯:《性學三論》,北京:臺海出版社,2018年
[14]俞東明:《戲劇文體與戲劇文體學》,《浙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15]J.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
責任編輯 岳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