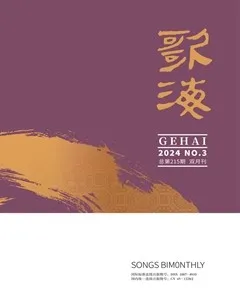《時間之野》中感性與理性的平衡
[摘 要]從藝術創作上看,散文集《時間之野》集中地展現了何述強作品的特點。他的感性思維通過多重意象的架構,延伸至理性思維,從而將藝術的真與哲學的真有機結合起來。這種架構的實施過程,體現出何述強對人性的關注,對審美的重視,以及對文學技巧的掌控能力。
[關鍵詞]《時間之野》;意象;感性;理性;何述強
藝術美不是一種單純的意識結果,而是復雜的心理認知,包含著感性思維和抽象思維。這樣的理念,是何述強一直堅持并將其融入個人創作過程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散文集《時間之野》是何述強多年創作的作品選集,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他的創作理念和哲學觀。黑格爾認為藝術的首要因素是理性內容,但他沒有看到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密切聯系,忽略了藝術美。何述強在他的作品中很好地打破了二者的界限,將感性認識在藝術加工中巧妙地延展至抽象思維,從而將藝術的真與哲學的真有機融合。
藝術創作也是一種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其要產生美,就一定涉及人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羅蘭·巴爾特認為一個作家的風格形成是多因素的,形象、敘述方式、詞匯都是從作家的身體和經歷中產生,并逐漸成為其藝術規律的1。何述強多年以來一直身體力行在民間開展走訪采風,這也使得他在創作手法上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同時也造就了他作品內容多樣化的風格,更注重文學的美感和人性。何述強的作品大多從情懷入手,時間的主線痕跡明顯,這決定了他不會單純地以自然美為目標進行創作,也決定了他的藝術創作必然具有感性與理性二重性。
一、美的創造與解析
在《時間之野》中,何述強用其超越地域與時間的獨特眼光,駕馭文字遨游在時間之野中。他的行文風格頗有蘇東坡那種揮灑自如的狀態,在敘事和結構上不拘一格,既可疏柳明月吟風流,也可以手執鐵板唱大江。在敘述故鄉往事的時候,他能夠娓娓道來,以透徹之眼行走在鄉愁之野,將一個個活生生的故人請到跟前來拉家常,一顆赤子之心躍然紙上。他對歷史典故的研究造詣深厚,古今人物信手即可拈來。他專注于杜甫的詩歌研究30多年,對佛老也頗有研究,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注定了他的文章必定不走尋常路,其氣勢如排山倒海一般,一浪高過一浪,連綿不絕。他的創作眼光很銳利,能站在不一樣的角度,往往三言兩語就抓住重點,幾句話就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他能從繁復的事件當中抓住那根龍筋,干凈利落地抽出來,也可以如庖丁解牛一般,在歷史時空中將最適當的細節剝離出來,一塊塊擺在案板上,任人賞析。其語言之凝練,敘述之從容,令人嘆為觀止。
何述強的寫作方式不是尋常能夠模仿得來的,他有他獨特的風格,這跟他的人生閱歷和情懷是完全融合的。他不避諱自己的不足,善于利用自己的特性,揚長避短。他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且完整的主體,不需要扼殺任何一種可能性。他在《老木棉》里說:“你身上的缺點會轉化為你的優點、你的個性,會成為你身上最寶貴的東西。”1
何述強的描寫和敘述不是機械的,而是從人對美的普遍認知的角度著手。他能夠用藝術家的眼光去發現時間和事物,同時又用人生的眼光去創作作品。善用某個節點是他散文的一大優勢,也是他散文風格敘事宏大的“藥引”。一地一景,一景一情,小到一個竹簡,大到幾千年的歷史風云,對何述強來說俯拾皆是,信手拈來。就如同他在《青磚物語》里牽掛的那塊青磚,恰到好處地站在了平衡點上。在他眾多的文章里面,也是總能恰到好處地設置這樣的“一塊青磚”。在《夢尋靈渠》中,老父親連接了時空的變幻,好比圍棋黑白世界里的粘法一樣,在靈渠古今之情中找到了平衡點,也讓何述強找到了個人情感的出路。《應說陽明舊草堂》則由一篇《瘞旅文》勾連起時間與地域的深度,讓何述強能夠肆意地發揮想象,從扶風山到黔靈山到黃金鎮,從理性到佛性到人性。《時間的鞭影》里的那根書包帶子,它沒有來歷也沒有結局,卻將束縛命運的隱喻和拷打人生的慘烈合二為一。
能夠將文字之美與山水之美、人文之美互相成就,也是何述強散文的一大特點。他對文字使用有一種新鮮感,他給文字下了他的定義:“本質和內核是寂寞的,并沒有熱鬧的成分,文字負載的東西和傳承的東西也是寂寞的。”2文字并不是生硬冷漠的,它只是寂寞而已,等待有人來發現它的美,而何述強就是能夠發現文字之美的一個人。他的文字是靈動跳躍的,不講究孤芳自賞,但同時他的文字又是陌生的。
經得起細品和回味的美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美,真正的美是需要用心去發現的,由外而內產生的美才是永恒的。這樣的美感如同桃花源那樣,“初極狹”,進入后“豁然開朗”。何述強深知藝術之美是需要創作的,同時也是需要被欣賞的。因此他認為寫好一篇文章需要沖波逆折,崇尚那種“道是平常最奇崛”的意境。他認為:“太流暢的語言無法給心靈以觸動,無法沖刷出人們閱讀中微妙的情感。”1在寫游記的時候,何述強對不同場面的記述不是走馬觀花,而是有電影蒙太奇那種移步換景的效果。他從城市走入山間,從山間小道進入原始森林,從原始森林走入靈魂洗禮之山水。穿越和尚崗的路和到達高山嶺頂侗天湖的路有什么不同嗎,他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浪費精力,不會事無巨細地去描繪景觀,他更愿意用寫意的筆法而不是工筆的細致。他在意的是事物深處,而不是停留在大家都能一目了然的面上。這讓他的敘述更有伸縮性,從而在意識上產生一種跳躍,有效地避免了產生審美疲勞。
就如同希臘古典悲劇那樣,何述強的內心之中也必須有一個英雄存在。這個英雄,有時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敢于獨自與命運斗爭到底;這個英雄,有時必須光照日月,成神成圣。這樣的形象,除了守著水碾的軍官以外,最好的對象就是關云長了。何述強沒有去宣揚他的功和圣,而是演繹能夠傳承2000多年的精神。他深知“手上的經典會慢慢模糊面容,直至被風吹散,被雨打濕,化為塵土”2,而能夠永久傳承的東西在人的心里,是一種信仰,是一種苦行,這也正是何述強堅持行走的。
在《烏雷的那場雨》里,何述強對“悲劇英雄律”是否存在提出了疑問,這同樣也是古希臘悲劇中的永恒話題。英雄是歡樂還是悲劇,這個矛盾而又統一的話題,在人類的歷史上無數次出現。這出人世間永恒的大戲,不單單是有馬援、黃庭堅、王陽明、蘇軾這樣的大人物作為其中的角色,更有蕓蕓眾生充當幕后點綴。跟死在水溝里的叔叔一樣,很多故事都以悲劇告終,但精神上又給人以喜劇的鼓動。《沉寂中的轟鳴》里那個守水碾的軍官,他來自何方,去往何處,他守著一具在荒僻處的水碾,他堅守的是什么,又或者是要跟什么抗爭,這都是需要我們去思考去探尋的真相,或許這個真相永遠沒有真相,但我們在這種現象背后,可以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美感和理性的樂趣。
尼采認為,不管現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之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和充滿歡樂的1。何述強所描寫的每一個生命,都不是悲觀沉淪的。母親費盡心血建造起來卻又被冷落的泥房,在物質上它已經死亡,但是它背后所蘊含的是母親的信念和“我”心的歸宿。那棵在刀斧下轟然倒下的椿樹,最終落到木匠叔叔的手里,必然會有另一種形式的生命價值體現在他人身上。叔叔倒在干涸的水溝里,沒有展現出所謂的慘狀,因為至少他在倒下去之前向刺竹揮動斧頭的瞬間依然是滿懷希望的。
何述強是勇于探索的,這種探索不僅是追求藝術上的美,也在思索人的復雜性和悲劇性。黑夜給了人們黑色的眼睛,但是有多少人用它來尋找光明?肉體可以被白日的喧囂同化,但孤獨的靈魂一定在黑夜里奔突吶喊。何述強白日里游走在世間的河流山川大街小巷,晚上放肆吟唱唐詩宋詞縱橫捭闔激揚文字。相對于光天化日,何述強更迷戀黑夜的舞臺,白日與黑夜的平衡點就在他的文章。他看到世界那“湮滅的真實”激蕩出“深夜的潮水”2。從《故山松竹月》《江流無聲》《夜訪鐵城》《拉住你的手,這樣的夜晚才不會迷路》這樣的文章,他以撲火之勢沖入黑夜當中去尋找美,在單調的黑色里面往外看,看出人的弱性——無奈、迷惘、虛無、悲涼。
二、意象架構下美的延展
何述強是善用意象的。
藝術美高于自然美。藝術美是經過人的創造,而后又被人接收的美。對于何述強來說,自然的概念涵蓋了未經過加工的認知的意象和具體的事物。
本雅明說:“歷史是一個結構的主體,但這個結構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時間之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時此刻的存在充滿的時間里。”3單薄的歷史意象是一種孤立的東西,沒有延續性也沒有美感。何述強的“歷史”,是感性的歷史,是具有美感的歷史,是多態的歷史。他善于運用歷史的意象構造成為我所用的藝術意象、歷史意象、藝術加工、理性分析。何述強的《靈渠夢尋》亮題即說“夢”,他將瀟湘二妃、杜甫、史祿、馬援,甚至不為人熟知的李渤、魚孟威、李師中、自己的父親等人的歷史意象悉數拋出,構造出歷史的厚度和故事的張力,造出一個靈渠“夢”,將延續的歷史由意象轉化為“夢”而成就藝術之美。同樣的手法也運用在《認出你的混茫》,只不過將人的歷史意象替換為物的意象,用一連串的石頭去豐滿兩塊石頭的故事。
抓住正確的意象才能形成架構,從而產生美。本雅明說:“過去的真實圖景就像是過眼云煙,他唯有作為在能被人認識到的瞬間閃現出來而又一去不復返的意象才能被捕獲。”1不論是歷史印跡還是自然景觀或者人的意識,要抓住某個意象重點,首先要有理性。何述強作為一個冷靜的旁觀者,他很明確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材料,準確無誤而且不帶任何偏見地從世間萬物的沉淀中發現那些線索。在《月光下的那團白霧》里,何述強敏銳地捕獲了三伯父和他創造的白霧,將其與明亮的月光交織構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夜晚,像是一幅用透視法結構的絕美圖卷,塵埃落定后不可復制。
朱光潛說:“單純的過去意象的復現是被動式的,文藝創作所用的都是一種‘創造性的形象思維’,就各種具體的意象進行組織安排和藝術加工,創造出一個新的整體,即藝術作品。”2沒有新的創造,就沒有美的生成。何述強在《來寶》的故事里,沒有單純地講述來寶這只只存在于人們口中的狗,而是用它的故事為曾祖父的形象做了素描,再通過狗與安寧寺的前世今生來映射以曾祖父為代表的群類人格。而在《青龍偃月刀守護的閱讀》中,何述強又賦予了關羽這個千百年來一直被書寫和分析的人物一種新的任務,他所守護的不僅僅是武圣的職責,還有守護文圣的意義。這是何述強的一種創造——將“發生在少數人的心靈深處”3的隱秘形象創造出來,將人們潛意識里的單純意象轉化為新的形象思維。
藝術作品,必定帶著感情。這種感情,一定是寄托在物質上,并朝向著一定的對象發生。新的形象一定是審美對象。沒有審美主體,或者以一般意義去聯想的關系去聯系所看到的對象,都不能形成審美的結果。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任何物質原本都是沒有感情的,如果我們不能對其賦予情感,那么就沒有完成藝術加工。何述強巧妙地將其所用的意象或物質都納入感情,一塊荒野的墓碑也可以有血有肉。物質沒有悲喜憂愁,它們“本身是無辜的……因為人類的參與,才使它們格外沉重”4。這是因為人們將自己的情感賦予其上,這才讓人性這個東西無處不在。
如同前述何述強游記中蒙太奇的形態那樣,他面對同一性質的物質時,總能發現其不同的意象,這正所謂藝術加工。本雅明說:“在時間中找到其豐富蘊藏的預言家所體驗的時間既不雷同也不空泛。”5不做簡單的重復,這也正是何述強對藝術美具有的獨特的創造性。他在《故鄉是每個人心中隱秘的事物》中認真地講述了自己的父親、母親、舅公、三伯父和弟弟的故事,這五個人所處時空不盡相同,但其中的關聯卻盤根錯節,同樣的親情其中不同的表現和牽系也千姿百態。
“不同年代時光的色彩和流淌的紋路,被揉進一個相同的時空里,相互輝映,縱橫馳騁。”1在一個藝術品里,其所展現在眼前的就是一個平面的時光,它隱藏起來的是五彩斑斕千變萬化的時光和空間。這樣的藝術架構層次足夠豐富,就可以由一而生萬物了。一間屋子在外面看到的只是磚瓦,只有走進去才能看到里面的雕梁畫棟,或許還有人有物。在何述強的作品里,時空感是無休止的,他絕不允許自己停留在某處,也不允許他的觀賞者被鎖在門外,更不允許他們被關進某個籠子里。為此,何述強努力地將自己變成一個有感情的講故事的人——將散文故事化。
本雅明在定義“講故事的人”的時候大致劃分了兩個類型:“人們把講故事的人想象成遠方來客,但對家居者的故事同樣樂于傾聽。”2這兩種類型的故事自然是各有特點的,但它們是否互滲交融決定了一個故事的寬度和厚度。何述強的很多文章有時候反而不像散文,都可以作為一個故事來看待,這就是他高超敘事能力的體現。何述強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他眼中的故鄉有兩種意象:一是時間上的,由遠而近;一是意識上的,由近至遠。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產生的情感和美感交織在一起,最終統一成了“死亡”這樣的歸途。“歸途是人生無法逃離的影子,牽系著我們所能承受的幸福和痛苦。前進的路有多遠,歸途就有多遠,前進的路有多艱難,歸途就有多艱難。”3何述強將同一個故鄉用不同的意象構造出幸福和痛苦兩個層次,寓示這個世界的矛盾之美,其意義如同哈姆雷特說出的“生存還是毀滅”的人生之惑,讓人不由自主地去再一次審視那個永遠沒有唯一答案的問題: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而歸途的那一頭,是我們的故鄉。”4物質可以湮滅,精神和意識又將去往何處?何述強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探索其中可能存在的答案。
感性與理性是兩個概念,不能直接畫等號。當感性影響到體驗對象的認知時,體驗對象才會發起理性回應,這種回應的程度與所受到影響的大小成正比。朱光潛說:“哲學家和科學家對這種來自感性認知的具體事物的意象卻用不同于藝術的方式加以處理。那就是用分析、綜合、判斷和推理,得出普遍概念或規律的邏輯思維。”5于是,當形成美的意象的架構達到足夠厚度時,我們便看到美向另一個更廣闊的天地走去了。
三、美與哲學的和諧之途
“光憑印象得到的東西,往往是膚淺的、表面的。”1在這里,何述強文字的哲學感就展露出來了,這是對形而上學的一種否定。宗白華認為:“藝術的模仿不是徘徊于自然的外表,乃是深深透入真實的必然性。所以藝術最鄰近于哲學,它是達到真理表現真理的另一條道路,它使真理披了一件美麗的外衣。”2在唯物主義觀里強調研究一件事物,不要形而上學,而要追尋事物的內涵本質。這種透露作者哲學思想之處如佛門壇宗的靈機一樣,一閃而過,而且并沒有在太多的文章里如此直白。若按照尼采對于藝術的觀點,何述強在其宏大敘事的面上就如日神一樣,究其根本的酒神現象就是在文字背后所若隱若現的深厚人文情懷。尼采說:“酒神藝術也要使我們相信生存的永恒樂趣,不過我們不應該在現象之中,而應在現象背后,尋找這種樂趣。”3這些也正是何述強希望讀者能看到和理解的真正的東西。藝術作品直接的主題是完全感性的、具體的,可以被人直接感知的,普遍人性問題不會是抽象的,它或許藏在暗處,但卻是可以通過感性的意象激發出來。
到了《用一根琴弦征服世界》,何述強說:“極致的美,往往來路是最簡單的。”4此時迎來的是一種大道至簡的思想,也是何述強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參悟的那種禪機道藏的結果,他看到了,他說出來了。在這里,中西哲學可以有機地統一起來。在唯物觀里,強調的是抓住事物的本質。這個本質不在于繁復,而在于核心要義。何述強曾經在一次文學講座上說過,老虎不會跟牛去比個頭,而是比身上的花紋。這也正是哲學所說的要從矛盾當中發現問題,從而解決問題。文學也是如此,必須抓住有意義的表達方式,而不是不厭其煩地去進行無意義的敘述。這樣的思想在《回到竹簡——忻城漫筆》里運用到文學創作上,他說要“用最樸素的方法擁抱每一個文字,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不聲不響”5。
文字的美感離不開一個人文化修養的高度,藝術的美感與一個人審美觀的高度有關,而理性的內涵則取決于一個人有沒有思想。尼采認為,違背藝術的真正目的,必然導致對傾向的崇拜6。藝術本身沒有傾向,但是人有。藝術呈現給我們的是美感,其中的情感是我們每個人的思想產生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何述強所講述的是自己的“故事”,讀者讀到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寂寞的墳碑》里的“百二堆”與《應說陽明舊草堂》里的“百二堆”,《仿佛一道電光》里的伏波廟與《烏雷的那一場雨》中的伏波廟,和尚崗的茶樹與高山嶺頂侗天湖的茶樹,同質而不同感。這是何述強在運用意象進行藝術構造時注重不同情感可以帶來不同認知的結果,就如同哭泣可以是喜悅的也可以是悲傷的。
沒有一定的厚度,文學就無法容納下美的瑰麗,因為冰山下的三分之二和浮冰水線上的那一截斷然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厚度,往往就是何述強散文的光芒所在。“簡單的文字,若要永久,必須具備深刻的思想內涵,以及豐富的情感。一切泛濫的表達,像洪水一樣,很快就會消退,只留下黃泥水蕩過的痕跡。”1
我們如何去定義美?美應該是能夠激蕩一個人情感產生某種興奮的事物,不論這樣的情感和興奮是歡樂或是憂傷,還是一種長久的思考。美是以調解的身份進入矛盾之中,因此它對感性和理性都具有一種凈化的作用。為了尋求這樣的美,創作者就必須到自己的心靈深處去探求這世界的投影,與自己的靈魂徹夜長談,在找到美的那一刻,他必須“與寂寞、孤獨、荒涼結緣”2。也只有這樣,何述強才可以把他所見所憶所想的事物真實地展現出來,這也是他在敘述上“真”的體現。他毫不避諱對生命存亡的豁達態度,理解一進一退就是人生必然的動作,也承認人人都有脆弱的堤岸,這是何述強在其散文中創造美以調和人生矛盾達到和諧的過程。
文學從來都不是一具僵硬的尸體,它更應該是一個站在讀者眼前活生生的生命,甚至還打扮得花枝招展,這是一種生命的樂趣,不管這個生命是歡樂的還是痛苦的,它所代表的都是這個世界永恒的樂趣。何述強的散文始終離不開事物中蘊含的生命這個基礎,他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結構,跟他生命的情緒表現交織起來,融合成為一種境界。生命不是人生的最高價值,而是創造最高價值的介質。因此在何述強的散文里,不管是眾多的人物,還是朝火而來撲窗的飛蛾,或者山中的茶樹,甚至是一只蚊子,它們都有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都帶著何述強那種強烈的人文價值觀的個人色彩。當借三伯父之口說出“蚊子也要生活”這句話的時候,何述強在人文關懷上就有了一個新高度的升華。《死亡故鄉》里短壽的小叔叔一輩子在鄉下,斧頭伴他生伴他死,在別人眼里他意外身亡充滿了不幸,但寂寂的一生也同樣充滿著他的樂趣。那棵椿樹用自己生命的價值,將年逾花甲的農村老漢與木匠叔叔勾連起來,創造了生和死兩種矛盾的價值。
宗白華認為文藝從它的左鄰“宗教”獲得深厚熱情的灌溉,而從它的右鄰“哲學”獲得深雋的人生智慧、宇宙觀念1。何述強對儒釋道三教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這也讓他能夠從容地走進哲學的大門。在何述強的散文里,理性、感性和人性始終貫穿其中,由大及小,由小彰大。他的文學藝術不是簡單地對自然現實的模仿,而是基于自然現實的一種升華,作為他對此種現象一種征服性的掌控。這種冷靜的能力,來源于他那雙“與其他人相比更悲涼的眼睛”2對生活的透視,使得他可以從容游走于美和哲學之間。
何述強走的這條路,是孤獨的,難以復制的。別人或是跟在旁邊但是插不上話,或是跟在后面卻始終差那幾步。他的寫作是一種儀式,是那種穿透身體和靈魂的獻祭。他的信念就是,“我們的生命中,總需要保留一些遺世獨立的儀式”3。
結語
羅蘭·巴爾特認為,如果作家的寫作使作家處于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就不可能產生現代的文學杰作4。通過對意象進行加工重構,何述強完美地完成了從物質到美到哲學的延展,解決了文學創作中現實與精神難以統一的矛盾。他沒有深沉地故弄玄虛,只是把個人的感性思維通過高超的敘事手段,將抽象思維以審美結果的方式展現出來。他認為文學要脫掉亂七八糟的東西,只留下血肉與心靈。這也是文學具有美感的重要步驟,而美感的核心要義就是真,包括藝術和哲學。
- 在文學里形而上的東西只能當作定義,而不能認為本質。文學如果不能給人以真實的情感交流,那它只能算是文字。何述強的創作沒有停留在表面,他也不迎合那種堆砌華麗詞藻的手法。他的文字樸素,更講究藝境。在文學創作上,何述強是懂得揚長避短的,他對每一個文字都有感情,對他要還原的每一個意象都有情緒。正是如此,他的文章才能有血有肉,帶著快感或痛感,還有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