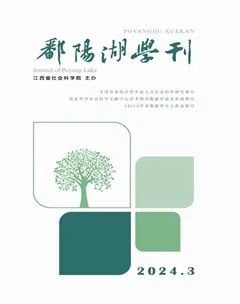去增長意味著什么:澄清幾個問題
[摘 要]去增長是指有計劃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量,旨在通過減少不平等現象和提高人類福祉的方式,使經濟與生物世界恢復平衡。在過去幾年里,雖然該理念在學術界和社會運動中引起了極大關注,但是初次接觸這個理念的人還是會遇到許多問題。文章試圖澄清三個具體問題:一是明確“去增長”的含義,并論證去增長框架是一種資產而非負債;二是解釋去增長與經濟衰退之間的根本區別;三是確認去增長主要集中于高收入國家,并探討去增長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
[關鍵詞]去增長;新冠肺炎疫情;經濟衰退;全球南方
引 言
目前,人類文明正在突破一些關鍵的地球極限,面臨著多維度的生態破壞危機,包括危險的氣候變化、海洋酸化、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崩潰。①與人類世的一般說法相反,這場危機并非由人類自身引起,而是由一個特定的經濟體系造成的。這是一個建立在永續擴張基礎上的體系,它為少數富人謀取過多的利益。②
經濟增長與生態破壞之間的關系現已通過實證研究得到充分證明。在主流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我們必須追求永續增長,③因此必須使GDP與生態破壞影響脫鉤,實現“綠色”增長。遺憾的是,綠色增長希望渺茫。沒有任何史實表明GDP與資源使用(就物質材料而言)能夠長期絕對脫鉤,而且現存的所有模型都預測,即便在樂觀條件下也無法實現這一目標。①如果我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就能實現GDP與碳排放的絕對脫鉤。但如果經濟繼續以正常的速度增長,則難以很快實現1.5°C和2°C的碳預算。更多的增長意味著更多的能源需求,而更多的能源需求使我們在所剩不多的時間里用可再生能源來滿足這些需求變得更加困難。②
鑒于此,科學家和生態經濟學家越來越多地呼吁轉向“后增長”(post-growth)和“去增長”(degrowth)策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年的特別報告指出,在沒有投機性負排放技術的情況下,保持在安全碳預算范圍內的唯一可行方式是讓高收入國家主動放慢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步伐。③減少物質使用量(material throughput)可以減少能源需求,從而更容易實現向可再生能源的快速過渡。這種方法在生態學上也是合乎邏輯的:減少物質使用量不僅有助于我們應對氣候變化,還可以消除對地球的其他極限造成的壓力。這被稱為“去增長”。
去增長是指有計劃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量,旨在通過減少不平等現象和改善人類福祉的方式,使經濟與生物世界恢復平衡。④必須澄清的是,去增長不是要減少GDP,而是要減少使用量。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才是最重要的。當然,還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降低使用量可能會導致GDP增長率下降,甚至GDP本身的下降,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安全、公正的方式對待這一結果。這就是去增長的目標所在。雖然去增長理論在學術界和社會運動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初次接觸這一理念的人還是會遇到許多問題。下面,筆者將對其中有關概念和術語的問題,有關經濟衰退的問題,以及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和南北分歧的問題逐一進行探討。
一、“去增長”術語
許多反對“去增長”的理由都與這個詞本身有關。有些人擔心去增長會引起混淆,因為它實際上并不是增長的對立面。當人們說“增長”時,通常指的是GDP的增長。因此,人們可能會合理地假設去增長也專注于減少GDP。由此,去增長的支持者需要不斷澄清去增長不是減少GDP,而是減少材料和能源的使用量。這似乎會產生不必要的問題。
但事實上,這里的問題源于“增長”一詞,而不是去增長。實際上,人們追求增長并不是為了增加一個抽象的數字(GDP),而是因為他們想要消費或做更多的事情,這當然需要使用更多的物質和能源。因此,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談及增長時,他們實際上指的是物質和能源的增加(具體而言是商品化的物質和能源的增加),盡管這并沒有直接聲明。對GDP的癡迷掩蓋了這一事實,它使得增長看起來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如果GDP的增長沒有伴隨著物質消費的增加,那么人們就不會去追求它(如果高收入不能讓你擴大軍費開支,或購買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汽車,或雇傭人為你做事,那又有什么意義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減少材料和能源使用量(以及減少商品化模式)為重點的去增長,實際上與增長正好相反,并的確澄清了增長本身的真正含義。
現在,有人可能會問,當你說“我們想要減少能源和物質使用量”并避免混淆時,為什么要使用“去增長”這一詞呢?這有幾個原因。首先,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減少能源和物質使用量很重要,但他們認為這可以在繼續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事實上,他們甚至可能認為更多的增長最終會導致使用量的減少)。我們需要運用某種方法將去增長立場與這種標準的“綠色增長”假設區分開來。如果我們接受不太可能實現綠色增長的實證研究,那么我們就必須看到使用量的減少將會影響GDP本身,必須專注于如何重組經濟,以便以安全和公正的方式進行管理。因此,“去增長”是一個簡單而方便的術語,它使我們能夠澄清利害關系,并集中注意力于所需之處。
去增長的支持者經常認為,將“去增長”這個詞視作“導彈”(missile)一詞是有用的。很明顯,對于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永續增長存在問題。對于他們而言,去增長似乎是對生態危機的直觀正確的反應,他們可以立即支持這一觀點。其他人對這個詞的第一反應是消極的,盡管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它還是有用的,因為它挑戰并顛覆了人們對經濟應該如何運行的假設,質疑了一些通常被視為自然和美好的事物。在許多情況下,最初的消極反應讓位于沉思(高收入國家真的需要更多的增長嗎?),然后好奇(也許我們實際上可以在更少的使用量甚至更少的產出下蓬勃發展?),再調查(相關的實證證據是什么?),最終會導致人們改變他們的看法。使用這種具有挑釁性的術語并不會阻礙、反而會促使這種智力上的轉變。試圖避免挑釁或者對增長持中立態度營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有問題的假設仍是未知的、未經檢驗的,這有利于禮貌的交談和協定,但并不是推進知識的有效方式,特別是在利害關系如此之大的情況下。
有些人對使用“去增長”術語有顧慮,因為它是一個消極的術語。但只有當我們從更多的增長是好的、可取的假設出發時,它才是消極的。如果我們試圖挑戰這一假設并提出相反的觀點(更多的增長是不必要且有害的,如果我們放慢速度會更好),那么“去增長”就是一個積極的術語。以“殖民化”(colonization)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這兩個詞為例:我們知道,那些從事殖民活動的人認為殖民化是一件好事,因此,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去殖民化似乎是消極的,這是過去500年來歐洲的主流觀點。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挑戰主流觀點,因為主流觀點是錯誤的。的確,今天我們認為這種反對殖民化的立場是正確的和有價值的。我們反對殖民化,并相信沒有殖民化的世界將會更好,這不是一個消極的愿景,而是一個積極的愿景,一個值得我們共同擁有的愿景。同樣,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向往一個沒有增長的經濟,就像我們向往一個沒有殖民的世界一樣。
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觀察這一點,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增長”一詞已成為一種宣傳術語。事實上,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一個精英積累、公地商品化以及人力和自然資源占有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帶有殖民性質,通常對人類社會和生態具有破壞性,并被掩飾為增長。增長聽起來自然而積極(誰可能反對增長呢?),因此,人們很容易被說服去接受它,并支持能夠產生更多增長的政策,否則他們可能不會這么做。在葛蘭西的意義上,增長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是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核心原則。“去增長”一詞強大而有效,因為它發現了這個陷阱,并拒絕了它。去增長呼吁扭轉增長背后的過程:它要求去積累(disaccumulation)、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以及去殖民化。
二、去增長vs經濟衰退
關于去增長的另一個常見問題與經濟衰退有關。實際上,當新冠疫情(COVID-19)引發的經濟衰退來襲時,一些去增長的詆毀者指出,這就是去增長將會是一場災難的一個例子。在很大程度上,這不是一個善意的論點,而是一種有意的誤導,因為即使粗略地閱讀有關去增長的文獻,也不可能犯這個錯誤。事實上,去增長在各個方面都與經濟衰退相反。我們用不同的詞來形容它們,因為它們表達不同的意思。以下是值得注意的六大主要區別:
(1)去增長是一項有計劃的、連貫的政策,旨在減少生態破壞、減少不平等并改善福祉。經濟衰退不是計劃好的,也不以上述任何一種結果為目標,它并不是為了減少生態破壞的影響(盡管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當然也不是為了減少不平等和改善福祉——事實上,它的目標正好相反。
(2)去增長在減少經濟活動方面采取了一種區別對待的方法。它試圖減少具有生態破壞性、對社會不那么必要的生產(即生產SUV、武器、牛肉、私人交通工具、廣告以及計劃性的報廢燈),同時擴大醫療、教育、護理和娛樂等社會重要行業。相比之下,經濟衰退不會明智地加以區分,它往往會破壞社會上重要的行業,同時賦予社會上不太必要的行業權力。例如在新冠疫情危機中,學校、娛樂設施和公共交通都受到了負面影響,而亞馬遜(Amazon)卻在擴張,股價也在上漲。
(3)去增長出臺了防止失業的政策,甚至還出臺了改善就業的政策,例如縮短工作周、推行帶有最低生活工資的就業保障,并推出再培訓計劃,將人們從夕陽產業中轉移出去。盡管總體經濟活動有所減少,但去增長顯然側重于維持和改善人們的生計。相比之下,經濟衰退導致了大規模失業,許多普通人失去了生計。
(4)去增長旨在減少不平等,更公平地分享國家和全球收入,例如實施累進稅和最低生活工資政策。相比之下,經濟衰退往往會加劇不平等。新冠疫情危機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即一攬子應對措施(量化寬松、企業緊急援助等)讓富人(特別是資產所有者)變得更加富有,億萬富翁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而大多數人都在遭受損失,50%最貧窮的人每天損失44億美元。①
(5)去增長尋求擴大普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健康、教育、交通和住房等,以便減少人們過上富足生活所需的基本商品。相比之下,經濟衰退則通常采取削減公共服務支出的緊縮措施。
(6)去增長是實現向可再生能源快速過渡、恢復土壤和生物多樣性以及扭轉生態崩潰計劃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在經濟衰退期間,不管付出怎樣的生態代價,政府通常會放棄這些目標,轉而將一切精力集中于恢復經濟增長上。
我們對經濟衰退與去增長有不同的說法,是因為它們具有不同的含義。當依賴增長的經濟體停止增長時,經濟衰退就會發生: 這是一場災難,會破壞人們的生活,加劇不公正。而去增長呼吁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一個從一開始就不需要增長的經濟,即使在使用量下降的情況下,它也能伸張正義、增進福祉。
三、去增長與全球南方
有些人擔心,去增長的支持者希望看到去增長在所有國家中都得到普遍應用,這將是有問題的,因為很顯然,許多貧窮國家實際上需要增加資源和能源的使用,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事實上,去增長的支持者清楚地認識到,需要去增長的是高收入國家(或者更具體地說,是那些人均占有率超過地球邊界很大一部分的國家②),而不是其他國家。同樣,由于去增長重點在于減少資源和能源的過度使用,因此它并不適用于那些沒有過度使用資源和能源的經濟體。
這就引出了去增長政策的一個重要含義。絕大多數的生態破壞是由全球北方國家的過度消費造成的,但對南方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們可以從排放物和物質開采兩方面來看這一點。其一,北方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2%,超過了地球的安全邊界,③但南方國家卻遭受了絕大多數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害(就貨幣成本以及生命損失而言)。其二,高收入國家依賴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量資源凈占有(相當于其總消費量的50%)。換言之,北方國家的資源消耗對生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南方國家中。④
因此,在排放和資源利用方面,北方國家的過度消費依賴于殖民化模式:對南方國家大氣公域公允份額的侵占以及對南方國家生態系統的掠奪。從這個角度來看,北方國家的去增長代表了南方國家的非殖民化進程。在某種程度上,北方國家將南方國家的社區從大氣殖民化和物質掠奪主義的壓力中釋放出來。
盡管如此,一些人擔心北方國家的去增長可能會對南方國家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畢竟,許多全球南方經濟體嚴重依賴于向北方國家出口原材料和輕工業制成品。如果北方國家的需求下降,那么他們將從哪里獲得收入呢?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它建立在一個有問題的邏輯上。也就是說,即使它會導致生態破壞,對南方國家造成嚴重的影響,北方國家的過度消費仍必須繼續增加,因為這對南方國家的發展是必要的,最終也是為了南方國家自身的利益。這一論點呼應了殖民主義時期經常提出的論點,即殖民者的掠奪和剝削最終對被殖民者有利。例如,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為血汗工廠喝彩》的文章中指出,血汗工廠是幫助人們擺脫貧困的最佳途徑,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血汗工廠;如果我們關心窮人,就不應該抵制血汗工廠的產品,而是應該多消費這些產品。這個論點中的謬誤不需要指出。顯然,減少貧困的最佳途徑不是更多的剝削,而是更多的經濟正義:南方國家為全球經濟提供的勞動力和資源應該得到公平的價格。沒有人會認為一家美國公司每天付給美國工人2美元是減少美國貧困的好方法。我們堅持認為,減少貧困需要支付最低生活工資,但出于某種原因,這種邏輯并不適用于南方國家的工人,因為這可能將降低北方公司對南方國家勞動力和資源的依賴及其國家的累積盈余率(the rate of surplus accumulation)。換句話說,為南方國家伸張正義(公允的勞動力工資以及公允的資源價格)將意味著北方國家的去增長。我們應該接受這一結果。事實上,北方國家放棄追求增長將是有益的,因為它將消除北方政府、公司不斷施加的壓力,以壓低南方國家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北方國家的去增長為南方經濟體創造了空間,使其能夠擺脫作為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出口國的強制性角色,轉而專注于發展主義改革:構建以主權、自給自足和人類福祉為重點的經濟體。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之前,這是大多數全球南方政府在后殖民時代的最初幾十年,即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所采取的做法。①結構調整試圖瓦解整個南方國家的發展主義改革,以便為北方國家的積累創造新的天地。在去增長的情況下,這種“修正”的壓力將得到改善,并且南方政府會發現自己更自由地追求以人為中心的經濟。②很明顯,在這里,北方國家的去增長代表著南方國家的非殖民化。
當然,全球南方國家不需要也不應該等待非殖民化,他們可以自己擺脫枷鎖。在這里,筆者想到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脫鉤”概念:拒絕將國家發展政策服從于北方國家資本的要求。例如,全球南方各國政府可以集體組織起來提高勞動力和資源的價格,并提出更公平的貿易和金融條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取得更民主的代表權(就像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對新國際經濟秩序所做的那樣)。這些想法在今天的后發展話語中得到了體現。除了拒絕新自由全球化的原則之外,后發展思想還拒絕了(由殖民者和國際金融機構提出的)追求GDP增長是為了自身利益的這一觀點,相反,它更傾向于關注人類福祉。①
無論通過哪種方式,南方國家的去殖民化按照此方法可能會導致北方國家的去增長,這一點千真萬確。目前,高收入國家通過不斷對南方國家凈占有(土地、勞動力、資源和能源)以及通過不平等的交換來維持高水平的收入和消費。換句話說,它們試圖將勞動力和資源的價格壓低到全球平均價格以下。②這是殖民關系基本原則的延續,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占領。結束這種剝削關系將意味著要么結束凈占有模式,要么結束不平等交換,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導致經濟精英的累計盈余率下降,并減少由北方國家積累所推動的增長,但它將造福于全球南方國家的社區和生態。
(原載于Globlizations, vol. 18, no. 7, 2021. 此次翻譯已獲作者授權,版權歸作者所有,內容無刪減。)
責任編輯:胡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