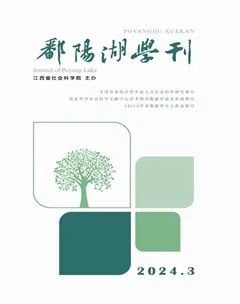華茲華斯的潮汐農事詩學
[摘 要]由于農事詩常表現人類因自身需要而對原始自然進行干預、改變或開發,生態批評家往往對其評價不高,而對田園化傾向強烈的浪漫主義詩歌情有獨鐘。威廉·華茲華斯寫于1798年的《丁登寺旁》便是生態批評家所贊美的田園詩的典范之作。然而至少在對該詩作的分析中發現,田園與農事之間或許存有更多的延續性和接壤地帶,二者或能合為一體。不僅如此,《丁登寺旁》所蘊含的潮汐元素著力于表現人們面對潮去潮來的節奏時應如何棲居、如何響應、如何思索。該詩依循潮起潮落的節奏,以歸來為起點,以在展望中離去為終結,詩的弧形運動軌跡因此具有了潮汐性質,這一形態在詩的終結時仍連綿不絕。欲走還留的意趣在詩的末段又得到了重申,其在開篇的回聲延續著詩的周期性、潮汐性的模式。
[關鍵詞]華茲華斯;潮汐農事詩;田園詩;《丁登寺旁》;生態批評
大衛·法里爾(David Fairer)發現,生態批評“對詩作的田園化解讀情有獨鐘”,這便“部分地導致了這樣一種結果,即只要因人類自身需要而對原始自然采取的干預、改變或開發都遭到了妖魔化”。①他談到“綠色浪漫主義”之所以對18世紀大加鞭笞,正是因其與人定勝天的啟蒙思想緊密相關,其結果是:“在生態批評家的心目中,如果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詩歌體裁,那就得算農事詩了。”②在他看來,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寫于1798年的《一次旅行時重訪懷河兩岸,在丁登寺上游數英里處吟得的詩行》[“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常稱作《丁登寺旁》③(“Tintern Abbey”)],便是生態批評所贊美的田園詩的典范之作。
(華茲華斯)或許對“隱沒在灌木和樹林之中”的“叢叢果園”是喜聞樂見的,但這露出了農業經營不善的苗頭。真正懂行的是約翰·菲利普,他明白自然的豐產是需要打理的,蘋果樹是需要呵護的。①
約翰·菲利普(John Philips)寫的《蘋果酒》(“Cyder”,1790)便是一首農事詩,其中就包括對果園的管理指導。法里爾在討論羅伯特·多茲利(Robert Dodsley)的《農業》(Agriculture,1753)時亦有類似觀感。多茲利對扎籬笆的熟稔,表明他意識到“萬物關聯的環境”發自“基于經驗的本地實踐精神”。②相比之下,在浪漫主義文學中:
“共生”(symbiosis)只是隱喻,并非一種生態機制。而與自然對應更多的是熟練編扎籬笆,而非“像是有高度融合的東西”。③
以上兩句,每句都包含了鮮明的對比,第二句最后的引語來自《丁登寺旁》:“崇高思想的歡樂,一種超脫之感/像是有高度融合的東西。”④在法里爾看來,浪漫主義詩歌(而不僅僅是生態批評對此類詩歌的解讀)就是在歌頌人與自然的聯姻關系,同時卻忽視了人與環境在實踐與身體層面上的互動。
華茲華斯的詩作名動天下,并成為生態批評的試金石,輕而易舉地被法里爾拿來作為例證,用以在浪漫主義田園詩與18世紀農事詩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然而至少在對華茲華斯這一詩作的分析中可發現,或許就在二者之間存有更多的延續性,而并不像法里爾所說的這么涇渭分明(誠然該文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華茲華斯對菲利普、約翰·戴依爾(John Dyer)、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等18世紀農事詩傳統代表人物的欽慕是有目共睹的。⑤布魯斯·格拉弗(Bruce Graver)詳細記述過華茲華斯對充滿維吉爾風格的農事詩的興趣。不僅如此,格拉弗認為華茲華斯還對他所繼承的傳統進行了改良。他把華氏寫于1800年的詩作《邁克爾》(“Michael”)視為一種“新型農事混合體”,即“農事田園詩”(a georgic pastoral)。⑥筆者認為,《丁登寺旁》則提供了華茲華斯對田園與農事同時進行再塑的另一例證。盡管該詩已成為“田園化傾向”的典型代表,但實則對田園詩學既有贊同又有所抗拒。與此同時,它也質疑了18世紀農事詩所表達出的關注重點與價值觀。因此,《丁登寺旁》的創作革新對法里爾的假說提出了挑戰,后者所持有的是關于浪漫主義時期的寫作及其在生態批評視角下的解讀。總之,對于法里爾關于生態批評的觀點,有很多學者并不茍同。⑦
約翰·巴雷爾(John Barrell)歸納了農事書寫的特點:“將自然設想成吝嗇寡情的形象,出產果實時總是心有不甘,其狂暴的脾性隨時都會顯露,對我們深懷敵意,因而我們必須通過勞動來降服它。”①雷切爾·克勞福德(Rachel Crawford)也有類似的描述,她在維吉爾和彌爾頓的詳細描寫中找到了農事詩的基本主題:“在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里,勞動原本是輕松自在的,可人們卻遭到了驅逐……艱苦的勞動正是被從花園逐出的后果。”②維吉爾的《農事集》最有力地驗證了這一點。在第2卷的尾章,農牧業給人們帶來了城市或宮廷生活所不能比擬的快樂——自然的回報比任何人類雇主都要慷慨;不過,自然在《農事集》的大部分篇章里都是與人類作對的,人的生活便是一場與之不懈纏斗的戰爭:
于是一切均聽命于天,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除非他持槳奮力逆流而上,偶有懈怠,洶涌的河流便要令他覆沒。③
格拉弗引用這一名喻并評論道:
在維吉爾看來,這一比喻描繪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我們總是險象環生,因而必須勞作不止,只為生存。④
同引此詩的大衛·法里爾將其形容為“投往自然的一瞥,這樣的自然比起其他任何仁善的體系來,都更使人捉摸不透且感到孤立無援”。⑤
不過有跡象表明,華茲華斯也能體會到一種更加仁善的世態,其中勞動或仍然成為——至少有時如此——“輕松自在”的源泉。有鑒于此,格拉弗便提到過華茲華斯在《序曲》里所描寫到的那種“少年人的消遣”(boyish pastimes):
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其自身所特有的管控力,仿佛通過消遣,少年人的精神便可以得到訓練或管控,就如同維吉爾詩中的農夫管控他的田地一樣。華茲華斯似乎在暗示,玩耍便是童年的勞動。⑥
筆者的觀點是,《丁登寺旁》揭示出華茲華斯對勞動和玩樂的同步呈現,這在童年及成年時期都是如此。由于(且只要)成年人能夠在成熟的自我中保留兒時的感覺,那么田園和農事或能合為一體。不僅如此,通過縱觀《丁登寺旁》,看華茲華斯如何重涉維吉爾的河流這一明喻,對此論點便可以一目了然。
該詩初載于《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1798),這個集子是與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作的。詩名顯然將吟詩的時間和地點交代得相當完整:“1798年7月13日的一次旅行,重訪懷河兩岸,在丁登寺上游數英里處吟得的詩行。”這一詩名在《抒情歌謠集》所有的版本——1800年、1802年及1804年——中都得以保留,也出現在各種版本的《華茲華斯詩選》(Collected Poems)中,且只有零星的版式變動,偶以“作得”(Composed)替換“吟得”(Written)。開篇如下:
五年過去了,五個夏天,加上
長長的五個冬天!我終于又能聆
這水聲,這從高山滾流而下的泉水,
帶著清淡的內陸河的潺潺。①
華茲華斯為該詩加了兩條腳注,第一條便是在“潺潺”一詞之后:“河流并無受到丁登寺上游數英里的潮汐的影響。”此注解連同長標題被保留在日后所有的版本中,且一直是腳注而非尾注。后來華茲華斯將“清淡”(sweet)改為“柔和”(soft)時,該注依然如故。
詩人此舉頗出乎意料,因為他用這條注至少部分地解說了“清淡”這一相對平常的選詞,“清水”(sweet water)通常就是“淡水”(fresh water)的同義詞。華茲華斯由此為自己作了辯護:此文并非僅僅充滿詩情畫意,“內陸”(inland)——該詞并不常見,因而或會遭到詬病——也可以得到解釋。注解在保證華茲華斯文字準確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討論語境。在這里,“清淡”和“內陸”、陳詞與異字之間的不協調,既彰顯了用詞的精準,同時又令人矚目。換言之,華茲華斯通過風格各異的遣詞,創造了特點鮮明、幽微隱蓄且活力流溢的緊張度,而該注解為這種張力提供了合理說明。即使在經過修訂、解釋的必要性降低之后,華茲華斯仍保留了此注。在其詩人生涯之中,他始終心系寫詩的位置與潮汐間的關系。
盡管關于《丁登寺旁》的創作地點已有充分討論,但這條注釋的關注度并不高,多半因為通常的理解只停留于對該詩“田園化傾向”的肯定。一條不受潮汐影響的河意味著河水流經之處均為一派田園景觀:“看到了田園的綠色,一直綠到家門。”②風景旅游作家威廉·吉爾平(William Gilpin)肯定會對此表示認同,他在丁登寺下游的懷河段發現了“很煞風景之處”:
此前一直河水清清,風光旖旎,河岸上的幾處風物也倒映在水里。可到了此處卻有河沙摻雜,顏色也渾濁起來,兩岸也都變得十分泥濘。種種跡象表明這里受到了潮汐的影響。③
對于已然習慣了優美格調的讀者,華茲華斯的注解似要消除其疑慮:《丁登寺旁》贊頌的便是一片潔凈無瑕的怡人景致。
新歷史主義批評者在品讀《丁登寺旁》時,一再著眼于其退隱“翠綠的田園風景”。丁登寺附近“興辦了大型煉鐵廠,將噪聲和喧鬧引入了這片寧靜地帶”,①而華茲華斯便要逆流而上,去尋找自己真正要的——一塊遠離歷史的庇護地。②華茲華斯故地重游之時,丁登寺一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工業和污染的影響,這一點是存疑的。③然而人們雖則意見不一,對該詩的田園屬性卻并無質疑;討論的核心在于田園的價值,或者說田園是否貨真價實。華茲華斯關于潮汐的注解雖然表面上強化了對田園的強調,但打破了上述那種對田園性的一致認同,因為注解揭示的其實正是該詩的農事屬性。
吉爾平直到河水流過了丁登寺才留意到潮汐的影響。《從懷河源頭走起》(An Excursion from the Source of the Wye,1810)的作者馬克·威利特(Mark Willett)觀察得更為確切。他記述道:懷河流經丁登寺上游三英里處的“蘭多加”[Llandoga,今蘭多格(Llandogo)]時便成了“潮河”。④因而丁登寺以上“數英里”也成為淡水與咸水的分界點。只有遠離海潮最高點之處,河水才能保持穩定的下流方向。而至潮起處,這一穩定性便出現了震蕩。一路往下的河水被暫時沖散,直至潮汐流動并退卻時才重整旗鼓。潮汐既借助了地外之力(由宇宙天體運動產生的持續的——穩定而恒久的能量),同時也很接地氣:滾滾而來的潮水一路溯河而上,其行程也受到天氣和降雨量等偶發狀況的影響。如逢干旱時節,河流水位走低,潮汐便會上溯得更遠,反之亦然。故而華茲華斯那句模棱兩可的“以上數英里”與實際情形完全相稱,如此描述堪稱精準。閾限點總是如期而至,然而確切定位實難預料。
華茲華斯完全可以更深入內陸來創作這首詩,比方說在古德里奇堡(Goodrich Castle),或如大衛·邁阿爾(David Miall)謹慎指出的上至西蒙茲雅特(Symonds Yat),⑤這兩處均是一片田園風光,河水也完全未受潮汐擾動,但他選擇了一個潮汐河段與非潮汐河段的交匯地。達米安·沃爾福德·戴維斯(Damian Walford Davis)是極少數幾個關注華茲華斯注解之潮汐內容的批評家之一,他認為《丁登寺旁》自始至終都涌動著潮水,稱該詩“本身便是一張水文圖”:
一張文字繪就的地形圖,其中包括了海濱、河流、潮匯、河口和海事信息,而詩就在這張地形圖上流動。⑥
這段話也可以用來描述新近的詩歌,例如愛麗絲·奧斯瓦德的《達特河》(Dart,2002)和《夢游塞汶河》(A Sleepwalk on the Severn,2009),或是亦談及塞汶河河口的菲利普·格羅斯(Philip Gross)的《地下水位》(The Water Table,2009),但《丁登寺旁》所蘊含的潮汐元素比一張水文圖要更加含蓄、更富政治色彩。該詩并沒有要費心繪制潮汐曲線圖的意思,而是著力于表現面對這潮去潮來的節奏,人們應如何棲居、如何響應、如何思索。
戴維斯的興趣點使他也很關注其他批評家對該問題的認識。他引用了斯圖爾特·柯倫(Stuart Curran)的話:“詩里展現的每一流向都不無逆流”;①以及帕梅拉·伍夫(Pamela Woof)所發現的:“行云流水般的涌動,那種流動與逆流正是詩意的運轉”。②例如詩的開篇便能覓得這一運轉,題名中的日期合乎詩人一如既往的精準記憶(“五年……五個夏天……長長的五個冬天”)。與此類似,“懷河兩岸”成了“這水聲”。在標題和詩文中,地形參照點與指示系統都能一一對應,如同網格坐標與谷歌街景,而其意義基本一致。題名中的客觀記錄與開篇詩行里的個性言表之間的差異,進一步構成了記錄的不一致與陳述的意義一致之間的差異。亞當·波特凱(Adam Potkay)和羅伯特·哈斯(Robert Haas)都引人注目地將研究重心放在了詩的開篇的聽覺認知上,這與18世紀如畫美學的視覺強調形成了對照。③哈斯注意到詩中之傾聽與詩之傾聽,二者相輔相成,于是“我聆”(I hear)與“我臨”(I here)之雙關音效便不絕于耳。進而還可以解釋說,這一短語的雙重意義和音響表明了認知與存在如何能同時發生,二者既有區分又難舍難分,在讀者的腦海里交替閃現,而且這種交替的呈現在二者之中都能夠找到:在聚精會神聆聽之時或會忘卻自我意識,而自我也許更能意識到作為認知主題的自身;同樣,“臨”可以是自我忘卻的過程,或也可以自我定義。“我臨”(I here)一語少了“我臨及此地”(I am here)或“我來了”(Here I am)等用語中的連接性字眼,反倒彰顯了不確定性,并使得對位的“我聆”得以存在。如此,柯倫和伍夫所留意到的流動與逆流能夠在詩的風格中覓得,讀者在其字里行間也能感受到一種躊躇的搖擺,徘徊在可替代的意義與視角之間——而此躊躇居然就生發于(也相對照于)詩文酣暢的前行動能之中。這一躊躇可以安居于詩句向前奔流的進程中,甚或逆向而動——也許就“生發于”或“相對照于”前進中,這種不確定性創造了更深遠的、元層次意義上的躊躇。因此,詩便產生了循環往復的效果,既指其生成性,又指其不斷的回歸性。
從更宏闊的視角來看,類似的情形依然顯在。總體而言,該詩依循著潮起潮落的節奏,以歸來為起點,以在展望中離去為終結。起初,華茲華斯來到一處可供緬懷、重溫美好的青春歲月的所在。從駐足之地開始他便受到吸引,溯河而上,描繪實為河源的“從高山滾流而下的泉水”,并留意到了懸崖峭壁:“這里已經是幽靜的野地/它們卻使人感到更加清幽。”在這個閾限點上,他被吸引去往山上、回歸源頭,但實則佇立不動,并放眼前方、下游及至未來。詩的弧形運動軌跡因此具有了潮汐性質——河水漲起涌向丁登寺,很快重又退去——這一形態在詩的終結時仍連綿不絕。華茲華斯在預知要離去時卻又想象著復返:
“那時候你更不會忘記,”他道,說話的對象是妹妹多蘿西,“我倆曾在這條可愛的河岸/并肩站著。”①
這種欲走還留的意趣在詩的末段又得到了重申,其在開篇的回聲延續著詩的周期性、潮汐性的模式。 于是,“在丁登寺上游數英里”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伊甸園的門已然關閉,華茲華斯與妹妹多蘿西手牽著手,必須立刻走進塵世,面對“日常人生里的全部陰郁的交際”。②舉目回望,舉目內陸,他看見了“綠色的田園景色”。他可以肯定的是,在很久以后的將來,即便眼前的實地遠去,他也依然記得:
我站在這里,不僅感到
當前的愉快,而且愉快地想到
眼前這一刻包含了生命和糧食
留給將來的歲月。③
如同開篇那樣,華茲華斯的詩風表現出他的回歸主題(restoration)的復雜性質。從“當前的愉快”中涌出更多愉快的想法:此刻的歡悅激發出萬千思緒,既有憧憬又不無懷舊。于是,當“愉快”轉換為愉快的想法時,歡樂本身便顯現為一種鼓動性、生發性的力量。他發現,除了“感到/當前的愉快”之外,還能“愉快地想到”。與其說前瞻與后顧之間存在著一種平衡,不如認為二者是相互交融的,其間能量滿滿。詩句延續的跨行書寫一開始就表達了“愉快地想”,在片刻之后、下行的整句完成之前,先出現了“生命和糧食”。從“生命和糧食”跨到“留給將來的歲月”,這一步啟動了向前的運行,同時也包含了一種恒久的感受(這一刻將延續下去)以及于將來再回首的意識。華茲華斯有朝一日回看往昔,便能明白這一刻已成為加持力的來源,他在當前預見了自己在未來的懷舊。
佇立于潮汐的閾限點,詩人原本波瀾不驚的心緒及其勻稱穩固的白體詩風也脈動著起伏漲落。華茲華斯在詩中寫道:懷河的景致曾給了他“甜蜜的感覺,讓我從血液里、沿心臟里感到”。④血液當然是脈動著的。生物機體中持續不斷地發生著往復運動,并由此保持了機體的平衡。同樣的視角也統領了華茲華斯對過去與未來的潮汐般的感受,并觸發他寫下了“沿心臟里”(along the heart)這樣奇異的詞組,因為“沿”(along)暗示了心臟內核處的運行(血液運行)。“從心臟里”(in the heart)和“沿血液里”(along the blood)是更加常見的表達,介詞的互換營造出運動中的穩定感以及穩定中的運動感,而似曾相識的感覺便是詩人在歡欣雀躍之時產生的思想的前瞻與回溯。滾滾而下的時間之河從不變的田園流入歷史的變幻之中。詩歌在追思與展望中輪番鋪陳,表現出既復雜卻又可辨的循環性,這與詩在總體上的循環構思共同彰顯著潮汐的特征。潮汐可表達為“動力”(motion)和“精神”(spirit),按華茲華斯的說法,二者“推動”(impels)精神“穿過一切東西而運行”。
妙不可言的是,華茲華斯的踏足而行也模仿了河水和詩句的潮汐節奏。他和妹妹多蘿西在布里斯托爾的歐斯特坐輪渡,并在靠近切普斯托的懷河東岸下船,自此徒步北上至丁登寺,在那里住了一宿。次日早晨,他們繼續溯流而行,穿過西蒙茲雅特,最遠達古德里奇堡,第三天方返程,沿河下行,穿過丁登寺,直抵切普斯托。
接著,正如約翰·麥克納爾蒂(John McNulty)所指出的:“在從古德里奇堡到切普斯托的長途跋涉——約22英里——之后,華茲華斯兄妹又乘舟上行,返回到丁登寺,并在那里過夜。”①數日之內他們雙向兩顧丁登寺——沿河而上、沿河而下——并坐船逆流而上,第三次抵達了寺院。丁登寺既是中點,又兩度成為終點,具有反復閾限性。華茲華斯的詩無論在結構還是文體上,便是在這樣的來回、往復的徒步旅行之中展現出阿卡迪亞式的牧歌風情,這也是他人生之旅的寫照。
而且同樣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們與侵入內陸、泥沙俱下的潮汐一同逆流重返時,此處的阿卡迪亞牧歌風情并不遜于河水清淡的上游,流經之地依然是田園農舍。放眼內陸和上游,他們有了重溫童年記憶的機會;待回到下游、置身充斥著工作和壓力的成人生活世界時,這些記憶又能給予他們精神的慰藉與心情的平復。兩股水流的混合被賦予了此種深意。然而水流在此交融的起因只是兩種對立而又互補的自然力:受地球引力作用而流向大海的水流,以及受月球引力吸引而上溯內陸的海潮。盡管天真陷進了經驗,生命沉淪入死亡,但狹路相逢的卻是相通之力,邂逅的是勃勃生機。
換言之,吉爾平所說的潮汐之煞風景,并不會得到華茲華斯的認同。他立足當時自己的人生階段,在潮汐的自然力以及這種力量所創造的機遇中發現了價值。威利特的旅行指南尤其鐘情布勞克威爾(Brockweir)村(他改其名為“Brook-weir”②)。村子在蘭多加和丁登寺之間,正處于已是強弩之末的潮水的下方。威利特談道:
此地住戶幾乎清一色地經營著貨船,他們從這里把船開到布里斯托爾。懷河沿岸的產品由駁船搬上這類帆船,后者大多可以承載40至70噸重物。③
威利特贊同吉爾平的觀點,即懷河一旦成為“潮河”,便“沒有了優勢,除非在高水位期”。④盡管如此,他還是注意到了其中的商業利益。隱藏于密林中的布勞克威爾其實是轉運碼頭,這里的居民與西南部的大港口多有交集。克利夫(C. F. Cliffe)在《南威爾士志》(The Book of South Wales,1847)中有著同樣的觀察:
布勞克威爾是個小港口,從布里斯托爾開來的大船把貨卸到懷河的駁船上,此處的熱鬧景象、木料廠及正在建造的船只(有的載貨量高達五六百噸)似乎很有些違和感。幸而懷河緊接著來了個馬蹄形大回轉,沖刷著丁登鎮(Tintern Parva)的村舍下沿——“天賜的丁登寺”不負期望,在綠葉翠林前端巍然挺立出來。①
“熱鬧”似乎是“違和”的(正如吉爾平眼中的丁登煉鐵業),克利夫期望的圖景是一種亂入,不過在他看來河道幸而回轉,緊接著那座寺院便映入了眼簾。即便如此,他仍為這個小港口里的造船規模感到有些自豪。懷河岸邊蔥郁的林木掩映著一處生機勃勃的產業中心。
布勞克威爾的船碼頭留存至今,不過已難覓船廠及造船業的蹤影。現在村子是作為田園度假地來推廣的。②但在華茲華斯寫詩之時,本地的工業不僅存在,而且相當活躍。這個深藏在懷河河谷里的偏僻村落,創造了一個兩種交通模式的交互界面,站在了兩種境域的交匯點上,即田園的內陸與農事的市場。這里對于逆水行舟而言是終點,但從資源集散、輸往下游外界的意義上說又是起點,相應的景觀特色得到了華茲華斯詩名及其有關潮汐的注解的暗示,但也僅此而已。該詩完全沒有提及布勞克威爾,而且清晰可辨的是,正如丁登的煉鐵業藏于深山一樣,詩句徹底地(也應為此受到指摘)遮蔽了所有的業態。不過,村莊里商品的雙向交換卻也能在詩中找到合拍的節奏:時間意義上的前進和后退,詩人風格上各種蓄勢待發的張力,以及敘述上的弧形軌跡。這種雙向交換還與他(通過詩文創作)對相反運動的互補機制的探索步調一致。此外,這種互補性還代表了商品交換所產生的互惠性。進一步說,自然運動及由此帶來的欣欣向榮的商品經濟都因河而生。
在華茲華斯的時代,在潮汐內溯范圍中,航船無需槳手或岸邊馬拉的協助便可行進。潮汐是主要的動力源,有助于實現大宗貨品的運輸。為此,從18世紀以降,多條河流得到了“改造”,其中就有懷河,它可航行的河段遠至赫里福德(其上游部分在枯水期仍難以行船)。改造工程大體上需完成兩項任務,即清淤和移除水流障礙物,后者尤其指當地人利用水力所建的眾多圍堰和水閘。其結果便是造成了適航性與當地差異化利益間的矛盾,以及本地利益與國家利益間的矛盾。③根據改造方的觀點,疏浚河道中的人為障礙能夠保證河流順“其自然水道”向下游運行,水流很平滑、更穩定。①他們倡議在去往上游的反向河道中進行同樣的施工,因為改造工程也能釋放上溯內陸的潮汐能量。
約瑟夫·羅布森(Joseph Robson,1763)在《英倫戰神》(The British Mars)其中一章“江、河、港口;及對海潮的合理使用”中宣稱:
將河港等設施打造得更安全、便利,方便船只往來。充分利用海潮,使其深入陸上并提升內河航運。清理河流入海口淤障,助力海流上溯。這些技術在歐洲很多地方都頗有價值,尤其在英國。②
河口淤障越少,內涌的海潮就越強勁,對內河航運的推動力就越大。文明發展水平的提升,使人們能夠從海里汲取更大的能量,并且如羅布森所言,這一資源如今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而且,仿佛有如神助的妙處在于,退潮的力道也增強了。潮勢洶涌之時,下行的內河水被暫時遏制,而待其勢衰,便與退潮形成合力,為行船掃清了航道,“流水全力沖刷著海峽底部或是河床地帶”。③
關于潮汐能的最佳利用,存在著廣泛的爭論,④因為從商業角度來看這種能量很重要,于是將水流量調節至最大化的手段便成為“頗有價值”的“技術”。詹姆斯·湯姆森在其《自由》(Liberty)中稱頌了大不列顛的諸多河流,對海潮在促進貿易上的貢獻也不吝贊美:
哦,泰晤士!
每一道潮水,喜迎返航的風帆,
在人類的多重收獲中流淌⑤
無獨有偶,在其短詩《關于西敏寺將建木橋的一則報道》(“On a Report that a Wooden Bridge was to be Built at Westminster”)中,湯姆森讓河流訴說道:
難道不是我經年累月地為你們沖積出肥沃的平原?不是我
養活了成群的牛羊,更多的村莊,貢獻了
比金羊毛更豐足的東西?難道不是我,你們這些生意人哪,
乘著每一波澎湃的浪潮,送進來非洲的財寶,
和印度的驕傲?
不是我給了你們各國辛勞的成果?
讓全年氣候適宜,使四方土地肥沃?①
涌入河流的潮汐輸送著帝國的物資,殖民擴張就此得到了歸化。湯姆森把潮汐視作河流的屬性,從而賦予河流雙重價值:既給土地增添了“更多”,又輸入了舶來品。農民和商人均從中受益,鄉村黨與輝格黨也都因此更加有錢。大家露水均沾,潮汐平衡了各方利益。
湯姆森在對商業帝國進行鼓吹的過程中將潮汐用作貿易及其一切利益的象征。于是,在“大不列顛國度”,潮汐干預或導流的影響令人生畏:
這充沛的貿易大潮,
千千萬萬勞力卷入
其洪流,直至望無邊際的潮汐
席卷成滔天巨浪滿溢于大地;
而清亮的河水,毫無曲折,卻也
調轉了流向。②
“充沛的”(Redundant)意即“大量的”(abundant)或“充滿的”(overflowing)。高漲的貿易潮將遍布大地。“曲折”(Inflected)意即“彎折”(bent)或“改向”(deflected),因而哪怕最微小的轉向都是毀滅性的。對商貿事業的忠誠至為重要。
在湯姆森的時代,“曲折”是個光學用語,相當于現在的“衍射”(diffracted)。湯姆森在《秋》(“Autumn”)中把月光形容為洪水:
皎白的洪流漂游廣闊,輕淡淡涌動于
蒼穹下的山巒間,直至疊影重重的溪谷,
巖石和洪水映射著粼粼微波,
整個空氣因了無邊的銀光之潮而泛白,
在天地間顫然翕動。③
在“大不列顛國度”里,“皎白的洪流”喚起了通感,仿佛貿易亦如月光,一種全球性、自天而降并踏潮而來的啟明。18世紀的科學發現了潮汐與月球的關聯,④此關聯揭示了一種更為宏闊的秩序。當人們認識到潮汐與月光相伴相生并可以構成一個和諧世界時,便能因勢利導,化洪水和海潮為人類之裨益。
湯姆森將潮汐能視作神佑之物,從而為不列顛海洋帝國的擴張作了辯護。邁克爾·杰諾韋塞(Michael Genovese)便指出過這種樂觀版農事詩學的危險:
事實上,農事詩學對18世紀的農村劇變揭露得不痛不癢,因為這種轉型袒護了地主而不是擁有自由產權的農民及佃戶。圈地運動、公地體系的消匿、高漲的租金以及不顧佃農反對而恣意兼并農莊的行徑,這些都驟然加劇了經濟不平等。①
類似的記述也出現在凱倫·奧布賴恩(Karen O’Brien)和羅伯特·歐文(Robert Irvine)的著作中。②庫爾特·海因策爾曼(Kurt Heinzelman)認為,農事詩學在18世紀后半葉的式微,要歸因于官方(甚至皇家)對其收編之需,與當政者的結盟摧毀了這一體裁的反抗力量。③
在對歷史進程進行農事性的描述之下,社會變遷被賦予了積極意義,斷崖式劇變也貌似人畜無害。艾倫·劉(Alan Liu)指出,18世紀的農事詩學是一種具有意識形態動機的偽裝:“農事自然之鏡的目的在于隱藏歷史。”他寫道:歷史被理解為“真正的疾病”(real ills)。而喬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擔憂的正是,他或會將這一疾患“隱藏/在詩之自負的俗麗飾片之中”。④凱維斯·古德曼(Kevis Goodman)認為,華茲華斯對這些危險是有所警惕的,這在其《遠游》(The Excursion)中體現得尤為突出。“請求歷史把艾迪生式的‘快樂原則’讓渡給現今,這究竟是有理可陳,還是有欠公道?”該詩“試圖在二者之間達成一種復雜的調解”。⑤古德曼在華茲華斯[以及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的詩句中辨別出對農事詩學的迂回運用,而種種跡象又表明,他一直存有抗拒及這樣一種意識:改良或許掩蓋了歷史,進步也會抹殺抗議。
對于農業改良以及關于重商主義的自我辯護、自我肯定的敘事,華茲華斯多次表達了不安,這在其除《遠游》之外的其他詩文里也時常顯現。《邁克爾》(1800)和《最后一只羊》(“The Last of the Flock”,1798)都質疑了農事詩學對于進步的普世性福利的信心。《丁登寺旁》中的潮汐元素對華茲華斯及其讀者而言顯然是一種對能源的另類描述。在18世紀的農事詩學中,物力論(dynamism)總體而言是服務于進步事業的。詩歌的目的論是于自然和個人力之間為一種進階敘事進行調和。華茲華斯的農事書寫是拒斥目的論的,他筆下的潮汐表達了一種可持續的生命力他既不茍同田園詩對完美的主張,也不應和史詩對進步道路的追逐,由此而生成的農事詩學卻能同時給予二者更多的活性。
在華茲華斯似最有可能與湯姆森之類的作者發生共鳴時,這一點尤為清晰地凸顯出來,因為此時他的書寫產生了迥然不同的效果,仿佛他或許是在通過比較來揭示自己獨有的立場。例如在《遠游》的第8卷中,華茲華斯對約翰·戴依爾的《羊毛》(The Fleece)評論道:
在其寫作生涯里,機器時代剛剛開始,而古道熱腸的戴依爾對機器的預言則極盡溢美之詞。
接著他表明了保留意見,但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護,唯恐流露出離經叛道的語氣:
真理促使我去琢磨對能源的不當使用或濫用所帶來的惡果,盡管能源本身是那么美好。①
然而,他在《遠游》中為自己辯護的一段卻表達了對進步之裨益的十足信心:“唯社會工業之命,/多么快速、多么巨大的增長!”華茲華斯寫道:盡管伴隨工業化而來的首先是城市蔓延(“萌發于/這里某個貧窮的村莊,飛速生長出/一座大城市,綿延而密集,/遮蓋了數十里土地的面容”),其次還有空氣污染(“持續燃燒的煙火/經久不散”凌壓于“人們的居住地”),但即便煙塵如云,他也能接受:它們“繁多如一圈圈/的水汽,在朝陽中閃現”。②
在這里,從華茲華斯詩中呼之欲出的似乎是一幅美輪美奐的圖景,這與吉爾平在南威爾士路遇尼絲(Neath)時的記述可謂異曲同工:
目光越過河流,鄉野兀現于山巒之中;遠處有一兩座鍛鐵爐或燒炭坊令人欣喜地點綴其間,我們在懷河兩岸均可領略其風采;爐頂裊裊升起一圈圈煙霧,悠然融入天際。③
吉爾平全神貫注于這如畫一般雅致的風景,卻暗含了對勞作于鍛坊中的人們的鄙薄,而這些苦工正是因在廠房里罹患了各種呼吸系統疾病而變得日益衰弱。華茲華斯則表現得更富關愛和責任心,他既認同煙霧所營造出的奇景,又注意到了持續燃燒并產生煙氣的火。詩歌從對污染的留意過渡到對風景的刻畫,似重蹈了重后者而輕前者的一貫輕巧的做法,但 “持續”和“經久”又使詩人無法罔顧揪心的現實。類似的情況是,在朝陽中閃現的水汽似應為一種短暫的意象,而華茲華斯則將它形容為“繁多”(plentiful),而非“容易消散”(evanescent)或“稍縱即逝”(fleeting)。煙氣既是閃亮的,又是沉重的。此外,“繁多”也暗示了豐饒和繁榮。
換言之,詩的書寫在吸能與賦能的過程中充滿了張力。正是潮汐之本色,引得讀者在對工業發展的褒貶之間徘徊不定,這并不是為了站定立場,恰恰是為了在不安分的矛盾中保持生機。盡管如此,華茲華斯的字里行間仍隱現著樂觀主義。雖然前行帶來了憂患,但工業繁榮無可否認,進步依然閃現著亮點。不過華茲華斯詩作并不被動接受發展進程中的種種悖論,也并非隨波逐流。全然對立的語句并置,以及用詞之推敲中生發的錯綜復雜的緊張度,都促發了讀者內心的辯論,即一種潮汐式的俯仰:此刻接受了一種主張, 在下一刻又對其真實性產生疑問。
這些詩句因此促生出了潮汐式閱讀,既接受商業活動帶來的各種好處,又積極參與對其所引發的種種問題的揭露。《遠游》同時還十分推重商業創造生機的力量,而不是帶給英國什么國家層面的財政利益或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優勢。該詩的潮汐式涌動敦促著讀者思想的更新和創新。《丁登寺旁》自開篇伊始,便對張力的使用收放自如。從此意義上來說,《遠游》承續了前詩的主旨。在所有這些例證中,華茲華斯的詩風給人的印象便是彼此競爭的力量被掌控在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里。①不僅如此,于風格的選擇上,華茲華斯總是在考量自己在世上的存在:能有多么遠大、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換言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田園狀態,而在農事活動上又能走多遠。
維吉爾所感知的自然對于人類活動是有敵意的,他以河流為喻來闡明自己的觀念,而這也體現在華茲華斯的思想中,其《丁登寺旁》便是如此。1798年前后,他在筆記本上寫到人們該如何看待似乎無可避免的外在壓力:
有些人如同蟲豸,面對滔滔水流或莽然跟進,或負隅頑抗;另一些人雖非妄自菲薄亦不甘平庸,卻也淡然順流而下。②
“滔滔水流”勢不可逆,“或莽然跟進,或負隅頑抗”意味著徒勞無功或自我毀滅。不過,除了如此瘋狂之外,也可以選擇懈怠——一種對平庸的反抗的有意識規避。華茲華斯的詩尋求極端中間的道路,在下行水流與上涌海潮之間、在被動與主動之間、在循規與“沿心”(felt along the heart)之間維系動態平衡。《丁登寺旁》在整體上同樣如此——風格有了調校,懷河潮汐得到了關注——詩人周旋于意愿和選擇之間,探索著順流而行(時間的、歷史的及局勢意義上的)與逆潮而上,動能與沉浸,以及神意與人力之間的關系。
華茲華斯的潮汐書寫因此蘊含了對帝國權力的思考:昭昭天命之下尚有能動的空間么?勢不可擋的河流賦予人以榮耀,這些人還能夠博取多少國家或民族的優越感?同樣,坐享神佑的習慣思維,能抵擋住個人意志的覺悟么?潮汐也讓人關注治理(stewardship)的可能和性質。田園必須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么?在史詩的發展過程中,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朝向創建田園的農事勞作?如此說來,華茲華斯的農事書寫修復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理念——不為繁榮進步,也不為賺錢發家。
因此,《丁登寺旁》從其定位和語言上說與布魯斯·格拉弗的“農事田園詩”很相像,還外加了一種經濟維度。布勞克威爾的潮汐能量揭示了商業與自然間的和諧,而詹姆斯·湯姆森的心目中也有一個潮汐推動的商貿帝國,它在全球范圍內也能夠達成一種類似的和諧。然而,華茲華斯將被給予的與被追捧的結合了起來,讓田園式的昭昭天命與農事的權力意志聯手。潮汐與其說把英國的成功自然化,不如說更多地將農事象征化為一種存在模式——如何隨時代乃至跨時代為生計而工作,如何為商業和交換而勞動。此外,潮汐還象征了人類憂患意識的動態性質。
還是在1798年的筆記手稿中,華茲華斯在描述或抗拒或順應“滔滔水流”時,贊頌了一種“大惰”(holy indolence):“至智之順從,而心中/豁然而開。”①該筆記中還有一些未面世的詩句得到了大衛·邁阿爾(David S. Miall)的關注:
我身處生活之中而并不自知
旖旎的物事使我重新回歸
再度失卻自身仿佛我的生命
隨一種詭譎之神秘或衰落或高漲②
旖旎的風景使他“重新回歸”——回歸生活及對活著的意識,接著仿佛又倏然間“再度失卻自身”。這一轉換使他想到,他的生命亦包含衰落和高漲,激蕩于知覺與意識之間。這種感知的節奏故而是自然而然的,找回這一感知也要通過自然的、日常的經驗。心智在追隨自然界的模式——如潮汐之漲落——時才能達到最佳狀態。與此類似,在《遠游》中的“小販”(“The Pedlar”)一節中,主人公在各種自然形態中看到的也是一種潮汐式運動。他自少年時代便獲取了“專注形象的活躍力量/深印于腦際”(an active power to fasten images / Upon his brain)。③這一對真實事物的探求性關注,生發出了他的知察能力:“在它們確定而穩固的輪廓線中/……尋到一種漲衰輪替的思想。”④
類似的情形是,接著《遠游》那段既認可繁榮又不忽視污染的段落之后,華茲華斯又唱起了帝國的贊歌,這既呼應了18世紀的農事書寫,同時又改變了他所強調的重點。
因此可見不計其數的
舟楫棲息在她那些船頭攢動的港口里,
或停泊于其海峽和海灣中;
生機盎然的千帆壯景
船只深入她的內陸地帶,縱橫往來
懷著潮汐的吐納氣息,經久不止,
浩瀚繁盛!⑤
企業經營產出的不僅有奢華的商品和遍布全球的足跡,還有“生機盎然的千帆壯景”,這情形既令人振奮,或又成為自豪感的源泉,且事實上讓人文思勃發,促動并激勵著心靈感知。他的遣詞造句在消極與活躍、變動與自足之間起伏漲落。接下來的用語同樣如此:“經久不止,浩瀚繁盛!”這壯麗的場面不僅續存長遠,而且擁有著數不勝數的具體景觀。
壯觀的景象呈現出更為本真的盎然生機,是因為在其背后推動的是自然之力,即由開拓河道而得以利用和改良的潮汐流;也因為這一景象表明,自然界之中與身體之中的能量流轉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延續性。潮汐是星球的呼吸,它同時也形成了人類思想的范式。把握住這浩瀚繁盛的相互關聯的意義,則能煥發出盎然生機,可謂“有物令我驚起,它帶來了/崇高思想的歡樂”。這里的用語,在“歡樂”、“驚起”及“崇高思想”之間產生的錯綜復雜的交鋒,其本身既汲取了生機又能夠賦予生機。①再者,當我們辨識到心靈與世界間的相互關聯時,我們也回憶并回歸到了自身存在的源泉:
因此在天氣宜人的季節里
盡管我們遠居內陸
我們的靈魂仍能放眼不朽的大海
是它將我們送到了這里
而我們還可以倏忽間抵達海邊
去看孩子們沿岸奔跑②
不朽的大海,是我們的出發之處,也是命定的歸途。大海“將我們送到了這里”,也即“生命里”(in life)的地方:我們在此回望不朽,同時也前瞻不朽。同樣在丁登寺,潮汐把華茲華斯帶回到初始之地,且與此地融為一體。不朽之海生發的不僅是生命之潮,而且是潮水本身。誠然,我們在生命里時時處于死亡的進程中,但如華茲華斯所說,我們在生命里又是生生不息的。牢固而指引性的記憶——“最純潔的思想之錨”,③只能在潮汐的往返中追回。
維吉爾的詩歌之輪從田園轉向農事,又朝著史詩進發,這一演化與成熟的過程相互對應,也與河流自源頭奔往海洋的走向相映成趣。華茲華斯在《序曲》及1820年的十四行詩系列《達登河》(The River Duddon)中,都通過這條河的意象來運用以上延伸隱喻。④他在1809年的《答馬塞特》(“Reply to Mathetes”)中重申了這一比喻:
人類的進步既非也不可能像羅馬筑成的康莊大道。可將之更貼切地比作一條河,無論在其較為狹小的流域里還是在更寬闊的彎口,都常常受到難以回避或克服的障礙物的逼迫,而折返向其發源地;但伴隨著這些千難萬阻的,還有那一股沖勁,保證其終究仍能一往無前。①
我們或可將《丁登寺旁》所描繪的人生片段置于這樣的思想洪流中來觀照,視之為一段農事時刻,在一個農事興盛的地點被他捕捉并領悟。華茲華斯通過進一步的書寫又強化了自己的領悟,他敘述了勞作以及達到更高級的自我理解時的“輕松自在”,此時他使用的語言多方面復刻了潮汐的漲落。與此類似,《遠游》敘述了回逆的經歷——后退的步調實則為了前進。詩歌贊頌源源不斷積聚的投入,認可多種形式的工作,其間的創造力直接參與到生命的活性之中。這種贊美與華茲華斯那錯綜復雜而又充滿張力的詩句一樣,反抗著熵的衰朽,甚或正因為寫作之事就如商業勞作一樣,必投入到時間的循環往復中。
(原載于Sue Edney and Tess Somervell, Georgic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Land, Reworking Genre, Routledge, 2023, pp. 104-121.此次翻譯已獲作者授權。)
責任編輯:胡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