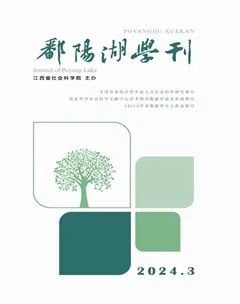物質(zhì)生態(tài)批評(píng)視域中《嘉莉妹妹》的車敘事
[摘 要]在物質(zhì)生態(tài)批評(píng)視域中,車如同其他很多物件一樣,早已擅自超越其交通工具屬性,成為一種強(qiáng)大的有故事的物,這在《嘉莉妹妹》中有著高度戲劇化的體現(xiàn)。該作的整個(gè)情節(jié)都搭乘著車,五光十色的車輛留下了主人公嘉莉與赫斯特伍德人生曲線的印記。車是諸多物質(zhì)元素的一種,也是最有存在感的一種,一直伴隨著男主人公的起落,其境遇可謂一場(chǎng)翻車事故,而車作為一種本身就具有高度機(jī)動(dòng)性、施事性的器物似乎在加快情節(jié)的發(fā)展。車以其自身特有的活動(dòng)特征,完成了從功用性到建構(gòu)性的轉(zhuǎn)變。以車為代表的物敘事,或?qū)⒃跓o形的世界里繼續(xù)延伸。人們需時(shí)時(shí)自省,方能在當(dāng)下人工智能日益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里學(xué)會(huì)駕馭好自己。
[關(guān)鍵詞]物質(zhì)生態(tài)批評(píng);《嘉莉妹妹》;車敘事
“我應(yīng)該回到城市去,無論那里潛藏著什么危險(xiǎn)。假如可以,我就悄無聲息地去;倘若必須,我就光明正大地走。”①——無論面對(duì)何種困苦,無論怎樣遇人不淑,《嘉莉妹妹》的同名女主人公,這個(gè)藝術(shù)的精靈同時(shí)又作為物質(zhì)的追逐者,在書頁間輕盈起舞。然而這樣的悖論并無違和感,因?yàn)樯畹默F(xiàn)實(shí)原本就是矛盾的,不要去想像不食人間煙火的唯美。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力便是在矛盾沖突的張力中釋放出來的。嘉莉妹妹這個(gè)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同時(shí)又飽嘗生活之艱辛的美麗姑娘,脫逸于百年前德萊塞的案臺(tái),至今仍舞動(dòng)在人們的心頭。雖然時(shí)過境遷,但后人對(duì)她的解讀、翻譯、詮釋并不鮮見。作為小說的新譯者,筆者亦傾心于她的靚麗、才華與果敢。她先隨命運(yùn)顛沛而后弄潮于時(shí)代,牢牢把握著自己的前途。即便面對(duì)21世紀(jì)的中國(guó)讀者群,尤其是已然或?qū)⒁允г谖镉麢M流的都市里的男男女女們,她也同樣能夠打動(dòng)人心。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外學(xué)者多從德萊塞的自然主義小說技法入手來探討作品及其塑造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學(xué)研究的物轉(zhuǎn)向浪潮中,學(xué)者批評(píng)的目光逐漸從前景的人擴(kuò)展至背景的物,而循著這樣的視線審視自然主義小說,物的活性仿佛在批評(píng)的視野中重新得到了釋放。例如有學(xué)者指出,“無論是芝加哥建筑外墻的透明玻璃,還是商店櫥窗里巧妙展示的時(shí)尚服裝,都在介入嘉莉妹妹的渴望和訴求時(shí)獲得了重要的生命維度,也成為反觀嘉莉妹妹從落后鄉(xiāng)村進(jìn)入豪華大都市后身份如何重新受虛幻的商品世界建構(gòu)的一個(gè)重要入口”。①
筆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的確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這種物的涌動(dòng)。本文嘗試探討令人印象至深的“車”作為一個(gè)新的物敘事視角在《嘉莉妹妹》中的體現(xiàn)。筆者認(rèn)為,作為交通工具的車,已擅自超越了被人類規(guī)限的功能,成為一種強(qiáng)大的有故事的物(storied matter)。車的出現(xiàn)頻率看似超出了必要,但正是這一“指涉過量”強(qiáng)化了作為一種物的車的能動(dòng)性甚或主宰——你不得不去正視其意義。雖然在一百多年前,各類車輛的性能無法與今日的出行工具相提并論,但其實(shí)從那個(gè)時(shí)候起——或許更早——當(dāng)人們以為自己在驅(qū)車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受到了車的驅(qū)使。從這個(gè)視角去讀《嘉莉妹妹》,便有了別樣的感受。可以說,這部作品的整個(gè)情節(jié)都搭乘著車,五光十色的車輛留下了女主人公嘉莉與赫斯特伍德人生曲線的印記:第一次四目相對(duì)時(shí)他們以為相愛了,殊不知目光在交匯的那一刻,他們的道路便各自發(fā)生了人們所能夠想象到的最大限度的反轉(zhuǎn)。雖然嘉莉妹妹光芒四射,可是赫斯特伍德這個(gè)最大的(雖然不是唯一的)男性陪襯,其悲劇性的震撼力也非同小可。一個(gè)已經(jīng)在人生布局中的確定贏家,一個(gè)拿了一手好牌的上層社會(huì)中堅(jiān)分子,卻也會(huì)在一念之間滿盤皆輸;一個(gè)深思熟慮滴水不漏地經(jīng)營(yíng)著自己生活的人,一旦在沖動(dòng)之下鋌而走險(xiǎn),突入到茫茫的未知領(lǐng)域,其防御體系也就立刻漏洞百出,而且竟然無法翻身。那種孔武男性的脆弱無助,令人百感交集。在此過程中,車作為諸多物質(zhì)元素的一種,也是最有存在感的一種,一直伴隨著他的起落,他的境遇可謂一場(chǎng)翻車事故。車以其自身特有的活動(dòng)特征,完成了伍德沃德(Ian Woodward)所說的從“功用性”到“建構(gòu)性”的轉(zhuǎn)型。②下文將研讀德萊塞是怎樣通過具體的車敘事來構(gòu)造他的自然主義情節(jié)的。
在文學(xué)的新物質(zhì)主義研究領(lǐng)域里,有學(xué)者將此學(xué)術(shù)潮流形象地比作“發(fā)動(dòng)機(jī)引擎”,因其“深刻影響了生態(tài)批評(píng)、后人類批評(píng)、情感批評(píng)等眾多理論場(chǎng)域的前沿趨勢(shì)”。③而在《嘉莉妹妹》中,這一比喻已從修辭演進(jìn)為車的實(shí)在動(dòng)能。嘉莉在去芝加哥開啟新征程的火車上邂逅了德魯埃——第一位關(guān)鍵先生,而她兜兜轉(zhuǎn)轉(zhuǎn)離開芝加哥去紐約開啟第二段人生時(shí)也是坐著火車,只是此時(shí)陪伴在左右的已是另一個(gè)風(fēng)流人物——赫斯特伍德。可以說,她的每一次轉(zhuǎn)身都伴隨著滾滾的車輪聲。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物》一文中說:“只有通過物,人才能了解自己。”④物不僅可以是故事的載體,甚至能夠參與故事的生成。物的研究實(shí)際上具有兩面性,而且這兩個(gè)面在物轉(zhuǎn)向研究中正在實(shí)現(xiàn)過渡,即從對(duì)來源于資本擴(kuò)張的物質(zhì)主義的批判,到作為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批判的物的主體性凸顯。事實(shí)上,“物轉(zhuǎn)向”的批評(píng)話語也影響了筆者的翻譯策略。例如原譯文“嘉莉?qū)λ械钠列乱律讯甲巫我郧蟆保愿臑椤凹卫蛟谟墓鼟叮╰he drag of desire)下對(duì)所有的漂亮新衣裳都孜孜以求”,就是為了凸顯人與物之主/被動(dòng)關(guān)系的悄然反轉(zhuǎn)。在這樣的物敘事中,物不是用來凝視的,也無法凝視,因?yàn)槲锱c人之間的距離已經(jīng)縮短到無法測(cè)量。物是與人交匯在一起的,同時(shí)淪為待價(jià)而沽的商品,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已經(jīng)同化。當(dāng)然,對(duì)物的研究的兩個(gè)面并不能簡(jiǎn)單地理解為物取代人而奪得主角地位,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構(gòu)建,況且對(duì)物質(zhì)主義的批判和對(duì)物質(zhì)關(guān)注的提升,最終仍落實(shí)到人究竟應(yīng)該怎樣棲居于這個(gè)他自以為靜止且被動(dòng)、實(shí)則活潑且主動(dòng)的物質(zhì)世界里。《嘉莉妹妹》中特別突出典型的“物”有不少,如餐廳、衣帽、酒食等,不一而足,但在翻譯中車對(duì)譯者的沖擊幾乎無可避讓,因?yàn)榈氯R塞在車敘事上的用詞極為豐富。
故事里的車可以分為三大類,除了火車之外,都市生活中最常見的其實(shí)是馬車和有軌電車,尤其是前者,不同的說法多達(dá)十余種,如軌道馬車(horse-car)、輕便馬車(trap;buggy)、轎式四輪馬車(coach)、四輪馬車(barouche)、四座大馬車(carriage)、運(yùn)貨馬車(truck)、馬拉拖掛車廂(van)、馬拉巡邏警車(patrol wagon)、馬拉救護(hù)車(ambulance)和出租馬車(cab)等。詞匯的豐富,說明此物的發(fā)達(dá)。雖然在翻譯中并不總是需要費(fèi)口舌說得非常明確,但在特定的情節(jié)中,馬車的檔次與人物的境遇直接相關(guān):
他養(yǎng)了一匹馬,配了整潔的輕便馬車。他有妻子和兩個(gè)孩子,安居于北區(qū)林肯公園附近一座優(yōu)雅的住宅,總體看便是我們偉大美國(guó)上流社會(huì)里很體面的一分子——僅次于奢華階層的第一梯隊(duì)。①
赫斯特伍德的社會(huì)階層定位于“僅次于奢華階層”,生活富足,但要躋身于頂流尚需時(shí)日。他的私家坐騎也相應(yīng)地達(dá)到了“小排量”的trap級(jí)別(同樣是輕便馬車,還有四輪的buggy),與其中產(chǎn)階級(jí)身份對(duì)接。與此形成對(duì)照,當(dāng)嘉莉在舞臺(tái)事業(yè)上如日中天時(shí),追求她的富人“信件來得既密又急。有身家的男人們除了自夸各種讓人喜聞樂見的優(yōu)點(diǎn)外,還迫不及待地提到自家養(yǎng)了馬兒備了四座大車(carriages)”。此時(shí)回過頭來看車的級(jí)別差異,我們隱約感到作者一開始就通過車暗示了赫斯特伍德在愛情道路上的力不從心。
伍德沃德將“物”的功能歸納為三種:用作價(jià)值標(biāo)記(markers of value)或社會(huì)標(biāo)記(social markers),融合及區(qū)分階級(jí)、 社群、部落、種族等;用作身份標(biāo)記(markers of identity),在反映個(gè)體身份的同時(shí)參與個(gè)體身份的建構(gòu);用作文化和政治的權(quán)力場(chǎng)(encapsulations of networks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ower)。②物在由特定的文化、政治權(quán)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建構(gòu)而成的同時(shí),也參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建構(gòu)。德萊塞在《嘉莉妹妹》中有意無意所賦予車的,正包含了以上所有的標(biāo)記功能,尤其是體現(xiàn)“社會(huì)差異、確立社會(huì)身份和管理社會(huì)地位”。③
馬車和電車,就這樣始終伴隨著三個(gè)主要人物在大都市里的衣食住行、工作娛樂和戀愛生死。嘉莉第一天來到芝加哥姐姐家時(shí),樓下街道上“軌道馬車的小鈴叮當(dāng)作響,又隨車遠(yuǎn)去,對(duì)于嘉莉來說既新奇又悅耳”。車鈴鐺帶給她的愉快,表明了她對(duì)都市生活的熱情和接受態(tài)度。幾天之后,當(dāng)她不算輕松但也并非特別困難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時(shí),“她登上電車,情緒高漲,心潮澎湃”。從童話般的車鈴聲及其樂觀的情緒里,還暫時(shí)聽不到前途的種種不測(cè)和艱辛。“登上電車”頗有城市生活出發(fā)點(diǎn)的象征意味,與小說的總體敘事基本同步,且相輔相成。
說到交通系統(tǒng),不妨看看1889年芝加哥的大手筆。作者于開篇就熱切地告訴人們:“大都市就在那里,正是這些每天運(yùn)行不息的火車越發(fā)緊密地將人們與都市捆綁起來。”①鐵路公司巨鱷們“為交通物流的目的攫取了大片土地。有軌電車線路在城市高速發(fā)展的預(yù)期下已遠(yuǎn)遠(yuǎn)延伸至空曠的郊外”。②這種超前的規(guī)劃的確令人慨嘆昔日美國(guó)的“基建狂魔”為日后的工業(yè)化進(jìn)程所打下的基礎(chǔ)(香港、天津、上海和大連分別在1904年、1906年、1908年和1909年修建了有軌電車)。在芝加哥這樣的都市里,有軌電車已經(jīng)普及到一般市民都能坐得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作為物質(zhì)的車也開始驅(qū)策人們更為生計(jì)奔忙,其中車費(fèi)雖然已相當(dāng)平民化,但對(duì)于中下層階級(jí)而言仍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當(dāng)嘉莉忙不迭地告訴姐姐找到了工作時(shí),明妮只是贊許地笑笑,問她以后要不要考慮電車費(fèi)用。在此不妨幫嘉莉算一筆帳:根據(jù)非官方的資料,19世紀(jì)末美國(guó)路面電車的平均票價(jià)為5美分,折合為今天的1.35美元。③以此計(jì)算,嘉莉每日車資10美分,每周花費(fèi)60美分,占一周收入(45美分)的13%。故有下文:“眼下一個(gè)星期60美分的車資還是很大一筆開銷。”姐姐因此建議她上班“最好步行去,至少那天早晨步行,試試看是否能每天如此”。④實(shí)際情況也確實(shí)如姐姐所預(yù)料的那樣,嘉莉還是選擇了步行上班。由此可見,當(dāng)時(shí)公共街車雖然已經(jīng)很廉價(jià),但對(duì)于困頓的嘉莉而言仍屬奢侈。盡管這樣,各種車輛仍充斥在她的生活里,關(guān)于車的念想也縈繞在心頭。而到了關(guān)鍵時(shí)刻,車也會(huì)“挺身而出”,為嘉莉的決策加上決定性的砝碼。當(dāng)失去工作、被姐夫奚落而走投無路時(shí),德魯埃從天而降(這個(gè)巧合算是個(gè)槽點(diǎn)),一番好吃好喝之后便是好言相勸。此時(shí),是回到閉塞沉悶的故鄉(xiāng),還是投靠德魯埃留在紙醉金迷的大城市,嘉莉面臨抉擇:
嘉莉的目光穿過窗戶落到忙碌的街上。就在那兒,令人向往的大都市,當(dāng)你擺脫了貧困,一切就那么美好。一輛優(yōu)雅的大馬車由一對(duì)四蹄騰躍的棗紅馬拉著駛了過去,車?yán)镆晃慌墒媸娣刈谲泬|上。⑤
豪華馬車的“適時(shí)”出現(xiàn),仿佛在推動(dòng)左右為難的嘉莉作出最終的選擇。車的“動(dòng)能”表現(xiàn)無遺:是馬車——而且是四輪大馬車——讓她看到了自己未來的鏡像。“四蹄騰躍的棗紅馬”又會(huì)載她到怎樣一個(gè)蓬勃向上的世界去?德萊塞的敘事是現(xiàn)實(shí)主義/自然主義的,但同時(shí)又是隱喻化的。“主義”的標(biāo)簽從來就不適用于大師。
當(dāng)她暫棲德魯埃檐下,車作為有靈性的物仍然不時(shí)閃現(xiàn)出來,為她的逐物之路作著標(biāo)記。兩人頻繁出入豪華場(chǎng)所,在劇院散場(chǎng)時(shí)需排隊(duì)等待馬車調(diào)度員叫號(hào),德魯埃笑著對(duì)嘉莉說:“緊跟著我,就會(huì)有車坐。”①心智有限的德魯埃未必意識(shí)到自己隨口說出的話有什么內(nèi)涵,但言者無心,讀/譯者可以有意,就不知嘉莉聽進(jìn)去了沒有,反正在赫斯特伍德出現(xiàn)以前,她的確打算緊跟這位旅行推銷員了。她開始過上了小資生活,閑暇無聊時(shí)與鄰居太太包租輕便馬車出游,而路過富人區(qū)時(shí),瞥見有錢人從四輪大車上下來走進(jìn)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又引發(fā)了她的不滿足。她并非完美的女神,她愛慕虛榮,向往都市的浮華:“有錢是多么美好”;②“關(guān)于貧窮的一切都可怕”。③德萊塞仿佛仗著這清純美好的女孩來抒發(fā)不太高尚的情操。可是不要去苛責(zé)嘉莉的直抒胸臆吧,德萊塞并不準(zhǔn)備歌頌一位圣女,他只不過想注目于生活中最平凡的人的最平凡的想法。作者真正賦予嘉莉的不平凡在于:當(dāng)幾乎所有的俗世女性都向往物質(zhì)的美好并希望擁有嘉莉的顏值與志向時(shí),其中很多人——至今也同樣如此——并不明白嘉莉真正的財(cái)富。她擁有的不是演藝的稟賦和俏麗的臉蛋兒,而是勇氣與獨(dú)立精神。在這一點(diǎn)上,她所經(jīng)歷的兩個(gè)最重要的男人——德魯埃和赫斯特伍德,都無法與她匹敵。
不會(huì)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赫斯特伍德這位大堂經(jīng)理對(duì)嘉莉的第一次邀約出游,也必須落腳在馬車上:“他在出租站挑了一匹溫順的馬,并很快駕車走遠(yuǎn)了,沒人看得見,也沒人聽得見他們。”④不但如此,他還教她駕車,似乎要引導(dǎo)她越走越遠(yuǎn)。男一號(hào)換了人,車還在繼續(xù)作為主動(dòng)媒質(zhì)為嘉莉開拓上升通道,雖然這個(gè)通道同時(shí)也曲折而幽深,甚或不無至暗階段。即便在兩人你儂我儂、一訴衷腸的公園里,不見車影,卻依然可聞車聲。類似的聲學(xué)化再現(xiàn)手段在小說中并不鮮見。作者通過聲音敘事繼續(xù)讓這一代表性的都市聲響介入人物的行動(dòng):“在涼爽、碧綠的灌木叢的樹蔭下,他懷著熱戀者的幻想張望著。他聽見有馬車在臨近街上笨重地移動(dòng)著,不過聲音很遠(yuǎn),僅在耳畔嗡嗡作響。四周都市的噪雜也只依稀可辨,偶爾傳來的鏗鏘鈴聲倒也悅耳。”⑤車因?yàn)闊o法進(jìn)入公園——這一象征青春愛情的城市飛地——而弱化,但顯然這只是暫時(shí)的,正如他們的柔情蜜意亦將無法持續(xù)——聽似“悅耳”的車輪聲掩藏了其真實(shí)的“噪雜”和“鏗鏘”,被欺騙的聽覺也暗示了兩人愛情的失真。此后在各種車行大道上,車可是將赫斯特伍德一路虐過去的,直至將他置于死地。筆者在翻譯中常會(huì)想到,德萊塞何以對(duì)嘉莉有多“好”,對(duì)這位大堂經(jīng)理就有多“壞”?或許,并不是他一定要把他寫死,而是不得已。在那個(gè)物質(zhì)當(dāng)家的世界里,人不是被捧紅,就是被棒殺,其中左右人們命運(yùn)的或許就是那些可敬可畏的帶輪子的家伙什兒。
前文提及,赫斯特伍德是有車一族,他和德魯埃都屬“互助會(huì)”這樣的實(shí)力中產(chǎn)團(tuán)體,互助會(huì)成員的標(biāo)配便是:“積一小筆財(cái)富,置一座漂亮的宅屋,配一部四輪或四座馬車,穿著高檔時(shí)裝,還要能在商界站穩(wěn)腳跟。”①從車的檔次看,赫斯特伍德那輛只能載兩人的座駕稍顯遜色,但比沒有車的德魯埃還是要強(qiáng)一些。馬車就是身份和地位的標(biāo)桿。德萊塞在后文借描述富家弟子追求嘉莉時(shí)總結(jié)道:“有身家的男人們除了自夸各種讓人喜聞樂見的優(yōu)點(diǎn)外,迫不及待地提到自家還養(yǎng)馬養(yǎng)車。”②時(shí)代再怎么變遷,虛榮的內(nèi)核并沒有太多不同,不同的只是外在幻象罷了。
比爾·布朗(Bill Brown)在《物論》一文中認(rèn)為,“物性”即指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及主體性。此時(shí)傳統(tǒng)的人為主體、物為客體的關(guān)系被顛覆甚或翻轉(zhuǎn)了:物并非僅僅只能被動(dòng)地充當(dāng)客體,也能施動(dòng)于人,具備建構(gòu)人類主體、 感動(dòng)主體、威脅主體、促進(jìn)或威脅其與其他主體的關(guān)系的能力。③在《嘉莉妹妹》中,車的移動(dòng)性變得更加名副其實(shí),甚至在隱喻層面已經(jīng)提前進(jìn)化到了自動(dòng)能走(automobile)的水平。這是赫斯特伍德所無法理解的,正如他無法理解自己日后的命運(yùn)一樣。他在私吞酒吧賬款后帶著嘉莉搭乘火車逃出芝加哥直奔蒙特利爾,接著仍輾轉(zhuǎn)坐車南下紐約。在這座魔幻都市中,德萊塞仿佛在赫斯特伍德與嘉莉之間架設(shè)了一副人氣指數(shù)蹺蹺板:嘉莉每高攀上一個(gè)層面,都以赫斯特伍德下滑一級(jí)臺(tái)階為前提條件。但這只是表面的吊詭,個(gè)中的此消彼長(zhǎng),很大程度上要?dú)w咎于赫斯特伍德的失誤:“既然在他的想象中她是安于現(xiàn)狀的,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致力于讓她安于現(xiàn)狀就行了。他提供了家具、飾品、食物和必要的衣裝。給予她休閑娛樂,帶她出去領(lǐng)略生活之光彩的想法便日漸淡漠。他感到外面的世界吸引著他,卻不曾想過她也愿意同往。”④他太低估了嘉莉的潛能:“待到風(fēng)起潮涌的變化之時(shí),她還是善于順勢(shì)而為的。”⑤他不能正視后者可以迸發(fā)的力量,其實(shí)原本也是可以拯救他自身的。
赫斯特伍德便如此在黑沉沉的迷霧中走向深淵。在此過程中每個(gè)關(guān)鍵跌點(diǎn),都有車碾過去的轍印。例如他所大敗虧輸?shù)馁€場(chǎng),就在輪渡(水上之車)附近;更重要的是,他甘當(dāng)工賊所選擇的行業(yè)正是電車司機(jī),這真是作者安排的一個(gè)絕妙諷刺:這個(gè)一生叱咤于各種車輪上的車友會(huì)會(huì)員,最終將職業(yè)生涯斷送在電車罷工中。這個(gè)“一日游”的情節(jié)雖然略顯生硬,但作為左翼作家的德萊塞借此一方面充分渲染資本主義上升時(shí)期的消費(fèi)文化,另一方面又借由對(duì)城市有軌電車行業(yè)罷工風(fēng)潮的詳述,對(duì)工人階級(jí)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時(shí)也暗示了物質(zhì)生產(chǎn)對(duì)于人的更深刻異化:讓工人更遠(yuǎn)地疏離了他所生產(chǎn)的物。
此時(shí),作為工業(yè)化時(shí)代代表性器物的電車,微妙地體現(xiàn)出對(duì)人的雙重控制:既是資本主義制度統(tǒng)治和奴役人的工具,又是人用物欲來奴役自己的代理者(agent)。無論如何,其外在的表現(xiàn)便是人所遭遇到的物的自反性。對(duì)此,伍德沃德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基礎(chǔ)上分析得很到位:
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物件或商品的面目并非如其通常示人的那般。這里的深意在于,人類錯(cuò)誤地相信,一種物件(如汽車、西裝、電腦或手機(jī))在社會(huì)進(jìn)步或個(gè)人提升上起到了積極作用,或者退一萬步說也是中性的。實(shí)際上人在調(diào)配這些物件時(shí),已經(jīng)在精神上奴役了自身;人們誤以為現(xiàn)代性所產(chǎn)生的物解放了他們,其實(shí)恰恰成為以這些物為具象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犧牲品。①
德萊塞便是如此將赫斯特伍德置身于車的大本營(yíng)里,并使他受了雙重的罪:讓這個(gè)錦衣玉食的有產(chǎn)者變?yōu)橐律酪h褸的工人(實(shí)為“工賊”),將他從豪華廳堂請(qǐng)到了寒風(fēng)刺骨的機(jī)車駕駛室。同情工人運(yùn)動(dòng)的小說家對(duì)昔日的大堂經(jīng)理毫不留情,而且“刻薄”地時(shí)時(shí)提醒讀者千萬別忘記赫斯特伍德的過去——赫斯特伍德鎮(zhèn)定地看著技師的演示:“他見過電車司機(jī)操作過。他很了解他們是怎么做的,也很確信自己只要稍加練習(xí)也能做得很好。”②這個(gè)看似平淡的記憶閃回,表面上是在為嘲弄赫斯特伍德接下來操作機(jī)車時(shí)的狼狽做準(zhǔn)備,但他與車的關(guān)系早已發(fā)生了反轉(zhuǎn):“見過電車司機(jī)操作”顯然發(fā)生在他昔年的風(fēng)光日子里,而街車不僅在此刻冷冰冰地見證了他身份的蛻變,也早就潛入了他的內(nèi)心,培植著他對(duì)車的依賴——就像我們大多數(shù)人一樣。
當(dāng)赫斯特伍德落魄到等候在劇院門口想找當(dāng)紅的嘉莉求助時(shí),橫亙?cè)趦扇酥g的屏障竟仍是盛氣凌人的座駕,而且是四輪大馬車:
他看見馬車載著紳士淑女們滾滾駛過——在這片劇院與酒店林立之地,夜生活的快樂才剛開始。
突然一輛四輪大車開了過來,車夫跳下來打開車門。還沒等赫斯特伍德反應(yīng)過來,兩位女士便快步穿過寬闊的人行道,消失在舞臺(tái)通道門口。③
正是車阻斷了這對(duì)昔日的亡命鴛鴦的重逢,而在他失望而歸時(shí),車還不忘要嘲諷似的刺痛他一下:“出租及私家馬車輕快地駛過,車燈閃爍如黃燦燦的眼睛。”④多日之后兩人終于相遇,也恰好是因?yàn)榧卫虍?dāng)天選擇了步行,車似乎才是說了算的因素。
到赫斯特伍德捱至生命的最后階段,車仍沒有要饒過他的意思:
走到四十二街時(shí),燈光招牌已閃耀成了一片。人群行色匆匆,各赴晚宴。在每處街角,透過明亮的窗戶,或都可見豪華餐廳里高朋滿座。四輪馬車往來川流不息,有軌電車上也滿載著乘客。
在疲憊和饑餓交加之時(shí),他真不該來這里。對(duì)比太鮮明了。連他自己都清晰地回憶了過去的風(fēng)光。⑤
如德萊塞本人寫的:“對(duì)比太鮮明了。”辛辣的對(duì)比不止一處:
此時(shí)一陣更凌厲的風(fēng)掃下來,他們更緊地瑟縮在一起。眾人攢擠著、挪移著、推搡著,毫無憤怒之色,沒有乞求之舉,不聞威逼之詞,完全缺乏由機(jī)智或友好帶來的生趣,只有飽含慍怒的忍耐。
一輛馬車叮當(dāng)駛過,里面有個(gè)人背靠著座椅。最靠近車門的人看得見車?yán)铩?/p>
“瞧那個(gè)坐馬車的小子。”
“他一點(diǎn)兒不冷啊。”
“唉,唉,唉!”另一個(gè)人嚎叫道,馬車已駛遠(yuǎn),不可能再聽到他的叫聲。①
已命薄如紙的赫斯特伍德似乎看見了曾經(jīng)的自己,就像他先前一再在恍惚中出現(xiàn)的幻象一樣。即使是描寫他的幻象,德萊塞也沒有放過他:“第一次出現(xiàn)這種情形,是他想起了車友會(huì)主辦的一次很熱鬧的聚會(huì),他是會(huì)員。他坐在椅子上,目光下垂,漸漸地感到舊友的談笑及觥籌交錯(cuò)之聲仿佛不絕于耳。”②此時(shí)——實(shí)際上任何時(shí)刻都是如此——車不再是個(gè)名詞,而是處于進(jìn)行時(shí)態(tài)的動(dòng)詞,還不只是一個(gè)短暫性動(dòng)詞:車是無情而有意的存在,車接著讓赫斯特伍德與眾流浪漢蹣跚行進(jìn)在被車馬碾過的污雪中,過去的榮光和眼前的馬車——四輪馬車——形成共謀,是準(zhǔn)備要將他奚落到底了。
當(dāng)然,車對(duì)于在蹺蹺板的那頭的嘉莉,也是格外的青睞。其實(shí)早在被迫跟從赫斯特伍德私奔的火車上,她的強(qiáng)韌性格就已初露端倪:“蒙特利爾和紐約!甚至就在此刻,她已直奔那廣袤而陌生的土地而去了,去看看她是否喜歡那些地方。她心里琢磨著,卻面無表情。”③幸虧有德萊塞的一支筆,幫助我們看到了她的內(nèi)心戲,否則我們也和赫斯特伍德一樣被浪漫的愛情感動(dòng)著。嘉莉“甚至就在此刻”已清醒得有些可怕了,她已迅速從淚水中看到了更繁華似錦的世界,而身邊的大堂經(jīng)理更像一種媒人而不是依戀的情人。在幾乎是被劫持著離開芝加哥的火車上,在瑟瑟顫抖和淋淋淚水之中,這個(gè)注定屬于更大的世界、終將登上更高舞臺(tái)的姑娘,已然打起了未來的算盤。此后當(dāng)她可以中途下車返回芝加哥時(shí),她放棄了機(jī)會(huì)。表面上她被男人的花言巧語打動(dòng)了,表面上她舉目無親,禁不住他的挽留而沒有下車,但別忘了,“她開始感到似乎自己可以掌控一切”。④她選擇與火車同行這一姿態(tài)意味深長(zhǎng),與其說是出于對(duì)男人的愛,不如說是出于對(duì)自己和城市的愛。“戀人靠邊站,悲傷腦后拋,死亡更別管。‘我要上路了’”——這不是原文,是筆者幫嘉莉說的心里話。我們不禁要敬畏起這個(gè)柔弱的女孩!她是一個(gè)非常追求物質(zhì)的女孩,但與此同時(shí),她的那種不滿足始終又不完全是物質(zhì)的。作為一個(gè)人,她真實(shí)無比,我們之中又有幾個(gè)能比她更高深、更高尚?而此時(shí),赫斯特伍德一手送她上了這趟通向遠(yuǎn)方的疾馳的列車,卻完全沒有意識(shí)到他在用自己的生命送嘉莉踏上征程。
起初跟從赫斯特伍德茍安于紐約時(shí),她只能仰望奢華的都市生活:“所到之處無不是香車寶馬、流光溢彩,而她卻完全置身事外。整整兩年了,她竟從未涉足其中。”⑤此時(shí),車?yán)^續(xù)充當(dāng)著計(jì)量幸福度的指標(biāo)。而當(dāng)她以自己的心氣、才氣和運(yùn)氣,贏得了劇院和觀眾,演藝道路越走越順暢、越走越寬敞時(shí),車自然也記錄下了她的軌跡:“放眼四下,錦衣、豪車、家俱、存款應(yīng)有盡有。”⑥車在她的生活中不間斷、不經(jīng)意地出現(xiàn),始終強(qiáng)化著她的上升趨勢(shì)。她的自食其力并不主要體現(xiàn)在藝術(shù)事業(yè)的成功而帶來的綠油油的鈔票上,而是她一旦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獨(dú)立價(jià)值,就能為此去堅(jiān)守并開掘,直至發(fā)揮出最閃亮的光彩。她為自己打造了一身足以征戰(zhàn)社會(huì)的鎧甲,而當(dāng)她每日披甲征戰(zhàn)時(shí),車就成了戰(zhàn)車:下班通勤是由劇院安排的(“演出一結(jié)束她便和洛拉坐車回自己屋子,車是劇院叫的”①);“白天里她們坐馬車兜風(fēng),晚上演出完后去吃夜宵”。②嘉莉?qū)账固匚榈旅劝l(fā)棄意,也是通過一次游車河活動(dòng)開始的。差不多也就在赫斯特伍德作了最后了斷之時(shí),嘉莉望著窗外紛飛的大雪心不在焉地說道:“今晚得坐四輪馬車了。”③
車的“自動(dòng)”敘事,不得不說是相當(dāng)殘酷的。車與德萊塞多次提到的森嚴(yán)的“墻”一樣,分割著人類的階層。墻的內(nèi)和外是迥異的世界,車輪的上與下也喻示著無常的人生。在論述文學(xué)創(chuàng)作/研究之物轉(zhuǎn)向時(shí),學(xué)者汪民安說:“物無論如何同人不是一種對(duì)立關(guān)系,也無論如何不是人要去探究的知識(shí)對(duì)象,相反,它類似于一種棲居之地,一種神秘的容納性的家宅,一個(gè)四方和諧其樂融融的溫柔之鄉(xiāng),它是一個(gè)微觀世界,但也是一個(gè)宏闊的世界。”④可見,人在幻想著能夠完全掌控物的時(shí)候,已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作為行動(dòng)元(actant)的物的反控之中。
行文至此,或許要面臨是否過度闡釋的詰問。然而,是否過于敏感,也取決于我們是否已傲慢得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感知變得遲鈍麻木。我們現(xiàn)在尤其需要的,是對(duì)物的一種再覺醒,要讓我們的意識(shí)尖銳到對(duì)物一觸即痛的程度,因?yàn)楫?dāng)今人類在被拋入虛擬的元宇宙與涌動(dòng)的物世界時(shí),如果因自大或畏懼變得更加惰怠,就必將為奴。
車作為一種本身就具有高度機(jī)動(dòng)性、施事性的器物,似乎在加快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事實(shí)上,車的快捷一直在比照著赫斯特伍德的遲緩。車敘事視角下《嘉莉妹妹》中的人物自以為在駕馭,實(shí)則在被駕馭著。自負(fù)的人們?cè)趭^斗著,但很難超越車的尺度。車在文明時(shí)代里,向來沒有缺席過:不論社會(huì)如何建構(gòu)它的存在,不論科學(xué)如何改良它的發(fā)展,轔轔車聲從未消逝。車一直在被操控與操控之間橫行。車在進(jìn)步,我們?nèi)祟惸兀咳绻?滤f的制服可以作為一種物對(duì)人的規(guī)訓(xùn),那么車何嘗不能碾壓人的自由呢?我們?cè)詾樵谶@個(gè)萬籟俱寂的宇宙里,只有人是活物,甚至早已不把神放在眼里,可我們突然又惶恐地發(fā)覺,其實(shí)自己一直飄搖在萬物有靈的海洋里。在當(dāng)今人工智能日益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難道我們還沒有意識(shí)到,原本尚具身形的物,可以在無形的世界里繼續(xù)延伸,直抵我們最深處么?當(dāng)AI越來越顯示出行動(dòng)元跡象的時(shí)候,尤其是在并沒有親人亡故的ChatGPT已經(jīng)能悲悲切切地寫出一篇悼詞的時(shí)候,我們還能駕馭好自己么?
責(zé)任編輯:胡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