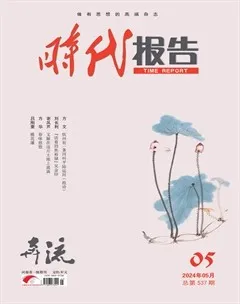文脈在這片土地上流淌

欽州地處嶺南,所謂嶺南者,在古代,就是五嶺之南,三代之前都屬于荒蕪之地,山川曠逮,人物稀少,財力微薄,一郡的人口和經濟還比不上浙江一帶的一個縣。
宋朝教育文化大家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寫道:“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于廉,則天涯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斯亭并城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
周去非認定的南轅窮途,欽州和廉州是一對難兄難弟,但欽州比廉州更悲催。真正如假包換的窮途。
宋朝周去非所寫的那個代表窮途的天涯亭,早已物是人非,那個位于“城之東”的天涯亭,經過多次遷移,已經從城東搬到了城南。
這個亭子既象征欽州曾經的荒涼與閉塞,更象征欽州文化主動學習中原文化,正衣冠,建學堂,守禮儀,以嶄新的形象屹立于祖國南大門的一座紀念亭。
古代的欽州,由于閉塞,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在這個荒蕪的地方,自生自滅,有的人一生終結,可能連個名字都沒有。
正是由于閉塞,從隋朝開始,欽州就被統治階級作為懲戒各種“犯事”官員之處,于是,在這荒蕪之地,一個又一個的“犯人”被流貶到欽州。欽州志書上記載有名有姓的就高達52人。這些人,大都是一些飽學詩書的文官,他們來到欽州,沒有過多沉浸在個人的悲憤之中,而是把滿身的學問開化欽州。
如長安三年(703年),被唐玄宗譽為“道合忠孝,文成典禮,當朝師表,一代詞宗”的文學界領袖人物,三朝宰相張說,因不肯作偽證陷害宰相魏忠良得罪武則天,從長安押送到欽州流放,從此,張說成為半個欽州人。
張說給欽州民眾帶來開放的文學思想,留下的詩作有十余首,其中有剛踏上欽州土地時作的《初赴欽州》。
張說謫居欽州,其人品、人格及文學造詣對欽州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固有的政治地位和才能、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質也對欽州吏治的改善、經濟的發展、社會風俗的變化帶來了隱性的促進作用。
對于背井離鄉的流放者,當然是身心都遭受到巨大的折磨,但對于欽州來說,何嘗不是一種幸運。
這些流放者來到欽州,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在欽州建功立業,建書院,修縣志,詠詩作詞,引領欽州文化藝術走上與國家發展同步的正途。
“去京師萬里”的欽州,在被動承接正統文化熏陶后,生化出欽州本土絢麗的特色文化,并一路前行,文脈薪火相傳。
在欽州遵化縣(如今的靈山縣)誕生了唐朝左相姜公輔。
姜公輔為大歷進士,德宗朝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于宰相),以直言敢諫觸犯圣怒而被貶為泉州別駕,居九日山東峰,死后埋藏于九日山。宋朝鄧祚作有《謁姜相祠墳有感》:
布衣崛起秉洪鈞,料事當年若有神。
三尺孤墳封馬鬣,一時直道犯龍鱗。
從容未見回天力,流落空聞棄海濱。
賴有高人秦處士,不妨筑室作居鄰。
姜公輔留下的文章有《對直言極諫策》等,還有《太公家教》,全文2610字,四言一句,哲理深,好讀好記,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誠禮也”。
姜公輔為欽州文人樹立了標桿,成為欽州文人代代效法的榜樣。
元符元年(1097年)大文豪蘇軾以“謗訕貶英州未幾再貶寧遠軍節度使,安置惠州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軍,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詔量移廉州安置”。在廉州期間,蘇軾多次“遨游欽州”,所謂遨游者就是遠游或漫游,蘇軾在遨游欽州期間,創作了一批詩詞,可惜大部已經遺失,只有清(康熙)《欽州志》收錄有蘇軾唯一留下的詩一首《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
馬革裹尸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人。
陣云冷壓黃茅瘴,羽扇斜揮白葛巾。
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清(康熙)《欽州志》同時收錄蘇軾《颶風賦》。
該賦描寫颶風“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觸。列萬馬而并騖,會千車而爭逐。虎豹懾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于一覆”,形象生動地描寫颶風的勢不可擋。
蘇東坡病逝后,欽州人不但建了東坡書院紀念這位大文豪,畫家還專門為其畫像,留下了蘇東坡頭戴斗笠,腳穿木屐的珍貴畫像《東坡笠屐圖》。如今,他留給欽州的兩件重要文物《東坡笠屐圖》和“游戲碑”被欽州市博物館收藏,成為珍貴的文物。
歷史在逶迤前行,宋朝以降,欽州教育事業蔚為大觀,成為各任官員的主要政績。
淳熙三年(1176年)岳飛之子岳霖任欽州知州。
下車伊始,岳霖以振興欽州教育為己任,特請《嶺外代答》作者,著名教育家周去非任教習,大力興辦教育,促進欽州文化教育更上一層樓。
淳熙六年(1179年),岳霖任滿,奉旨回京。民眾攀轅挽留,截路塞巷。
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林希元被謫知欽州。他大刀闊斧地辟荒地,勸農桑,薄賦斂,立社學,修橋梁,建營堡,固邊防,可謂一個全面開花的牛人。
他親自主持修建了18所社學,每間安排公田20畝作為辦學經費。
林希元深入到各家社學巡查,非常欣慰地寫道:“數月而后,教讀各以弟子見其父兄,共衣表、步履楚如也;進退、揖遜肅如也;諷誦、書仿朗如也。”
他親自編纂了嘉靖《欽州志》。嘉靖《欽州志》是研究明朝南方的政治、經濟、軍事、農業、社會生活等的珍貴資料,是一份寶貴的文化歷史遺產,一直保存完好地流傳至今。
林希元知州欽州三年,留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詩詞,他在一次到鄉下量田回來時創作了《至白皮丈田有述》:
忙里偷閑到海濱,朝風若為洗塵襟。
臨春出郭豈無事,自古均租即養民。
遇雨不妨衫袖濕,登山剛怕仆夫辛。
野人獻食無佳品,粗茗濁醪意自真。
這位在欽州品嘗“粗茗濁醪意自真”的知州,真把欽州當故鄉來經營了。
林希元詩中的家國情懷,與老百姓打成一片的親民行為,感情的真摯,讓欽州人至今還銘記于心。
在林希元這樣為和為民的官員引領下,到清末,欽州共建正規書院40所,社學30間,義學8間,私塾更是達到數百家,基本實現了在圩鎮或大村,村村有書院或社學或私塾。
林希元生前,欽州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專門為他建了生祠,春秋祭祀,為此,他非常自豪地寫下了《得欽州生祠春祭文有述》記述其事。
中原文明之光,就這樣溫暖了這片天之涯,成為欽州文化教育的河流,欽州人以中原文明為參照,整衣冠,改陋習,使欽州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祖國的西南邊陲。
在這些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就了農家弟子馮敏昌,終將以五嶺鴻儒的形象屹立于大清王朝。
他醉心詩詞創作,成為“嶺南三子”之首,留下了2000多首詩。他書畫師從翁方綱、錢載等大家,但最終超越自己的恩師,獨創了執筆法,奠定了他的書法地位;他教書育人,一生擔任過四所書院的院長,與王通的“王佐”教育并駕齊驅,當道以書來謂“有河汾禮樂之盛”。他主編的《孟縣志》成為“一代之宏載,千秋之杰作”。
他一生在欽州兩次發起修復兩座書院,嘉慶九年(1804年)發起修葺鰲州書院。
鰲州書院始建于明神宗萬歷年間(1573年—1620年),后被寇匪燒毀,馮敏昌父親馮達文發起重修倡議,完成了第一次修葺,但后來在一次大水中又被沖垮,馮敏昌子承父業,發起第二重修,這一次建成的書院,改名為“迴瀾書院”,其形“迨閣既然,云楣繡拱,鳥革翚飛”,其質“光氣熊熊照耀于中流兩岸,而上燭于霄漢,回映于州城者千萬狀焉”。欽州子弟讀書其中,“弦歌間作,波濤答樂,其樂無方”。
馮敏昌親自撰寫《州城迴瀾書院勸修小引》,認為修書院是不朽之功。文章雖然重在講述書院始建、重修的來龍去脈,卻體現出這位文化大家對教育肩負使命的高瞻遠矚。
“蓋聞不朽之一,在于立功。故立功者,可以立不朽也。然功之既立,亦且有久而漸朽者,又在有人焉以維持之,使其欲朽者,仍為不朽。則庶立功之人,長此不朽。”文字不算復雜,其深意卻值得好好揣摩。
他還在北京修建高廉會館,是公益先驅者。這位一生在河南、廣東擔任過四所書院講習的讀書人,一生做官政績不是很突出,但教育卻成為翹楚,他死后留下30多張當票,全是為了幫助貧困學子留下的借據,成為欽州自唐朝以來的最后一名鄉賢,入祀鄉賢祠。至今,廣西各類志書但凡要總結廣西歷史文化名人,馮敏昌成了絕對繞不開的重要人物。
“歷盡天華成此景,人間萬事出艱辛。” 馮敏昌如果九泉有知,看到當下那么多人崇拜他,一定深感欣慰。他實現了自己人生價值的“不朽”。
著名畫家齊白石對欽州情有獨鐘,一生五次出游,三次長駐欽州,時間達兩年之久,留下了13首與欽州有關的詩詞,寫下“此生無計作重游,五月垂丹勝鶴頭。為口不辭勞跋涉,愿風吹我到欽州” 的感人詩句。
著名詩人、戲劇家田漢也將睿智的目光投向這片土地,1962年到欽州采風,參觀欽州坭興陶時寫下《坭興頌》:
欽州橋畔紫煙騰,巧匠陶瓶寫墨鷹。
無盡瓷泥無盡藝,成功何止似宜興。
還有對英雄的欽州兒女的歌頌的詩《登欽州尖山》:
文峰如筆對雄城,欲濟無梁繞道行。
青紫齊腰包谷壯,白帆待孕午潮生。
尖山埋骨焦生炳,北海捐軀王有成。
多少南來好兒女,但為祖國一身輕。
日月經天,江河萬古。深厚的文脈,就像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孕育著欽州的文化自信,正以文化的力量書寫另一條平陸運河。
作者簡介:
謝鳳芹,中國作協會員,廣西作協理事。在《當代》《長篇小說》《文藝報》《中國藝術報》《延河》《安徽文學》《廣西文學》等50多種報刊發表作品450萬字,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家作品選》《小說精品集》《散文選刊》等。出版個人專著11部。獲國家級、省市級文學獎30多次,其中小說《天使》獲中國小說學會“中國當代小說獎”,散文《大地之上》《無名小橋》分別獲《散文選刊》2022年、2023年年度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