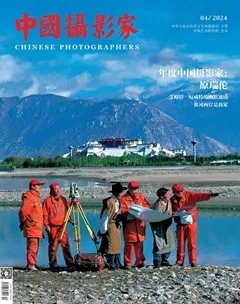媒介自反:論歷史先鋒派的攝影蒙太奇

1839年攝影的出現改變了藝術的走向,其物質還原屬性、可復制性以及對瞬間的捕捉能力,讓人們從傳統藝術的材料與形式中走向了技術美學的探索。但這一初創時期的攝影藝術就像每個時期出現的新媒介一樣,它若想成為藝術,那就必須以舊有的藝術規范作為美學的參照,才得以證明其“藝術”的合法性。致使早期攝影無論是從技術開發還是圖像生產的層面來看,都以古典主義美學體系與自然主義幻象作為樣板。
直到歷史先鋒派的出現,攝影才真正意義上邁進了現代藝術的道路。20世紀初的先鋒主義者以審美革命的姿態,不斷地沖撞傳統與資產階級的美學體系,他們專注于語言技巧,而非風格與主題,并從各個藝術領域中,解構與重組其手段策略,這就使得先鋒派在對于攝影藝術的探索中,將立體主義的拼貼手法,轉型為“蒙太奇”語言,并與之結合,從而對攝影藝術中媒介所反映的時間性與真實性兩個層面進行了自反性的另類表達。
一、攝影與蒙太奇
“蒙太奇”一詞,國內大多數文章中,將其看作是源于法語的“montage”,它隸屬于建筑學術語,指構成與裝配。但實際上這只是延續蘇聯的叫法,在同時代的魏瑪德國,這一術語有著不同的含義,用柏林達達主義者約翰·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1891-1968)的話來說:“蒙太奇這個詞在德國有特殊意義,這是德國工人用的一個字,原意是‘把零件拼成機器’。工人們在上班時就用蒙太奇三個字代表上班的意思。”[1]隨后,哈特菲爾德將蒙太奇與攝影結合,與好友喬治·格羅茨(George Grosz,1893-1959)共同探索出一門依靠東拼西湊形成的“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s)[2]的藝術形式。蘇聯與德國對蒙太奇的定義以及最初在藝術領域中的使用都有著差別,但作為一種關于不同元素組織的結構,其內涵趨于一致。

攝影蒙太奇,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相比較于蒙太奇在電影中建立的理論規范,它并沒有形成一整套嚴謹的美學體系,而是單純指向一種技術與形式結合的產物,雖然如此,但它依然能夠呈現出獨特的樣貌。攝影蒙太奇是指主要基于照片圖像,進行“剪切-異混-拼貼”的藝術形式,并常常配有文字、圖形等平面元素進行構成。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為什么不用“照片”作為其前綴呢?筆者認為這里有兩層原因,其一,是強調它的動態性,因為在當時關于攝影蒙太奇的制作是為了通過復制手段進行大批量宣發,使民眾都能夠輕易地接觸到為意圖,如同電影一樣,追求閱讀性的“展示價值”,而不是純粹作為現代主義藝術的唯一性審美對象的“膜拜價值”;其二,它也包括強調攝影操控性的多重曝光與利用暗房合成的作品。所以,將其翻譯為“攝影”作為前綴的詞,更能體現出先鋒派實踐的審美意圖。
如果在阿多諾的理論語境中,將印象派的繪畫語言表現出的筆觸對客觀世界的分解,再到立體主義的拼貼,視作蒙太奇最早的前身,那么攝影蒙太奇也有相似的過程。在19世紀中期,當時由于攝影技術的限制,人們很難獲取一張曝光正常的照片,所以,如法國攝影師愛德華·巴爾杜斯(Edouard Baldus,1813-1889)等人,開始用一種“停機再拍”的方式,將兩幅底片疊印,解決這一問題,并且一些攝影師為了獲得更大尺寸的照片,將前期所拍攝的多個畫面,在后期進行組合,來完成一張完整的圖像,等等,這一階段的探索可以認為是攝影蒙太奇的前身。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實驗只是在操作層面體現了蒙太奇的性質,以其最終所顯示出的有機統一的畫面來看,它與追求異質元素構成的攝影蒙太奇的審美訴求有著本質區別。


二、自反的雙重性:時間與真實
(一)時間的維度
凝固時間是西方藝術幾百年來一直探索的主題,直到攝影術發明,這一理想才得以實現,光學技術對瞬間的凝固與西方焦點透視的原則,成為攝影術初創時期對世界平面性還原的媒介規范,體現出一種古典主義審美價值的傳統與現代主義媒介自律的姿態,隨著歷史先鋒派的出現,將改變這一現象。歷史先鋒派本著反美學、反文化、反藝術的態度來展開激進的藝術實踐,攝影蒙太奇作為其核心手段之一,對于攝影藝術來說,呈現出一條不同的創作路徑,在筆者看來,路徑的形成源于攝影蒙太奇對攝影的時間與真實兩個范疇的另類詮釋。


攝影的瞬間性凝固,常常被理解為一種死亡,正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明室:攝影縱橫談》中強調:“說到底,我在別人給我拍的照片里看到的(我根據別人的‘意圖’看那張照片),是‘死亡’:死亡是這張照片的‘外貌’。”[4]而攝影蒙太奇卻與之相反,某種意義上,它是對凝固的激活,使其在所表現出的異質時空的矩陣中流動,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交織、并存以及互逆狀況中生成。
(二)真實的取向
紀實性可以說是攝影的天然屬性,到目前為止,人們依然將其視為“證據與文獻”承載物的代表,彰顯真實性的價值指向,即在場的光影。但對于攝影真實性的質疑也從未停止過。機械復制技術的冷眼旁觀,常常被主體的意志所蒙蔽,何況自身的景框與視點的限制,以及擺拍、搬演的人為夾持,讓攝影從來沒有真正走出虛構的邊緣。人們高度依賴影像來認識世界和建構世界,同時又不得不在其營造的情境中掌握分辨真偽的能力。而這樣一種關于攝影真實性問題的糾結,在歷史先鋒派所實踐的攝影蒙太奇中,從一開始就不曾存在。不是說他們不追求真實,而是先鋒主義者所認為的真實,從某種意義來說,并不是現象層面上的證據顯象,而是一種認知層面的真相。
歷史先鋒派反對自然主義式的象征系統,認為象征主義是一種偽裝成繪畫的不誠實的攝影。因此,這種經過撕裂與重合的攝影創作過程,是對傳統視錯覺主義美學的一種蔑視和反叛,攝影蒙太奇首先感興趣的并非是攝影題材,而是攝影的構成形式,及其所蘊含信息的感知力。正如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 Nagy,1895-1946)所認為的那樣,攝影蒙太奇不僅反情節、反內容,更注重圖像的形式及其能動性。這里的能動性并非來自敘事情節,而是來自形式本身的潛能。也就是說,影像所承載的信息,首先是通過形式構成所凸顯的震驚感激發出來的。正如上文提到的霍克的作品,她以非理性、偶然性營造的碎片感,正是對一戰后德國社會的混亂狀態、女性處境和民眾焦慮的真實演繹,映照著達達的無政府主義價值觀。而哈特菲爾德、利西茨基、亞歷山大·日托米爾斯基(Alexander Zhitormirsky)、羅欽科(Alexander Rodchenko,1891-1956)等人的大部分攝影蒙太奇作品,不同于柏林達達主義的非理性建構,而是通過改良,變成了一種“理性”的、相對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組織形式,但仍然伴隨著異質性關系的滲透和融合,它通常表現為一種古怪細節的激烈碰撞,在這種碰撞中,意義往往曇花一現,有時是一種苦澀的戲謔,有時則是一種詩意的褻瀆。[5]例如,在古斯塔夫·克盧蒂斯(Gustav Klutsis)的《斯巴達克聯盟》(All-Union Spartakiada,1928)(斯巴達克明信片設計)(圖3)作品中,藝術家通過水上運動項目相關的不同圖像,以充滿節奏與秩序的方式,來構成一種自由生命與革命信仰的辯證維度。

何為真實,或者從哪個角度來關注真實,攝影蒙太奇與攝影紀實性給出了不同的面相,正如在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2007)的影片《放大》(Blow-Up,1966)中,男主角通過一次偶然抓拍所深究的謀殺案,最終在結尾那一場沒有網球的小丑表演中,所揭示的結果那般—你看到的,并非是你真正看到的—體現出真實在現象與本質兩個層面之間的博弈,而攝影蒙太奇的實踐者正是基于此,通過解構窺見的真實,來傳達出感受的真實。攝影許諾給人類一個幻想,就是它能夠記錄真相。但是真相的“真實性”,有時被認為是建立在連續的、有機的現實關系中,有時卻被認為是存在于夢幻的、浪漫的革命理想里。也許,“決定性瞬間”只能記錄“瞬間的事實”,或者說它只是真實的一部分,而攝影蒙太奇體現了真實的另一部分,它潛藏在土壤之中,訴諸內在的心理與精神場域。
三、藝術他律:媒介自反的啟示
德國理論家彼得·比格爾(Peter Burger,1936-)認為,歷史先鋒派理論在兩個層面上被加以探討與界定,即歷史先鋒派的意圖與對先鋒派作品的描述。前者是指從生活實踐出發摧毀自律性藝術體制,強調藝術的他律性,并希冀“讓藝術回到生活實踐當中”,后者則是區別傳統有機性作品的非有機特征。他進一步描述,在有機的藝術作品中,結構原理支配著部分,并將它們結合成一個單一的整體,而在先鋒派的非有機作品中,部分對于整體來說具有大得多的自律性。它們作為一個意義整體之構成因素的重要性在降低,同時,它們作為相當于自律的符號的重要性在上升。[6]也就是說非有機內涵,瓦解了自柏拉圖以來的有機整體觀統攝下的人類的樹狀思維模式,而追求異質性、解域化、開放性與跨媒介的塊莖認知結構。以此,在先鋒主義者這里,攝影、繪畫、雕塑、設計、電影、戲劇、建筑、詩歌、文學以及其他無法被分類的日常物品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他們積極廢除自18、19世紀以來形成的知識分類系統,以及所孕育的媒介自律的審美觀念,而在此基礎上,構建全新的藝術審美立場與形式語言。攝影蒙太奇作為歷史先鋒派的最重要的實踐策略之一,從各個方面都遵循了以上意圖。
具體來說,從日常生活角度看,攝影作為當時的新媒介,所體現出的復制性與具象性,可以更好地進行觀念的表達以及革命理想的宣傳。從藝術層面上看,歷史先鋒派又不滿足于攝影媒介所體現的那樣一種通過技術謀劃的審美規訓。這兩種立場匯集在一起之后,它的首要任務就是通過對媒介的自反,來完成藝術自律體制的批判,從而進一步改造生活世界。
雖然在20世紀初,諸多先鋒主義者所采用的實踐方式豐富多樣,但攝影與蒙太奇的組合,算得上最為革命性的手段之一。首先,攝影蒙太奇的出現,為電影領域引進蒙太奇的概念以及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美學基礎。其次,攝影蒙太奇對今天的雜志、平面設計等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再次,攝影蒙太奇在當時相較于電影,更具有流通性,它的本質特征使其拒絕作為資產階級藝術自律體制的商品屬性,而是更多地通過書籍封面、插圖、海報等形式介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使每個普通人都能輕易地獲得與共享。最后,攝影蒙太奇基于攝影的物質還原屬性與復制性,將形式主義與現實主義統一起來,其技術所蘊含的創造性思維以及非有機結構,改變了傳統攝影表現客觀世界原有的形態與邏輯,形成了新的表達與觀看方式,為當代藝術視域下的攝影藝術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結語
攝影蒙太奇依據攝影與蒙太奇的雙重屬性,通過異質元素構建的非有機結構,所呈現的物像與現實的重組關系,以及融合多種藝術語言的策略,在20世紀初完成了其媒介自律性的批判以及將藝術與生活的融合。攝影在今天依然是展示與參與歷史構建和社會進程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影像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電影、數字視頻還是AI成像系統,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攝影的變體。而蒙太奇作為一種構成方式,存在于各種藝術形式之中,但它的使用完全取決于創作主體的認知思維。也就是說,它可以是一種有機模式的網絡,也可以是非有機形態的矩陣。面對當下技術的不斷同化,如何構筑新的藝術生產力,成為每個技術革命的時代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或許從攝影蒙太奇的非有機審美特征中可以探尋出一條解決之道。
(孟祥龍,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1] 周博:《剪輯理想圖景—“照相蒙太奇”的傳播及其中國境遇初探》,袁熙揚主編:《設計學論壇》第2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34-335頁。
[2] “photomontages”即合成照片的英文寫法,王瑞在《攝影百科》中將這個詞譯作“攝影蒙太奇”。
[3] [5] [美]拉茲洛·莫霍利-納吉著,周博、朱橙、馬蕓譯:《運動中的視覺:新包豪斯的基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4頁。
[4] [法]羅蘭·巴特著,趙克非譯:《明室:攝影縱橫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第22頁。
[6] [德]彼得·比格爾著,高建平譯:《先鋒派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62-163頁。
責任編輯/何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