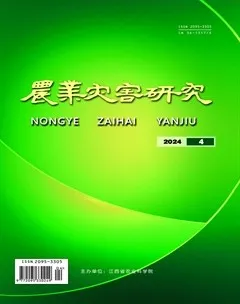吉林市雨澇風險模擬分析





收稿日期:2023-12-20
作者簡介:王元昊(1999—),男,吉林長春人,主要從事國土資源管理與規劃研究。
摘 要:以吉林市作為雨澇風險模擬分析的研究區域,將集水單元徑流量與吉林市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為模擬分析基礎,根據吉林市內降水量分布差異分析出集水流域,劃分集水單元,通過加權平均徑流系數計算每個集水單元的徑流量,比較地形面積與集水面積之間差值大小,依據差值數據得到雨澇風險預測區,對市域內雨澇風險集中程度進行分級。
關鍵詞:雨澇風險模擬;加權平均徑流系數;淹沒風險區分級
中圖分類號:TU998.4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2095–3305(2024)04–0-03
雨澇風險,又被稱為雨澇自然風險,是指一定時限因降雨量達到一定強度,超過區域內蓄水能力或城鄉部分地勢低洼區積水內澇形成雨澇災害,該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一定風險,威脅城鄉安全發展[1-2]。
以集水單元徑流量與吉林市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為模擬分析基礎,根據市域降水量分布差異分析出集水流域,劃分集水單元,通過加權平均徑流系數計算每個集水單元的徑流量,比較地形面積與集水面積之間差值的大小,并依據差值數據,得到雨澇風險預測區,并對雨澇風險集中程度進行分級。
1 研究區概況
吉林省吉林市,氣候類型屬于溫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3~5 ℃,受地形影響,由西、西北方向向東、東南方向的氣溫逐漸降低。1月平均氣溫最低,一般在-20~-18 ℃;7月平均氣溫最高,一般在21~23 ℃
之間,最高氣溫達36.6 ℃。山區無霜期為120 d,平原區無霜期則為130~140 d。降雨多集中在6—8月,全年降雨量約700 mm。地理位置介于東經124°18′
~127°05′,北緯43°05′~45°15′,位于長白山地區向松遼平原過渡地帶。地處東北平原中東部,境內水系發達,由松花江、拉林河、牡丹江3個水系的部分河段和支流組成,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降低,形成中山山區—低山丘陵區—峽谷湖泊區—河谷平原區四大地貌景觀。中心城市四面環山,三面環水,松花江呈倒“S”形穿城而過,水資源豐富,是吉林省重要水源涵養區,故而也常受洪患侵擾。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主要包括數字高程模型(DEM)數據、降水站點數據、行政區劃數據、土地利用數據、植被類型數據等,配合CGCS2000_3_Degree_GK_Zone_42投影坐標系進行分析。吉林市DEM高程數據源自ALOS衛星(Advanced Land Observing Satellite),其精度為
12.5 m分辨率;降水站點數據源于中國地面氣候資料日值數據集(V3.0),統計年份區間為2010—2020年,共計11年;行政區劃數據源于資源環境與數據科學中心;土地利用數據源于中國多時期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集[3];植被類型數據源于資源環境與數據科學中心提供的中國1∶100萬的植被類型空間分布數據。
2.2 研究方法
對吉林市2010—2020年的逐年降水站點進行克里金插值法處理,得到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柵格數據;通過吉林市市域DEM高程數據構建水文分析模型,劃分出集水流域和集水單元,集水單元掛接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柵格數據,獲得每個集水單元的降水量;根據植被類型數據和土地利用數據得到所需要的加權平均徑流系數,綜上計算出集水單元的徑流量和集水量,比較每個集水單元集水量數據與地形數據的體積、高度和面積,并最終確定吉林市市域內的雨澇風險預測區和風險集中程度分級情況,并依據風險程度確定雨澇洪澇災害預防措施(表1)。
在構建雨澇風險預測模型的流程中,各用地類型的平均地表徑流系數參照2019年版《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技術指南(試行)》的各類型生態系統地表徑流系數均值表和龔詩涵(2017)等學者在《中國生態系統水源涵養空間特征及其影響因素》中表述的各植被類型的各類型生態系統地表徑流系數均值[4]。
2.3 雨澇風險預測模型
/%=αi××100(1)
Sdem=(2)
S淹沒=Scell -Sdem(3)
式(1)~式(3),αi表示平均地表徑流系數(%);S某植被類型
表示某類型用地內的某植被類型面積(m2);S某用被類型
表示某類型用地面積(m2);表示某地類加權平均地表徑流系數(%);pre表示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m);GIS軟件計算集水單元面積Scell(m2);DEM為地形高度(m);Sdem為地形表面積(m2);S淹沒為預測淹沒面積(m2)。
3 結果與分析
3.1 降水量趨勢面分析
對201—2020年吉林省省域范圍降水站點的數據進行克里金插值半變異函數擬合分析,得到吉林省多年的年平均降水數據。在該研究時段,吉林省多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間趨勢線基本保持“中部高、東西低”“北低南高”的布局狀態,吉林省省域降水狀態,由西向東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平緩趨勢,由北向南呈現出逐漸陡峭地攀升狀態,因此,省域內年均降水量由北向南逐漸增多,由西部到中部逐漸上升、中部到東部逐漸下降,總體上看,東部降水量比西部高。
2010年吉林省各降水站點的年平均降水量呈現出“中部高,東西低”“北低南高”的地理分異布局狀態,表示出明顯的指向性狀態;2015年吉林省各降水站點的年平均降水量,呈現出“中部高,東西低”“北低南高”的分異布局狀態,表示出明顯的指向性狀態;2020年吉林省各降水站點的年平均降水量,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中部高,東西低,東比西高”“北低南高”的分異布局狀態,表示出明顯的指向性狀態。省域降水情況的空間分布特征與省地理地貌分布基本保持一致,吉林省西部、中部和東部的降水量呈現強烈的差異性,這決定了吉林省氣候總體可劃分為三部分,其中吉林市居于吉林省中心位置,其降水量位居全省最高(圖1)。
3.2 水文分析
采用12.5 m分辨率DEM高程數據,并按吉林市行政區的劃分提取吉林市域范圍DEM高程數據,通過填洼分析、流向分析、匯流河網分析、提取匯流河網、捕捉傾瀉點、河流連接分析等,劃分出吉林市具體的集水區和集水流域。
3.3 雨澇風險模擬與淹沒區分析
每個集水單元可能有多種地類和多個徑流系數,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技術指南(試行)》2019年版的表 B-2 各類型生態系統地表徑流系數均值,將每種地類占每個集水單元的百分比作為權重,然后將每個集水單元內的徑流系數乘以該地類的權重,進行加權求和,得到該集水單元的徑流系數,進而求算出集水單元地表徑流量。通過spatial analyst工具中的區域分析中的“以表格顯示分區統計”功能,將2010—2020年年均降水量去掛接集水單元,得到集水單元多年平均降
水量。
區域集水單元面積減去區域地表面積得到差值,差值即為預測淹沒區,而后將淹沒區通過GIS軟件轉為淹沒區點要素,對淹沒區點要素進行核密度分析得到雨澇風險分級結果。假設在集水單元體積一定的情況下,通過比較每個集水單元集水量和集水單元地形的體積、高度,即當某個區域集水單元面積大于該區域地表面積時,則該區域集水高度大于該區域的地表高度,可設定為預測淹沒區。根據淹沒區核密度分析結果可知,雨澇淹沒區主要分布在市域西北部的主城區及其外圍鄉村周圍(圖2)。
3.4 雨澇風險淹沒區分級
根據圖3所示,將吉林市市域范圍內雨澇淹沒風險進行分級,從而識別出雨澇風險斑塊,依據淹沒點核密度分析結果,按風險程度由高到低共劃分為Ⅰ級雨澇風險區、Ⅱ級雨澇風險區、Ⅲ級雨澇風險區和Ⅳ級雨澇風險區。Ⅰ級雨澇風險區主要集中在舒蘭市西部的亮甲山鄉、法特鎮、白旗鎮、朝陽鎮、天德鄉,龍潭區西部,昌邑區中東部,船營區北部,永吉縣北部,吉林市和蛟河市主城區也屬于Ⅰ級雨澇風險區;Ⅱ級雨澇風險區主要集中在Ⅰ級雨澇風險區的外圍緩沖區域,樺甸市主城區亦屬于Ⅱ級雨澇風險區;Ⅲ級雨澇風險區主要圍繞Ⅱ級雨澇風險區呈現帶狀分布;Ⅳ級雨澇風險區圍繞Ⅲ級雨澇風險區廣泛分布在吉林市市域自南向北方向上的東部邊緣地帶。
4 結束語
研究基于空間疊加分析和雨澇風險分析,精準識別市域雨澇淹沒風險。基于此,吉林市有關部門需要根據雨澇淹沒風險分級進行相應的防災分級措施,根據水源涵養空間特性,構建城區和鄉村雨澇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對于可能發生雨澇災害最為嚴重的Ⅰ級雨澇風險區,有關雨澇監測部門和防災應急部門應該在全年雨量最多的幾個月份進行實時雨量監測,以應對可能到來的汛情,并做好主城區防澇排水工程[5-6]。對于可能發生雨澇災害較為嚴重的Ⅱ級雨澇風險區應作為雨澇災害緩沖區域,以緩解重點雨澇災情;Ⅲ級雨澇風險區主要沿江、丘陵呈現帶狀分布,該區域需要做好民眾紓困工作;Ⅳ級雨澇風險區主要分布在市域的農業生產空間,需做好排洪工作[7-11]。
參考文獻
[1] 董偉,楊玲,康銘洋.安全韌性理念下的城市內澇災害風險評估[J].安全,2023,44(4):30-35.
[2] 倪麗麗.城市雨澇災害的精細化與快速化風險評估方法研究:以石家莊長安區為例[J].建筑與文化,2019(10):90-92.
[3] 石水源,謝思梅,謝榮安.利用遙感影像土地監測數據的城市化土地利用變化研究:以廣寧縣為例[J].測繪通報, 2018(8):102-105.
[4] 龔詩涵,肖洋,鄭華,等.中國生態系統水源涵養空間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生態學報,2017,37(7):2455-2462.
[5] 任劍,成鵬飛.城區雨澇成災模式分析及風險評估指標體系設計[J].采礦技術,2018,18(4):66-69.
[6] 王思敏,姜仁貴,解建倉,等.基于改進物元可拓模型的城市內澇災害風險評估[J].給水排水,2023,59(2):145-152.
[7] 劉希林,陳薈竹.廣東省熱帶氣旋、雨澇災害和地質災害生態風險評價(Ⅰ)[J].生態環境學報,2018,27(10):1890-1899.
[8] 陳薈竹,劉希林.廣東省熱帶氣旋、雨澇災害和地質災害生態風險評價(Ⅱ)[J].生態環境學報,2018,27(11):2047-2056.
[9] 張利君.國土空間規劃“雙評價”中氣象災害評價研究[J].國土資源信息化,2021(3):61-66.
[10] 夏曉琢,鄒嘉琪,金光日,等.圖們江流域洪水災害危險性評價實驗設計研究[J].延邊大學農學學報,2022,44(3): 82-89,109.
[11] 解明恩,陳鮮艷,張文千,等.雨澇指數在云南洪澇災害監測中的應用[J].災害學,2022,37(3):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