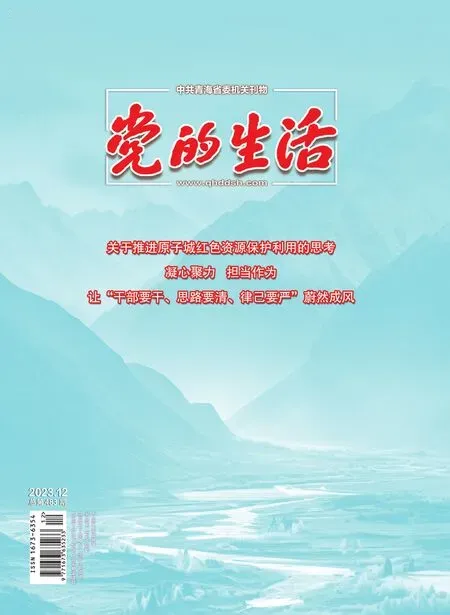青海數字經濟發展現狀調查研究
曲江尚瑪
青海處于國家生態功能區,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發展一些產業形式易受到限制,產業發展存在生產效率不高、企業創新能力不強、產業鏈條不完整,生產、管理、經營理念與發展不夠匹配等瓶頸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數字化轉型、數據要素賦能、數據治理等消除。數字經濟對接青海高質量發展,契合關系明顯,尤其是在算力中心構建上,優勢突出;對接地方公共服務、社會治理應用場景打造上,青海通過數字經濟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疊加效應、乘數效應、溢出效應、長尾效應、邊際效益。因此,發展數字經濟成為青海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路徑。青海要抓住智能化浪潮,發揮數字經濟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青海數字經濟發展現狀
(一)青海數字經濟發展初具規模
青海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對地方經濟的帶動作用,建成較為成熟的基于大數據應用綜合解決方案的“行業云”,具備一定的公有云和專業云的服務能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各類信息系統及數字化、智能化成果正在被青海企業所使用。通過開展國民經濟、社會領域的“互聯網+”,形成一批智慧政務、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數字化項目,如“智慧養老”“智慧政務”“智慧教育”等,“智慧+”類的服務正納入居民社會服務體系中。
(二)地方經濟體量、結構與數字經濟要素形成適配
2021 年數字經濟在青海生產總值的份額占比為25%,雖然低于預測值1/3,但數字經濟發展空間巨大。第三產業發展體量、空間、方式為數字經濟提供了比較舒適的發展環境,使第三產業與數字經濟結合有高嵌入可能。對新經濟形態、發展模式積極探索,受原有產業限制瓶頸少,數字產品消費處于低位,這些因素都幫助青海快速對接數字經濟模式,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后發優勢。在數字經濟環境下,經濟是外向的,青海經濟發展能夠擺脫空間、時間的限制,融入巨量市場,發揮長尾效應。
(三)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提供了有力支撐
青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快于全國,為地方數字經濟戰略的實施提供了良好保障;企業信息化、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為青海數字經濟打下了較好基礎,為進一步推進青海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平臺;數字技術使用方面有較大的突破,軟件業務收入增速全國最快,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高位發展,為數字技術集聚了技術力量。
二、青海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與不足
(一)青海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
青海在現有省級戰略基礎上,除了可以充分利用數字經濟本身優勢,如數字經濟報酬遞增、產業融合發展、政策疊加、知識能力擴散、數據溢出等,還在對接數字經濟上具有地方特殊優勢。
1.頂層設計優勢。數字經濟是青海加快推進生態高地和產業“四地”建設的新引擎,是青海“四種經濟形態”之一,青海通過戰略性發展思路,構建數字經濟布局,出臺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數字經濟發展,形成了“1119”數字經濟發展體系。目前,青海數字經濟高層規劃方面,政策體系完善、項目落地多,在融入實體經濟、公共服務、居民生活中的作用顯現,成果顯著。
2.數字區位、資源稟賦優勢。一是清潔能源優勢。青海省是全國重要的清潔能源生產基地,尤其水電、光伏發電等居全國前列。二是氣候優勢。青海氣候涼爽,年均氣溫5 攝氏度左右,適合數據中心、算力中心等對溫度的要求。三是環境優勢。青海位居青藏高原西北腹地,地質災害影響小,屬于地質災害輕度分布區;自然環境清潔,符合數字經濟設備對環境的要求。青海土地資源豐富,適合大規模數據中心、算力中心的用地要求,土地租賃成本低。四是區位優勢。青海地處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主線,是陸上絲綢之路西部通道、東西南北的橋梁與紐帶,具有發展數字經濟 “一體協同、輻射全域”的獨特區位優勢。
3.產業融合優勢。青海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信息技術產業運行良好。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如電信業務、寬帶接入、光纜覆蓋、互聯網使用、5G 基站等方面覆蓋率高于全國水平,具有較好的數字環境。另外,在地方數字化推進方面,“寬帶青海”“數字青海”布局基本形成;數字化產業方面,全省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重點企業累計完成軟件產品收入4018.3 萬元,15 家企業通過國家級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評定,5 戶企業成為全國工業信息化運行形勢指數企業。“四地經濟”“四種經濟形態”上,形成鹽湖綜合利用、鋰電、光伏制造、有色金屬及深加工、鋼鐵、煤化工、油氣化工、特色生態8 條循環經濟產業鏈。
4.資本拉動優勢。青海在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創新經濟、數字經濟資本獲得上具有很強的優勢,在項目使用上,成效顯著。因此,可以通過國家資本拉動,快速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數字高地,搶占數字經濟資源要素,實現數字經濟聚集,并通過良性循環,推進數字經濟長尾效應的發揮。
(二)青海發展數字經濟的不足
目前青海數字經濟發展如火如荼,但青海數字經濟發展還存在以下不足:
1.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比較滯后。國內高端智庫財新智庫發布的《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指數報告》中,青海數字產業化指數為268,數字經濟產業指數為0.4,數字與實體經濟融合指數為30.4,在省市區各項排名第29 位,西部五省數據中,與陜西、甘肅、新疆指數差距較大。青海產業發展模式仍較為粗放,產品附加值較低,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高技術產業鏈條延伸不足;融合發展不深。數字技術產業規模較小,缺少龍頭企業帶動,兩化融合不深;其他市場主體參與數字化建設的能力不強,動力不足;地方納入主流市場的體量小,承接產業轉移成效不明顯。
2.數據資源分析和挖掘能力還不足。一是數據要素的豐富度和準確性不高。地區當前布局數據中心的數據基本為沉淀性數據,而且數據的豐富度和準確性不高,尤其是對接全國層面數據需求成效不明顯。二是熱數據的及時處理能力還不夠高,并且離熱數據中心和主要消費地區比較遠,對發展熱數據有一定的限制。三是算力優勢發揮不完全。青海數據資源的分析挖掘以各大互聯網巨頭公司為主力,本省數據分析能力不足,難以滿足符合當前各類復雜應用場景的算法需求,深度挖掘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地方的優勢資源難以充分融入到數據計算中,利用地方資源反作用數字經濟發展效能體現不明顯。
3.數字經濟規劃和管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在數字經濟規劃上,還存在“數字經濟體制機制沒有理順”“數字經濟建設思路不清”等問題。尤其是企業層面,在數字經濟建設的頂層設計方面還存在偏差和差距,期望通過頂層設計推動企業數字經濟建設的思維較重。在管理方面,存在“管理科學水平有待提升,最先進的系統和模式使用方面存在水土不服”“信息企業建設追求一步到位的思想并且過分追求投資回報率”“對于數字經濟市場發展的不確定性還存在擔憂”等問題。特別是企業,覺得發展數字經濟是大勢所趨,但是覺得對本企業現階段發展益處不大,多持觀望態度。此外,在數字化人才建設方面,目前青海懂數字經濟建設的人才欠缺,造成了“對數字經濟認識不深刻不全面,雖然有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統籌規劃、工作機構、扶持政策,但是怎么做,做什么,還處在基礎認知階段,沒有創新的模式和做法。”“缺乏重點規劃布局”“對數字技術掌握不深,挖掘加工不夠,應用的路徑不清”“數字技術企業缺乏面向行業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難以滿足實體企業的需求”等問題。
三、數字經濟賦能青海高質量發展對策建議
面對新時代發展背景,青海發展數字經濟具有以下機遇:新一輪國家發展戰略加速實施,開創青海對外合作新局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構建青海產業優化新格局;生態發展理念的廣泛深入實施,健全青海綠色產業新體系;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加快構建,為青海帶來協同發展新契機;國內“新基建”全面提速實施,為青海帶來經濟發展新動能。但同時也面臨著經濟形勢挑戰和綠色轉型、競合發展、內生動力、產業變革方面的壓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青海高質量發展要做好以下幾點:
1.加強數字青海建設,培育數字經濟發展土壤。一是推動數字青海建設,推行政務數字化,協調數字端口建設,推進政務數據的協同共享,構建政務數字資源中心、大數據中心,打造政務數據庫,釋放政務數據資源價值;二是營造數字營商環境,推廣數字招商、企業注冊登記、稅務、工商管理平臺化應用全景,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營商能力;三是樹立數字經濟發展新思維,以數字技術的創新型使用為主要著力點,促進院校、企業、政府、社區凝聚開發數字城市應用場景,提升數字城市建設的專業性;四是同時組織開展數字城市、數字經濟專項培訓,提升具體人員的數字經濟專業知識和科學規劃能力;五是提升全民數字經濟素質,以地方全民發展需求為動力,強化地方居民生活、公共服務、行政事業辦理、醫療、出行、餐飲等的數字化建設水平,通過數字素質培育、智慧生活推廣、便民數字化端口打造、智慧社區支撐等推動數字化素質水平提升。
2.挖掘打造青海特色場景,開放場景引鳳項目。一是特色場景建設,強化青海數字經濟產業譜系,打造青海特色、重點產業數字化應用場景,并助推場景的區塊鏈、供應鏈鏈條延伸,形成“建鏈、補鏈、強鏈、引鏈”的場景使用推廣模式,促進青海智慧的更大范圍推廣。二是應用場景平臺建設,加快青海場景資源目錄,對接主要發展主體需求及青海區域內生產生活需要,打造數字經濟虛擬平臺,形成數字經濟場景聚集“高地”。三是精準對接、推廣應用場景,形成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場景目的地,發揮應用吸引項目落地的“凹地”效應。
3.培育數字經濟平臺,促進數字要素聚集。一是培育數字經濟平臺型企業,構建虛擬產業集群。二是強化平臺型企業(如電商平臺,通訊平臺,共享平臺、直播平臺、虛擬企業平臺、采購平臺、學習教育平臺等)進駐力度。三是加大特色產業和優勢企業的支持力度,推進平臺成果轉換,數字化平臺轉型。四是聚焦醫療、公共服務、教育、健康等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及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產業在區域內的推廣,挖掘建設區域內潛力企業平臺,并支持培育。五是注重區域內數字經濟產業的平臺體系建設,形成以主要城市帶動其他城市、主城區帶動副城區、主要數字經濟產業聚集區帶動周邊區的發展態勢,并促進數字經濟核心要素聚集,形成要素聚集“高地”;六是形成數字經濟產學研一體化研究基地,加快數字創新能力建設。
4.創新數字管理模式,營造數字政策“凹地”。一是建立青海特色數字經濟保障體系,促進數字政策、數字化人才、數字化金融等的注入,提升數字經濟保障能力,提高“凹地”吸引能力。二是構建青海地區產業協同、溝通協同、需求對接、招商引資、場景宣傳等內容綜合的政策鏈,制定支持技術突破、數據資源開放、場景創新構建、企業主體培育、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化平臺構建、人才梯度構建等一系列政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政策精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