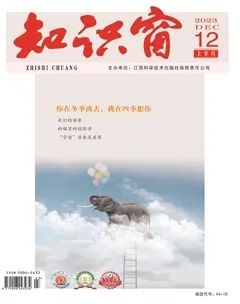一顆有理想的大棗
丁泳丹
它從枝頭探出頭來,滿意地看著自己圓潤的身材和有光澤的皮膚。躲過了炎炎烈日,歷經(jīng)四個多月的磨煉,它終于成熟了。大自然母親把陽光的顏色織進(jìn)它的紅裳,慶祝它即將開啟新的人生。
不,是“棗生”。
它是一顆大棗,一顆有理想的大棗。
藍(lán)天白云是它的伙伴,日月星辰賦予它智慧,母親河涵養(yǎng)了它溫潤的品性。俗話說:“南荔枝,北冬棗,百果王。”八月荔枝已下市,恰是冬棗正當(dāng)時。可它有點(diǎn)疑惑,明明自己是秋天出生,為什么被人們稱作“冬棗”呢?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冬”并非指冬天,而是代表晚熟的意思。相比其他果物,棗樹成熟期比較晚,果實足足要孕育120天以上,又因為北方天氣冷得早,因此得名“冬棗”。
當(dāng)然,它還是一個妥妥的“甜妹”。它善解人意,甜得恰到好處 ,這是一種沉靜與踏實的甜,不會讓人覺得膩。腹有詩書氣自華,想來是歷史文化的養(yǎng)分才能積淀出這富有層次的清甜。傳說棗的族名是黃帝所賜,當(dāng)年黃帝外出狩獵,又饑又渴,發(fā)現(xiàn)了脆甜可口的紅果子,便寫下一個象形字“棗”,取名“找”,意為找到果子。但因為口音的緣故,便口口相傳念成了“棗”。雖然這是個傳說,但據(jù)史料記載,早在三千多年前,古人就開始吟誦棗,《詩經(jīng)》有曰:“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中國最早的一部訓(xùn)解詞義的書《爾雅》首次記錄了棗的家族成員,其記錄的周代棗品種已有壺棗、白棗、酸棗、齊棗、羊棗、大棗、填棗、苦棗、無實棗等十一種。棗也與白居易、蘇東坡等名士結(jié)識,或是有幸生長在文人大家門前的棗樹上,也漸漸成為一種喜慶的文化象征。
天降大任于斯“棗”也,除了具有豐富的實用價值,棗更是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它想著,定要不負(fù)眾望,成為一顆優(yōu)秀的大棗。正因如此,它做了很多未來的規(guī)劃。它望著自己的小伙伴坐著貨車,駛向林立的高樓大廈,涌入車水馬龍的熱鬧。聽長輩說,趕在“頭茬”就業(yè)的棗能輕輕松松地在市場上獲得不菲的身價。
不過,它才不想這樣膚淺地度過一生。它是一顆有理想的大棗,它想見到更多風(fēng)景,不能局限于被“鮮食”,于是便靜靜等待著。漸漸地,它不再爽脆,皮膚有了皺紋,不再光鮮亮麗的它被來往的人們忽視。可是,它并不難過,因為這是自己升華的必經(jīng)之路。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沉淀出更多糖分!
待它通體變成深紅色,褶皺的外表如隨風(fēng)飄揚(yáng)的披風(fēng)般威風(fēng)凜凜地裹住飽金黃的果肉時,它總算登上了一生的高峰。成為干棗,它便有了更多價值,熬粥煮湯、入藥保健,或是化成棗泥被面皮幸福地裹住……初出茅廬的時候,棗子經(jīng)不住碰打,因為太脆,容易留下傷疤,甚至是裂開壞掉;如今,軟軟的外皮下是更加堅強(qiáng)的內(nèi)心,沒有什么能再讓它腐爛,這份堅守?fù)Q來的蜜甜,可以不折不扣地保存好些年。不,應(yīng)該是綿延不絕——紅棗孕育了獨(dú)特的紅文化,最終與其他文明成果匯聚成浩浩蕩蕩的中華文明。這是傳統(tǒng)的甜,是踏實的甜,是勤勞的甜,它不負(fù)自然哺育,不負(fù)果農(nóng)栽培,不負(fù)自己的追求,最終濃縮成一顆有理想的大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