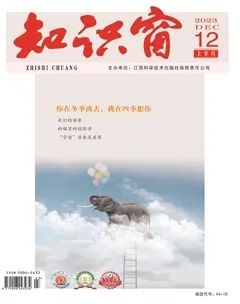矮身換肩,能挑重擔
段奇清
在我的家鄉江漢平原,擔子分為兩種:低腳擔和高腳擔。前者叫擔擔子,比如用兩個桶擔水,用兩個草架子擔草等,后者主要是挑捆子(也稱“挑草頭”),用草葽子將收割后的稻禾、棉梗、蘆葦、柴草等束捆起來,再挑回家。低腳擔用的是扁擔,由竹子制作的竹扁擔,或者由樹木做的木扁擔;高腳擔只能用樹木做的沖擔。
“擔”與“挑”的方式也不同。低腳擔,兩端“掛”的物什幾乎要垂到地面;高腳擔,沖擔兩端的草頭往往與肩齊。低腳擔的扁擔是扁而平的;高腳擔的沖擔兩端各有一個鐵制尖尖的角,使用時把這個角插入草頭,然后“挑”起來,在兩端的草頭都被挑起后,挑擔人站立起來,將雙手移到沖擔的中間,在獲得平衡后,將前面的一端輕輕往上一揚,借著這股力,擔子就到了肩頭。鄉人稱擔子這樣上肩是“打擔子”,“打”得漂亮的,如同做了一個輕盈的、優美的舞蹈動作,只有農活熟練的人才能這樣。青澀的小伙往往是將一端的沖擔角插入草頭后,再轉過身,蹲下,插好另一端的草頭,雙手再慢慢移到沖擔中間的平衡點,努力直起身來。這種上肩方式不但累人,而且挑不了重擔,更沒有“打”擔上肩的瀟灑自如。
沒有這種技能的人只能擔低腳擔,這樣卻受到許多限制,比如人擔了擔子在高農作物地里就無法走動。高腳擔就不會被高農作物阻礙,且由于沖擔兩頭翹,走起來時挑著的草頭隨著邁動的步子起起伏伏,人就輕松不少。不過,它也有不足:不能像掛著扁擔兩端的低腳擔可以隨時隨地放在地上歇著——因為放在地上的草頭又要吃力地“打”起來。挑高腳擔子的人一般不會把草頭放地上歇著,所以要不斷來回換肩。
把擔子“打”上肩,是挑高腳擔的第一個關口,換肩更不容易。記得第一次挑高腳擔,我總不敢換肩,雖說試著換過,那沖擔將肩上的皮肉撕扯得生疼,只得作罷。擔低腳擔時,我是把擔子放在地上,然后把空著的扁擔放到另一個肩頭,再把東西擔起來。
第一次挑高腳擔,我走了一百多米,實在累得不行,只得把草頭放在地上,打算再吃力地來一次“屙屎上肩”。正歇下來喘粗氣時,叔叔挑著擔子打身邊經過,見到我,說:“清兒,不會換肩吧,我來教你。”說著,他做了示范動作。只見叔叔的擔子極其輕松地從左肩換到了右肩,又從右肩換到了左肩。幾輪示范下來,我終于看出了門道:換肩時將前面一端的草頭輕輕往上一揚,雙手趁勢托住沖擔,在這一瞬間,人迅速地稍稍矮下身去,身子一轉,擔子就到了另一個肩頭上。換肩成功后,我欣喜中卻有著幾分羞愧。叔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說:“初出茅廬,處處逞強,人就要吃啞巴虧。”我的臉更紅了,“仗著在學校學習成績好,干農活時我從不向人討教。”我紫紅著臉,卻有所悟地對叔叔說,“將擔子換到另一個肩頭上,雖說是自助,或者說是自個兒的事,可也得矮下身段。”叔叔聽了一笑,說:“這就對了!人在這世界上,就是要矮下身段。這樣,才能時時得到他人的幫助。”
此后,我從只能挑三四十公斤,到能挑五十多公斤的高腳擔,走上幾公里路,也不覺得太累了。我遇事向人請教,只兩三年,便游刃有余地在各種農活中轉換,輕輕松松地成了干農活的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