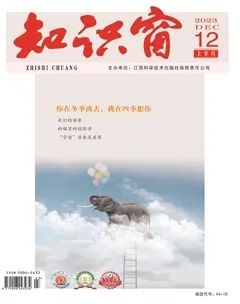橘子紅了
申功晶
白居易在《宿湖中》中寫道:“浸月冷波千頃練,苞霜新橘萬株金。”此詩中的“新橘”指的是我家鄉(xiāng)洞庭西山的特產(chǎn)橘子“洞庭紅”。很多年前,連續(xù)劇《橘子紅了》在東山陸巷古村取景開拍,讓這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地方著實火爆了一段時間。
說來奇怪,別處的橘子在中秋前后陸陸續(xù)續(xù)上市開賣,而我家鄉(xiāng)的“洞庭紅”要在霜降節(jié)氣之后才上市,有詩曰:“霜降莫愁時果少,客船爭買洞庭紅。”明末清初小說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里有一則故事《轉(zhuǎn)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話說明朝年間,吳地書生文若虛想下海經(jīng)商,苦于沒有本錢,鄰居張大贈了他一兩銀子。彼時,恰逢柑橘上市,文若虛信步街頭,“只見滿街上篋籃內(nèi)盛著賣的: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皸,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這便是洞庭西山所產(chǎn)之“洞庭紅”。文若虛用一兩銀子買下橘子百余斤,本意打算囤在艙內(nèi)用于途中解渴。等漂洋過海到了吉零國,其他同行客商各自上岸交易,文氏留下看船,他打開那簍紅橘,但見“擺得滿船紅焰焰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吸引了岸上無數(shù)眼球,竟被當成稀世珍品一搶而空,文若虛賺得紋銀上千兩,自此,時來運轉(zhuǎn),成為當?shù)匾桓弧?/p>
其實,早在唐朝,“洞庭紅”就被列為貢品級特產(chǎn)。當年,白居易在蘇州擔任刺史時,年年要來洞庭西山,親自挑選每一個上貢進京的橘子,故作詩:“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
“洞庭紅”到底有多好吃?三國時期,世家子弟陸績六歲那年,隨父拜見袁術(shù),袁術(shù)拿出橘子招待客人。大概是橘子太好吃了,年幼的陸績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偷藏了三個在懷里。臨別之際,陸績躬身拜別,橘子掉落在地上,袁術(shù)打趣道:“你來我家玩,怎么還偷藏橘子。”陸績跪地答曰:“橘子很甜,我想帶回家給母親嘗個鮮。”正是因為這件事,讓陸績在“舌戰(zhàn)群儒”時被諸葛亮借機嘲諷。
每年深秋,我叔祖母的大床底下總擱置著一簍晚輩送的“洞庭紅”,她習慣飯后吃上半個,美其名曰“消食”。父親有一手烹制甜點的絕活,他將紅橘和糯米小圓子放一起煮,做成橘紅、白玉相間的橘絡(luò)圓子,一碗熱乎乎下肚,味美管飽。
古人喚橘子為“木奴”。三國時期,丹陽太守李衡種橘千株,臨終前對兒子說:“我給你留下了一千株木奴,它們不吃不喝,還可以賺錢養(yǎng)家。”果不其然,等橘苗長成橘樹,每年出售橘子,便可獲絹數(shù)千匹,李氏后人過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
其實,現(xiàn)實中,靠賣橘子維持生計遠沒有想象中那般瀟灑、愜意。有一年深秋,我踱步至葑門橫街,一個年逾古稀的老嫗挑著兩擔沉甸甸、紅艷艷的“洞庭紅”,邊走邊叫賣。我估摸了一下,有二三十千克重,我叫住她,用手指按了按橘皮,很有彈性,橘肉也是新鮮的,于是稱了一點橘子。
到手的橘子個個飽滿,水靈靈的,一如《橘子紅了》里的女主角秀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