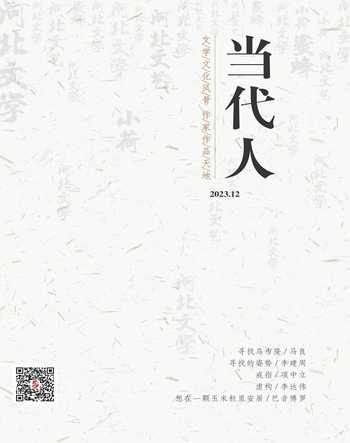尋找的姿勢(評論)
尋找是文學的一個基本母題。在世界最古老的神話《吉爾伽美什》中,身為國王的吉爾伽美什在自己的好朋友恩基杜去世后,便踏上了前往世界盡頭尋找人生意義的旅程,也正是在千辛萬苦的尋找過程中,增長了戰勝死亡的智慧。這一極具象征意義的神話故事呈現出的是一條人類精神探索的路徑。千百年來,不同時期的作家在這條路徑上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到了當下,這一文學姿勢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向性,同時又增添了某種形而上的內涵。
在馬良的《尋找烏布隆》中,首先引發讀者興趣的并不是“尋找”這個動作,而是一個顯得陌生而神秘的詞匯:烏布隆。什么是“烏布隆”?這是一個無法用百度解決的充滿神秘感的詞匯。無論是人名還是地名還是別的什么,都具有某種神奇的召喚力。讀者在閱讀這篇小說時會不自覺地加入這樣一個解謎的行列。閱讀行為本身變成了一個解謎過程,這使得小說的閱讀顯得輕松和順暢。
隨著故事的展開,烏布隆在小說中呈現出不同層面的文化意涵。
這個名詞首次出現是在二舅的“烏布隆玉石店”這個門臉中。這是世俗生活意義上的一個實體名詞,它關聯著二舅的日常生活,同時也是故事的一個基本承載空間。與眾多單純復制店面的模仿者的失敗不同,二舅的生意成功得益于真正的玉石愛好者的身份。二舅不僅會向顧客介紹各種玉石的品質與做工,而且還能準確說出多種巖石的形成年代,甚至礦物組成。這種準專家級的身份使得二舅在眾多的經營者中脫穎而出。在當下,各種文玩收集者甚多,然而多數并不具備基本的專業素養。“國寶幫”的盲目而熱烈的行為背后,除了意外之財幸運降臨的期許之外,更有一種用實際行動填滿生活空虛的渴望。與之不同,二舅的行為邏輯超越了盲目沖動,更多了一種理性探求色彩。
作為一個異己性的名詞,“烏布隆”在二舅生命中的出現,來源于他給人壘豬圈時發現的一塊殘損的石碑。作為一個界標,這塊石碑標示了二舅兩種不同的生命體驗方式。石碑上經過刀劈斧砍仍能夠辨別出的三十九個字中,赫然出現了“豎石訖成表言? 烏布隆? 如律? 斗出”的字樣,正是這最完整的最后一行字跡,徹底改變了二舅的生命軌跡。“烏布隆”三個字及其攜帶的歷史之謎開始在二舅的生命中發芽、生長。在獲得世俗意義上的經營玉石店的成功之后,由語言深入歷史進而追尋歷史真相的強烈欲望成了二舅最重要的人生課題。正是通過語言的連接,個體生命和歷史文化產生了內在呼應。也只有在這個層面,世俗意義的日常生活在二舅的生命中發生了動搖。正是個體生命和某種神秘的文化共同體發生了共振,讓他看到了生命的超越性價值。
烏布隆包含著對自然的崇拜和對歷史的追溯,但是馬良并不滿足于此,在接下來的敘述中更是包含了對生命自我完成的追求。殘損銘碑上的三個字,在二舅的想象中變得越來越富有詩意。它或許與北方少數民族突厥、黨項有關,或許與成吉思汗東征擄掠回來的族群有關,不過小說并沒有在這些似有似無的線索中有任何進展,而是轉向了二舅的生命體驗本身。這塊烏黑色的石碑不僅是烏布隆玉石店的靈魂,是二舅生命中的幸運石,更是美好追求的象征。雖然小說通過將心臟病置換成心靈感應這樣一個細節,解構了石碑在二舅心目中的持續升華,但是卻在結尾進行了浪漫主義式的收束。星星和石頭的重疊,使得小說在整體風格上多了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是啊,抬頭望見星光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呀!可是日常生活現實已經層層遮擋了這層詩意的星光,我們和詩意生活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遙遠越來越不可即。雖然我并不認為這種理想主義能夠解決我們的現實困境,但是仍然愿意相信這或許是一個出口,一個與美好相遇的可能的出口。從現代性的底層邏輯來看,這當然是不徹底的,不過我認為這種不徹底性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無論是對于作者來說,還是對于讀者而言。
需要強調的是,小說多重意味的呈現是通過特殊的結構實現的。作為敘事人的“我”和作為主人公的二舅,承擔了不同的敘事功能。作為敘事人的“我”是觀察者和見證者,是被二舅的行動所影響的,同時這個“我”也在“勸說”著讀者加入到這一尋找的行動中去。如此以來,實際效果是作者邀約讀者共同加入到了這樣一個行列之中。我們暫時從瑣碎的生活焦慮中抽身,踏上這一“生活在別處”的經驗旅程,并在這一旅程中獲得一次深入心靈深處觀察自我的機會。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這種經驗并不是被鼓勵的。正如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所描述的,中國人并不愿意背井離鄉到遠方,除非是被迫上路的。盡管當下很多人在旅游的意義上追尋詩和遠方,但是短暫的喘息之后仍然是困于一地雞毛的日常,真正的精神遠游極其稀少。正是在此處,小說以特殊的結構觸及到了生活的痛點,呈現了一種主動尋求的意外,一種無法預知的可能性,一種對未知的好奇和恐懼,讓人們在信息圍困中體驗了一次重新組織自身的可能,讓凌亂的生活多出了一層意義。
如果容量足夠大的話,小說的情節設置其實可以處理得更為曲折和婉轉些。對于現代人來說,所有行動的最終結果并沒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尋找這一姿勢本身,是在這一過程中淬煉出來的人生智慧,是因行動而來的跌宕起伏的心理褶皺。
(李建周,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