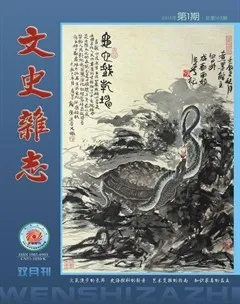清代宋詩運動與碑學比較研究
楊陽
摘 要:清代早期,“禰宋”詩風和書寫金石文字各為詩學、書學的取法方向,也是宋詩運動和碑學興起的萌芽。至清代晚期國運衰微之時,文藝思潮從主流的追求秀美風格,轉變為追求雄強風格。宋詩運動與碑學正是晚清文藝思潮追求雄強風格過程中,趁勢而起的兩大高峰。
關鍵詞:稱宋;碑學;雄強;相互影響;高峰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朝代。它曾經歷了“康乾盛世”;中期社會矛盾逐漸凸現;晚期則內憂外患驟至,政治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清代早中期,在清王朝高壓統治下,社會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文藝主流思潮偏向于“秀美”的風格,文學上如王世貞主“神韻”、納蘭性德工小令,書法上推崇董其昌、趙孟頫,流行秀美的帖派書法。而清代中晚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變化,學術上“乾嘉學派”和今文經學興起,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文藝上則從各方向不自覺地探索求變,都轉到追求雄強的風格上來。宋詩運動與碑學的興盛即為追求雄強風格的例證。
宋詩、碑學運動興起的比較
胡適在1922年為《申報》創刊50周年所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里說:“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于‘宋詩運動’。”[1]這大概是最早提出“宋詩運動”的文獻了。其實,從清代一開始,黃宗羲等為代表的一批詩人為改變明代前后七子“詩必盛唐”、師法唐詩的做法,而轉向學習宋詩,這便可看做“禰宋”的宋詩運動之濫觴。但清代早期詩學主流,仍主要宗法唐詩,游國恩稱之“祧唐”。
以王士禎為例,他的一生大半處于清朝政權逐漸穩固的時代。作為順治進士,他也逐漸成為當時頗有創見和影響力的詩人,被稱為“一代正宗”,其主張學習唐代“神韻”詩風。他曾選錄王維以下四十二人的詩為《唐賢三昧集》,目的是為了“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2]。又如沈德潛主張學習漢魏盛唐的體格聲調,稱“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3]
清代早期,反映民間疾苦的詩文大大減少,轉而為政治歌功頌德,或注重體裁。在書法藝術上,豪放雄強的書風與清初需要的穩定統治格格不入,燦爛輝煌的明末浪漫主義書風也只是曇花一現,為統治者宗“二王”、宗趙、宗董所取代。“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講子昂。”[4]統治者的提倡,加上張照、劉墉、王文治等書家的推動,帖學達到極盛。
清初王朝政權穩定后,經濟、文化都有極大發展,但統治者對于漢族士大夫的思想管控極為嚴格,文字獄可稱空前絕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極盛,士大夫人人自危,經世致用之學充滿危險,動輒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所以學術界也大多逐漸轉為考據之學。考據之學則對詩文取向和藝術取向都有重要影響。
以詩學來看,在考據之學直接影響下,產生了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肌理說”。在考據學間接影響下,清人與宋人重讀書、以學為詩相契合,與宋人“史詩”說相契合;另一方面,宋詩本身敘事詳明、淋漓奧博的風格,與考據學影響下的清人思維剛好契合,于是宋詩風尚逐漸流行。朱彝尊為考據的領軍人物,他是先宗唐詩后改宗宋詩的較為有影響力的詩人,向來被視為清代“宋詩運動”的前驅,備受后來宋詩派和同光體詩人的推崇。同時朱彝尊浸淫金石,又以隸書著稱清初書壇,被視為碑學萌芽階段最重要的書家之一。書法上,考據學者尋碑過程中增加了取法對象,逐漸形成蒼茫雄強的審美意識。
清代早中期,宗宋詩學與碑學萌芽主要是通過考據學的興起聯系起來的。而這樣的聯系太過于偶然性,或者說,宗宋詩的詩學審美和好碑學雄強的審美都還處于不自覺階段。例如袁枚反對詩學唐宋之分,但主張“當變則變”:“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也,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于詩之本已失矣。”“當變不變,其拘守者跡也。”[5]與袁枚齊名的趙翼,有詩曰:“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上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又云:“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常。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設唐?”又如“揚州八怪”的書法,并不是都取法金石,而是多方探索,藝術追求上都是求新求變,但各自風格突出,獨具創造。在這個階段,并沒有較為突出的唐詩、宋詩對立,也沒有突出的碑學、帖學的對立。
宋詩運動與碑學高峰比較
清代后期,爆發了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清代學術由古文經學轉入今文經學,宋詩運動與碑學逐漸興盛,并迅速風靡全國,分別成為詩學和書學的主流。包世臣《藝舟雙楫》有記錄:“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6]也正如前文提到胡適先生所說,那個時代的詩人大多屬于宋詩派。碑學方面也正是因為阮元、包世臣、何紹基等碑學理論大家的宣揚,碑學影響逐漸擴大,形成取代帖學之勢。
如果說清代中期宗宋詩、學金石還不夠自覺的話,那么,到咸豐、同治以后,宋詩派和碑派已經成為人們自覺追求的主流風尚了。
考察宋詩運動代表人物,無不是以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為宗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但贊成碑學,甚至有的就是碑學大家。而一般碑學家則多贊成宋詩運動,很難找到反對宋詩的。
程恩澤是宋詩派的直接開啟者,在詩法上,明確主張效法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獨于江西社,旆以杜韓幟”[7]。同時,程恩澤也研究金石,[8]且與碑學家阮元并稱為嘉慶、道光間儒林之首。何紹基、莫友芝、鄭珍是程恩澤門生,更是宋詩派的中堅力量,而何紹基、莫友芝皆為碑學代表書家;鄭珍亦好金石,篆書學習鄧石如,是典型的接受碑學思想的人物。曾國藩作為宋詩運動的贊成者和推動者,也明確主張碑帖兼之,并不反對碑學。
作為宋詩運動的接續者,“同光體”代表人物沈曾植、陳三立、陳衍、鄭孝胥等,皆為贊成碑學的詩人,沈曾植、鄭孝胥還是重要的碑學大家。可見宋詩運動和碑學有著較為特殊的聯系。
“禰宋”和碑學在清代早中期都是不自覺形成的。它們都受考據學的影響。至清代中晚期,隨著社會的巨大變動,主流學術轉為今文經學。今文經學主經世致用,以改變內憂外患的國勢,體現在文學和藝術上則是崇尚雄強和壯美的風格;而宋詩風格足以暢情,碑學風格足以雄強,宋詩運動和碑學便迅速成為文藝主流的追求。
清人邵長蘅在《研堂詩稿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論述:“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而能泛逸唐軌,大放厥詞。唐人尚醞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贍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9]可見詩于“祧唐禰宋”過程中,宋詩成為師法主流,而唐詩則成為這種主流的對立面。
蕭華榮先生在《中國詩學思想史》里評述道:“在風靡于整個清代‘祧唐禰宋’詩學主潮中,在當時須大聲疾呼、縱橫議論、鋪張描述的維新世運下,所謂‘舊風格’只能是‘禰宋’風貌。如果說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是通過今文經學向變法改良的‘西學’接榫過渡,那么在詩學上便是通過‘禰宋’詩學向‘詩界革命’‘移花接木’。”[10]
所以“禰宋”的宋詩運動成為詩界主流,又成為“詩界革命”“同光體”的實際崇尚方向。與此同時,碑學也以其雄強的風格成為書壇主流。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于是此學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11]此記述碑學興起的原因以及盛況。
更深層次,康有為則舉碑學與帖學審美上的不同:“即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帖學終致“淺弱”,碑學筆法“雄奇”,所以康有為極力推崇碑學,其理論被認為是碑學的總結。對此,侯開嘉先生評贊道:“清代碑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自覺的藝術階段。”[12]這種自覺也體現在眾多書家對這種雄強風格的一致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詩學中,原本主流的“祧唐”被視為宋詩運動的對立;書學上,原本主流的帖學也被視為碑學的對立。藝術發展過程中,一種風格過盛,必然導致其走向另外一面,如“尚法”的唐代出現狂草的高峰。從鴉片戰爭到甲午中日戰爭,沉醉于泱泱上國的士大夫終于驚醒,不管是以今文經學變法圖強,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都是想要重振國勢,這種心態成為清末士大夫的不懈追求。宋詩運動與碑學,以其容易抒發“泄其縱橫馳驟之氣”和展現“雄奇角出”的氣勢,成為士大夫一致贊成的文學藝術取法方向。
而兩者到清末民初皆有新發展,如康有為提出“漢唐格律周人意,悱惻雄奇亦可思”;“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意境幾于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13]。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作《飲冰室詩話》,倡導“詩界維新”,此則從宋詩派過渡到更為廣闊的取法天地之風了。而碑學方面,隨著金石學研究范圍的擴大和發展,碑學取法更為廣闊。璽印、錢幣、磚文、瓦當、甲骨文、漢晉簡牘以及敦煌文書等等都成為后來碑學的取法對象了。
結語
清代宋詩運動與碑學在一開始只是文藝上一個可輕可重的取法風尚,至清代末期形成兩大風靡全國的文藝流派。它們在到達頂峰時,詩學與書學藝術理念和追求相同或相近,因而相互影響,形成了宋詩運動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碑學家,而碑學家亦往往成了宋詩運動的中堅人物。宋詩運動與碑學,合力形成了清代末期追求雄強的文藝思潮。如今宋詩運動隨著時代變化已經煙消云散,碑學仍是書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藝繁榮的今天,我們已經能找到比宋詩更能直接宣泄縱橫才氣的藝術形式。碑學,站在帖學追求“二王”神態為宗的對立面,以開放的理念,敢取古代各種形態文字作為藝術表現形式,為書法藝術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
注釋:
[1]胡適:《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二卷,亞東圖書館1928年版,第144頁。
[2]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四》(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頁。
[3]鄔國平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明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頁。
[4]康有為:《書鏡》,楊素芳等編《中國書法理論經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頁。
[5]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頁。
[6]包世臣:《藝舟雙楫》,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頁。
[7]黃霖:《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頁。
[8]程恩澤:《程侍郎遺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頁。
[9]陳伯海:《歷代唐詩論評選》,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74頁。
[10]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頁。
[11]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0年版,第755頁。
[12]侯開嘉:《中國書法史新論》(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頁。
[13]桑咸之、閻潤魚譯注《康有為詩文選譯》,巴蜀書社1997年版,第99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