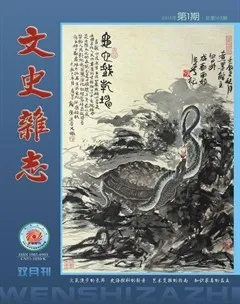從趙烈文的知識脈絡看其對于清朝滅亡的預言
蔡昭宇
摘 要: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了同治年間自己與曾國藩的對話,并預言了清朝五十年內將亡。多數史料僅僅將其作為一個奇異之事來記載。從趙烈文的日記史料中可見,做出該預言背后的思路,其實是對當時局勢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歷史大勢的把握,同時雜糅了民間佛教信仰以及民間術數的影子。由此可見以趙烈文為代表的一批中下層士人的思想取向,包括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對傳統史學的了解,同時兼容佛教信仰與民間術數。這種知識結構并不局限于傳統的儒學,具有較強的實用精神。這使得他們在面對西學的時候,可以更為務實地進行學習和吸納。
關鍵詞:晚清;曾國藩;趙烈文
一、“殆不出五十年”——趙烈文的歷史預言
趙烈文(1832—1894)被學者們提及最多的也是最廣為人知的事情,莫過于他與曾國藩談論清王朝的命運時,發出“殆不出五十年”的預言。該預言在有關曾國藩幕府的史料及研究中常被提及,但論者多將其作為驚奇之語,而少有考究其何出此言。事實上,趙烈文日記中所展現的知識脈絡與結構,使得此語言成為可能并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
在當時所謂“同治中興”的氛圍中,有這種看法的并不多見。趙烈文在曾國藩幕府中雖然職位不高,但深得曾國藩的信任和賞識。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準確地預見清王朝崩潰的第一人。趙烈文對此的分析如下:
初鼓后,滌師來暢譚,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變異,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軸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
余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師云:本朝君德比較正,或不至此。
余言: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1]
這段發生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8月7日)的對話當時并未傳出。44年后,在辛亥革命的沖擊下清帝退位,未能再偏安續命;接下來的是民國初期在北洋軍閥左右下長達十多年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的軍閥混戰,甚至在蔣介石名義上統一全國之后,各地依然山頭林立,抗拒中央。這么看來,趙烈文對于清朝崩潰的形式和時間,以及中央政權垮臺之后的全國形勢的預判,是較為準確的。
朱東安在《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序文中就以后人的角度論述了這一歷史進程:
如果說,曾國藩集團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墻腳的話,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背叛,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如果說,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國藩軍制改革之花的話,那么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就是其累累碩果了。由此可見,曾國藩集團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不僅數十年間暗中操縱著晚清政局,且開民國年間軍閥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2]
二、“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
——趙烈文的政治洞見
如果承認曾國藩集團對后世歷史進程的重要影響,那么趙烈文的預言無疑是在晚清督撫專權的形勢下,對自身所處的曾國藩集團的清醒前瞻與深刻洞察。
趙烈文初入幕府,并未對時局戰略發表太多意見,那時他主要是辦理夷務奏折。但隨著趙烈文一步步提升,尤其是他調入曾國荃幕府并委以重任后,逐漸接觸到當時東南政局最核心、最前沿的奏報咨復,且曾國藩、曾國荃大營與中央朝廷及四方督撫的來往信件,不少都經他之手修改潤色。這些常人難以接觸到的核心時政信息,使趙烈文逐漸對晚清政局的發展和趨勢有了一個清晰洞察。這些認識在后來同治六年(1867年)左右,同曾國藩在兩江總督衙署的每日閑談里,集中記錄下來了。
如,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867年8月10日)曾國藩與趙氏談到湘軍發展十多年的艱難歷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過來的:
起義之初,群疑眾滂,以至仇隙,甚有撻逐者,四年以后,在江西數載,人人以為詬病;在鄱湖時,足下目睹,迨后退守省垣,尤為叢鏑所射,八年起復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閩,毫不能自主,到九年與鄂合軍,胡詠芝事事相護,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誠令人念之不忘。[3]
曾國藩坦言:“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4]曾氏說自己靠自強不息之道“粗能有成”。曾國藩所說的自強之道,即是“權力在手”,為了事權歸一,將原本分屬的財權、人事權、地方政權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正是這樣,致使清朝軍制發生變革,政治結構逐漸位移,造成滿洲貴族在把持朝廷的同時,漢人督撫獨大一方,成為地方實力派這樣內輕外重的格局。這如同安史之亂后,唐朝借助各節度使的力量平定叛亂,節度使卻乘勢坐大,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趙烈文對此獨有精辟之論:“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5]此處“世俗文法”指的是中央為了統御臣下、制衡地方權力,而歷來推行的地方分權、制衡與檢視的政策,以及同僚猜忌、嫉功掣肘的官場習性。一方面,曾國藩為了達到對付太平天國的目的,需要主動突破這些限制地方督撫權力的政治限制;另一方面,清廷在新的形勢,不得不改變以往的做法,授予地方督撫更大的權力。于是在軍制、幕府與地方權力方面,這才有了一個制度性的突破。
而趙烈文看到了咸同年間這場動亂的本質,以及由此產生的制度突破所帶來的影響,于是說了下面這番話:
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6]
由于對太平天國的勝利而產生的督撫專權的情況,乃是曾氏所極不愿見到的“內輕外重”的局面。這一點,曾國藩自然是意識到了的。他曾在奏稿中表達了對“內輕外重”格局的擔憂。但形勢不由人,湘淮集團在內輕外重這條路上越走越遠,王闿運后來在《湘軍志》中寫道:
其后湘軍日強,巡撫亦日發舒,體日益尊。至庭見提鎮易置兩司,兵餉皆自專。湘軍則南至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潮、汀,乃渡海開臺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遂度烏孫,水屬長江五千里,擊柝聞于海。[7]
總之,趙烈文因為能夠接觸到當時東南官場的核心層面,從而加深了他對時政敏銳的洞察。趙烈文視野廣闊,不但對于經世致用的學術比較在行,而且對于水利、鹽務方面的議論亦屢受時人稱贊。他對史學尤為留心,曾下大工夫閱讀“二十四史”,并留下許多獨到見解。
毋庸多言,趙烈文正是具有了深厚的歷史文化素養與敏銳的政治觀察力,才會在清王朝貌似強大的背景下,作出那樣一個推論。
三、“以夢為真,真復為夢”
——趙烈文的佛教信仰
趙烈文的推論,并不全是基于歷史形勢而言,其中尚有佛家業因果報的思想在起作用。曾國藩說:“本朝君德比較正,或不至此。”趙烈文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8]
在曾國藩看來清朝君王德行尚中正,未必如此快地就滅亡。趙烈文則從佛家的角度認為,君德正是因,而清朝國勢昌盛這個食報是果,此果報已經很豐厚了;但是清朝建立之初,創業太容易,殺戮也太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了后面的果報。再說在佛教的因果中,善惡是不能相互抵消的,君德正這樣的善,也無法抵消殺戮太過這樣的惡;所以滅亡這個結果,在開創之初就已經種下了,后面君王的德行影響也無法改變。
趙烈文的思想受佛學影響很大,他不愛為官,一心求退,可能也與此有關。他時常會有人生如夢幻泡影的感受:
譬如夢然,問之于地,地不言,問之于吾,吾亦自迷。其真幻欲于妄想顛倒之外,求一證據,了不可得。……南無愣嚴佛偈有之曰:“磨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善體斯言,斯鮮夢矣。塵勞多著,書此自雪。[9]
曾國藩在其官宦生涯的后半期,常常得到趙烈文以佛學的道理來勸解,令其寬心。曾晚年關心佛學,趙烈文的影響恐怕至為關鍵。
趙烈文的佛教信仰,不但滲透到他的思想中,并且左右著他的生活。每年的初一,趙烈文都會“晨起執香,拜天、拜先圣孔子、拜十方如來、拜祖先父母。次詣寓庵殿上,禮謝佛神。”這個歲首將神佛與天地君親師、孔子一起祭拜的習慣,持續終身。
趙烈文的佛教信仰最早可能來源于母親,其母方怡在世時就茹素禮佛。趙烈文的四姊、六姊以及夫人南陽君也都茹素禮佛,可以說整個家族都有佛教信仰。[10]甚至在趙烈文的好友中,有不少也有佛教信仰。
總之,趙烈文深受佛教思想影響,同時也身處一個佛教信仰濃郁的家庭和交際網中。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始終以傳統儒學作為他的立身根本。
四、“卜以決疑”
——趙烈文的傳統術數
為什么在預言中,趙烈文不多不少剛好說出一個五十年的期限呢?這個可能跟趙烈文有中國傳統術數的知識背景有關。他在解釋這個期限的時候,除了歷史的洞見,更多是使用“氣數”“大勢”之類的術數用語。
術數門類眾多,趙烈文主要關注易學一類比較正統的著作。對于民間各種術數的流派,趙烈文既有批駁也有關注,在日記中也多所提及。比如,趙烈文曾讀《丙丁龜鑒》一書,對作者限定丙子、丁未這兩個年份多國禍的言論頗為質疑,于是又從當時的幾次戰事比如金田起義的時間推斷,認為“丙丁之年多禍起”這個結論是靠得住的。在趙烈文初到安慶的時候,記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4日)的五星連珠,認為是中興之兆。[11]
趙烈文最常使用的術數門類是六爻,一般會在大年初一早上,敬占一卦,看當年運勢如何。除此之外,趙烈文使用六爻占卜多集中在逃難的兩年。咸豐十年(1860年),浙江失陷,趙烈文在戰亂中多次占卜,內容包括占家屬安否,占祖墳安否、占兄長下落、占出行吉兇等等。迷信的人在危急迷茫的時候,特別容易依賴術數預測之類的手段。趙烈文在四月二十四日逃難路上,曾一日四占,都是占逃難路途、占朋友安危等難以把控的事情。
但趙烈文顯然不是一些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神算子的形象。在他留下的大概60多條六爻記錄中,有一些并不準確。咸豐十年(1860年)占木瀆以及常州城安危,趙烈文認為應該不會有事,但不久兩處都相繼遭受兵燹。
趙烈文并無術數類著作留下來,也不以算卦為生,甚至在他的日記中,都很少應別人之請而使用六爻的記載。可能術數對于趙烈文來說只是個人私下的愛好,他甚至都不愿讓身邊的人知道此事。
這類占卜的行為,在趙三四十歲以后,在日記中就很少出現了。其每年歲首卜課的舊例,也在48歲那年終止。他晚年認為:“循理而行,何卜之有,故已之。”[12]
五、結語
綜上所述,趙烈文在同治年間做出的清朝滅亡及其之后形勢的預言,其實是建立在他對當時局勢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歷史大勢的把握上;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預言雜糅了民間佛教信仰以及民間術數的內容。當然,我們亦可以從中窺見到趙烈文的知識結構的面貌。作為一位晚清士人,處于社會政治文化的深刻變革時期,趙烈文顯現出傳統中下層士人的一個面相:對于現實政治的關注、對于傳統儒家史學的了解,同時兼容佛教信仰與民間術數。這種知識結構并不局限于傳統的儒學。這種雜糅的知識結構與較強的實用精神,使得以趙烈文為代表的一批中下層士人在面對西學的時候,能夠更為務實地進行學習和吸納。
注釋:
[1][3][4][5][6][8][9][10][11][1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1068頁,第1072頁,第1072頁,第1072頁,第1072頁,第1068頁,第390頁,第626頁,第350頁,第1906頁。
[2]朱東安:《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7]王闿運:《湘軍志》,收入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湘軍專著綜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作者:復旦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