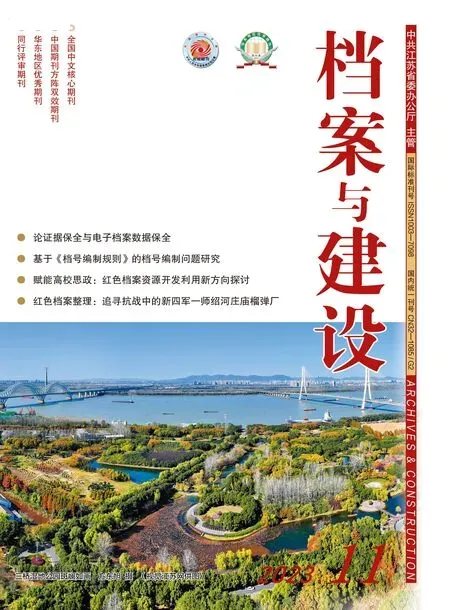明代醫(yī)家王肯堂生平述論*
王 亮 楊 帆 閔 文 陳 理 魏文霞
(1.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江蘇南京, 210029; 2.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第一臨床醫(yī)學(xué)院,江蘇南京, 210023)
王肯堂,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生,字宇泰,號損庵,又號念西居士,明代南直隸金壇(今江蘇金壇)人,是我國晚明一位重要的醫(yī)學(xué)家,先后著成《婦科準(zhǔn)繩》《幼科準(zhǔn)繩》《瘍科準(zhǔn)繩》流傳于世。而在西學(xué)東漸之先驅(qū)利瑪竇的口中,他除了是一位名醫(yī),還是“北京翰林院里一位杰出的哲學(xué)家”[1],其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經(jīng)歷,在悠遠(yuǎn)的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
一、因孝立志,名譽(yù)鄉(xiāng)里
王肯堂祖上三代為官。他的祖父王臬,在明武宗時期官至兵部主事,性格剛直,清正廉潔,因見武宗生活荒淫、政務(wù)廢弛、國庫漸虛,便上述諫言,結(jié)果冒犯天顏,被杖責(zé)后貶為山東副使,未能得到復(fù)用。其父王樵,字明遠(yuǎn),于明嘉靖年間舉為進(jìn)士,滿腹經(jīng)綸、恬澹誠懇、詩書傳家,堪稱一代名士,還著有《尚書別記》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品,但因?qū)掖蔚米锛槌紘?yán)嵩而被謫放山東。后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所重用,任浙江僉事,大力推行當(dāng)時的改革政策,在浙江沿海兢兢業(yè)業(yè),整肅宗社,帶兵抗倭,改善了浙江民眾的賦稅情況,口碑頗佳,累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后獲太子少保銜。[2]
出生在這樣一個官宦詩書之家,王肯堂受書香門第的家風(fēng)影響,少年起便刻苦攻讀文史經(jīng)典,把拼搏仕途留取功名作為主要目標(biāo),所以從醫(yī)并不是王肯堂最初的“職業(yè)規(guī)劃”。在他17歲那年,其母身患重病,家中長輩遍請名醫(yī)診治卻無法切中要害,在焦急和不滿之下,王肯堂認(rèn)為,如果自己精通醫(yī)道,不把家人交給水平低劣的醫(yī)生,就不會出現(xiàn)此種情況。出于對家人的孝德,王肯堂立志研究醫(yī)學(xué)。他發(fā)憤攻讀名醫(yī)典籍,遍訪求教各地名醫(yī)大家,利用有限的條件積極開展臨床治療實(shí)踐,逐漸成了當(dāng)?shù)孛癖姺Q贊的鄉(xiāng)醫(yī)。有一次,王肯堂的妹妹患病不起,找了很多醫(yī)生沒有療效,生命垂危,他通過自身的醫(yī)術(shù)把妹妹治好。這件事讓他名聲大噪,周邊縣鄉(xiāng)的百姓慕其醫(yī)術(shù)高超,紛紛前來求醫(yī),一時門庭若市。他對于疑難雜癥從不婉言推卻,而是耐心思考分析癥結(jié),花費(fèi)大量時間和精力梳理治病機(jī)理,而良好的療效讓他更加醉心于醫(yī)學(xué)。
二、為官剛正,不忘醫(yī)心
王肯堂在醫(yī)學(xué)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引起了父親王樵極力反對,要求他專注科舉,經(jīng)營仕途,繼承家族為官傳統(tǒng),光耀門楣,嚴(yán)禁他學(xué)醫(yī)。王肯堂只得又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科舉上,得益于扎實(shí)的學(xué)識基礎(chǔ)和聰穎才智,他于30 歲中舉人,40 歲中進(jìn)士,從此步入宦門,成為明廷史官。[3]
中國的明代,實(shí)為多事之秋。1592 年,在“關(guān)白”(即丞相)豐臣秀吉的鼓動下,日本大舉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并迅速占領(lǐng)了大半個朝鮮。這一舉動,更深層次的意圖是要入侵地域遼闊、物產(chǎn)富饒的中國,豐臣秀吉甚至公開言稱出兵朝鮮,實(shí)為假道朝鮮,超越山海,最終則要入侵中國。明廷也認(rèn)識到“關(guān)白之圖朝鮮,意實(shí)在中國”[4]。此時的王肯堂與其父一樣,是一名率直諫言的忠耿之士,在對待日本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的事情上,在朝堂上與大多數(shù)文官一起表達(dá)了援朝抗倭的態(tài)度。受父親事跡的激勵,他還專門上疏,提出了針砭時弊、極力抗倭的十條建議,并積極請求赴一線領(lǐng)兵。他對當(dāng)時武備廢弛、海防空虛、朝政弊病的批評,措辭懇切,但他的批評被朝廷視為浮躁言論,不予采納,他逐漸被疏遠(yuǎn)。王肯堂不忍此種狀況,在入朝僅三年后便托病回鄉(xiāng),史書記載“察降調(diào),家居久之”[5]。
史館的同仁對王肯堂的離開十分不忍,因?yàn)樵谒麨楣俚亩潭倘昀铮环矫嫠牟沙霰姡苏\懇熱情,展現(xiàn)出名臣子弟的深厚底蘊(yùn),在廷閣享有不錯的口碑。另一方面,他在朝廷事務(wù)之余,還為同僚、上司治療病痛,從不計(jì)較得失,用不凡的醫(yī)術(shù)贏得了館內(nèi)同仁的高度認(rèn)可,幾乎成為大家的保健醫(yī)生。例如有一史官名韓敬堂,久患膈痛病,一般的醫(yī)生都治不好,甚至經(jīng)醫(yī)生治療后,反而膈痛更甚。王肯堂給他仔細(xì)診斷了一番,確診其病之根在虛,若太疲勞且不及時進(jìn)食,必然發(fā)病。為此他主張用“千全大補(bǔ)湯”等劑攻其虛,并讓其注意調(diào)節(jié),韓敬堂的膈痛病慢慢痊愈。
三、潛心研醫(yī),復(fù)官盡責(zé)
在得罪權(quán)臣托病回鄉(xiāng)后,王肯堂迎來了自己徜徉醫(yī)道的黃金時光。他如饑似渴地遍覽醫(yī)書,探索醫(yī)學(xué)奧秘,同時積極匯總研究成果、著書立說。1598年,完成了《證治準(zhǔn)繩》的撰寫,6 年后又寫就《傷寒準(zhǔn)繩》[6],這兩部醫(yī)書是王肯堂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證治準(zhǔn)繩》在明代的眾多醫(yī)書中,以“列證最詳、論治最精”而著稱,被《四庫全書》評價(jià)為“醫(yī)家圭臬”,并以“世稱肯堂好讀書,尤精于醫(yī),所著《證治準(zhǔn)繩》,該(賅)博精詳,世競傳之”[7]予以盛贊。例如,在《證治準(zhǔn)繩·雜病》中“視白如赤癥,謂視物卻非本色也”“或觀太陽若冰輪,或睹燈火反粉色,或視粉墻如紅如碧,或看黃紙似藍(lán)等”[8],這些對于不同色盲患者癥狀的記載,是世界醫(yī)學(xué)史上關(guān)于色盲癥最早的文字描述,早于西方近200 年。
歸鄉(xiāng)后的王肯堂少了許多朝廷差事,有更多的時間治病救人,理論的研究與實(shí)踐的嘗試相結(jié)合,使他的醫(yī)術(shù)更加高明。他從未將功名利祿凌駕于自己從醫(yī)初心之上,鄉(xiāng)鄰慕名前來治病,不僅不收窮苦病家分文,對于疑難雜癥也從不婉言推卻。當(dāng)時的松江名士康孟修,年老體弱,一次持續(xù)發(fā)寒熱,多日幾不進(jìn)食,生命危在旦夕,請著有《本草經(jīng)疏》的名醫(yī)繆希雍診治[9],也未見好轉(zhuǎn)。繆希雍因曾在金壇住過多年,素知王肯堂醫(yī)術(shù)精湛,便邀他相助。他一面細(xì)細(xì)詢問康之病況,一面研究繆之處方。不久,康孟修之病漸告痊愈。
在王肯堂托病辭官后的第十四年(1606 年)[10],當(dāng)時的吏部侍郎楊時喬出于對他的敬佩和欣賞,極力邀請他復(fù)出為官。在楊時喬的大力舉薦下,心懷報(bào)國情懷的王肯堂沒有推卻,復(fù)入仕途,任南京行人司副之職。任上他兢兢業(yè)業(yè),后因政績突出被提拔為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11],與他的祖父、父親一樣,成為造福一方、有口皆碑的一代良臣。仕途的順利,沒有耽誤他對醫(yī)學(xué)的研究,在任上他又完成了《婦科準(zhǔn)繩》《幼科準(zhǔn)繩》《瘍科準(zhǔn)繩》等醫(yī)書,完善了自己的中醫(yī)理論體系。此外,王肯堂還編寫了一系列醫(yī)學(xué)叢書,編有《 醫(yī)統(tǒng)正脈全書》44 種,以及《醫(yī)論》3 卷、《醫(yī)辨》1 卷等,收錄范圍很廣,展現(xiàn)了他深厚的醫(yī)學(xué)功底,對研究我國醫(yī)學(xué)史也有很高的價(jià)值。
四、情趣高雅,博識多通
王肯堂作為一名從明代官宦家庭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為官和從醫(yī)是其人生的關(guān)鍵詞,但他也在日常生活中對書法、經(jīng)學(xué)、科技等方面都有著很深的研究,是一位有著豐富精神世界和高雅志趣的名士。
在書法方面,王肯堂因天資出眾、聰穎好學(xué),加之在皆為登科進(jìn)士的祖父、父親熏陶引導(dǎo)下,自幼便刻苦練習(xí)書法,認(rèn)真研習(xí)碑刻。在其撰寫的雜記《郁岡齋筆塵》中,記錄了大量他對于書法的認(rèn)識和見解。例如,他提出真正的楷書就必須是筆筆依照楷法書寫,認(rèn)為鐘繇、王羲之、王獻(xiàn)之、歐陽詢、顏真卿等七家作品方為純正楷書,其他各家只能算作正書,并以此作為練習(xí)書法最基本的要求。[12]在京為官期間,供職于翰林院的王肯堂與都城精英人士過往密切,在他留下的雜記中,與當(dāng)時著名的收藏家韓世能、書畫家董其昌等名士交游的趣聞軼事記錄甚多[13],這些經(jīng)歷也讓他本就出眾的書法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特別是在萬歷十九年(1591),他在京城匯集魏晉唐宋名人書法作品,并增入《真賞齋帖》火后本,親手勾拓了《郁岡齋帖》10 卷,還邀請名刻手鐫石,成為當(dāng)時珍貴的精刻叢帖[14]。王肯堂與書畫友人經(jīng)常研討前人作品的精妙之處,遇到愛不釋手的還會親手題跋,他曾為《黃庭經(jīng)》《十七帖》《鴨頭丸帖》等名作題跋,其中為王珣《伯遠(yuǎn)帖》的題跋,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被乾隆皇帝欽點(diǎn),御刻至《三希堂法帖》[15],足見當(dāng)世對其書法水平的高度認(rèn)可。
此外,王肯堂在經(jīng)學(xué)上也有很高造詣,著有《尚書要旨》20 卷、《論語義府》20 卷和《成唯識論證義》10 卷等,在歷史上也為各家品評,雖褒貶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經(jīng)學(xué)界是一位很有個性且敢于創(chuàng)新的獨(dú)立學(xué)者。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99 年到達(dá)南京后,在南京除了會見當(dāng)?shù)毓賳T外,還廣交當(dāng)?shù)孛浚蹩咸檬撬煌^多的一位名醫(yī)。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數(shù)次提到王肯堂,講述相互討論的內(nèi)容,涉及中外文化、天文、地理、數(shù)學(xué)、哲學(xué)、宗教等多個領(lǐng)域。從他們之間廣博而深入的交流,足以看出王肯堂在多個領(lǐng)域均有所建樹。他甚至對文房四寶之一的硯臺,也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硯品理論,并提出過“作書使鈍硯,如娶妻得石女,將按用之”[16]的鮮明觀點(diǎn)。
不幸的是,這樣一位終生筆耕不輟、知識淵博、一專多通的博學(xué)家,在其仕途和醫(yī)學(xué)研究尚未達(dá)至極限的時候,罹患重病,在福建任上告老還鄉(xiāng),次年(1613年)[17]回到故鄉(xiāng)金壇不久后,便因病辭世,享年64歲。
五、結(jié)語
王肯堂的一生,既是他在從醫(yī)路上孜孜不怠,終成一代儒醫(yī)的勵志佳話,也是他在醫(yī)界、宦門輾轉(zhuǎn)前行,思想認(rèn)識和人生境界不斷提升的蛻變史。他在不同人生階段和學(xué)習(xí)研究領(lǐng)域所體現(xiàn)出的勤勉、高潔之品質(zhì),同樣也是留給后人的寶貴財(cái)富。近些年,隨著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各個領(lǐng)域都受到了一些不良思潮和風(fēng)氣的侵蝕,醫(yī)療機(jī)構(gòu)也不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行業(yè)不良競爭、就醫(yī)矛盾腐敗等對傳統(tǒng)醫(yī)德觀念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沖擊,出現(xiàn)了醫(yī)者職業(yè)信仰缺失、職業(yè)操守失當(dāng)、服務(wù)意識淡薄、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wù)的醫(yī)者初心動搖等問題。[18]同樣作為一名醫(yī)者,王肯堂對于醫(yī)品醫(yī)德的追求孜孜不倦,始終如一。他強(qiáng)調(diào)習(xí)醫(yī)的目的是濟(jì)世救人,而非為了一己私利,其《證治準(zhǔn)繩》作為一部醫(yī)學(xué)書籍,還專列了“醫(yī)家五戒”“醫(yī)家十要”作為重要內(nèi)容,他強(qiáng)調(diào)的“欲濟(jì)世而習(xí)醫(yī)則是,欲謀利而習(xí)醫(yī)則非。我若有疾,望醫(yī)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孫小有疾,望醫(yī)之相救者何如?易地而觀,則利心自淡矣。利心淡,仁心現(xiàn)。仁心現(xiàn),斯畏心生”[19]便是給后世留下的諄諄肺腑,既為從醫(yī)者制定了行醫(yī)守則,更是勉勵從醫(yī)者要真正以崇尚醫(yī)德為習(xí)醫(yī)行醫(yī)的最終目標(biāo)。這些論述在中國醫(yī)療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也為當(dāng)今醫(yī)者如何堅(jiān)守“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xiàn),大愛無疆”的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深刻啟示。作為一名官宦家庭培養(yǎng)、握有權(quán)力的官員,王肯堂不貪圖功名利祿,精忠朝堂耿直諫言,一生遵從修身治國的遠(yuǎn)大理想抱負(fù),始終能夠秉公諫言用權(quán);在平時生活中也是“慎獨(dú)”“慎微”,培養(yǎng)健康而富于志趣的愛好和興趣,不因貶謫而郁郁沉抑,更不因權(quán)勢的誘惑和官場的腐朽而拋棄初心、貪名逐利、人格墮落。作為明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王肯堂向世人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一部分精英群體獨(dú)立、清醒、雅致的生活方式,而他以其豐富的精神素養(yǎng)和人文情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古人埋頭八股、鉆營功名的陳舊認(rèn)知,也是當(dāng)代治學(xué)為官為醫(yī)者學(xué)習(xí)的榜樣。
縱覽王肯堂的一生,他最精通也最傾心于醫(yī)學(xué),在經(jīng)學(xué)、書法、哲學(xué)等方面也有著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官也是錚錚忠臣、惠濟(jì)黎民,是明朝一位不同凡響的名士,為各行各業(yè)的知識分子在如何修身養(yǎng)性、堅(jiān)守良好的職業(yè)操守,進(jìn)而在生活工作中提升境界、做出成績,提供了很好的啟發(fā)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