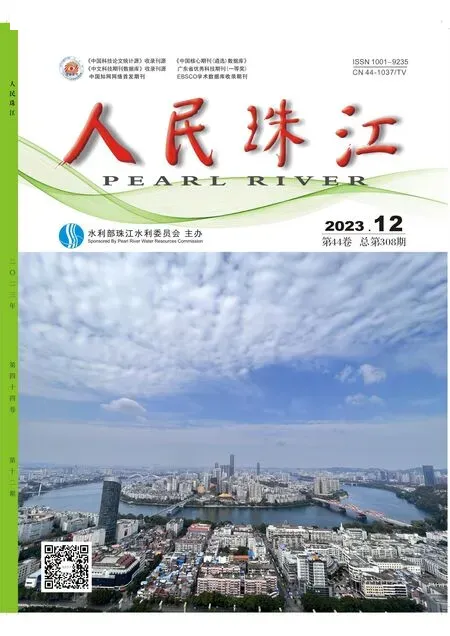東江流域1980—2020年森林時空演變特征及水源林改造潛力分析
戴妙琳,陸曉琪,臧傳富*,朱 可,邱欣彤,羅洢雯,張衛強,甘先華
(1.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2.廣東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520;3.廣東省森林培育與保護利用重點實驗室,廣東 廣州 510520)
土地資源是地球生物生存的環境基礎,是人類可支配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與社會經濟開發和自然環境相關[1-4],對可持續發展、生態安全等一系列核心問題有著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在土地利用的變化特征、空間分布格局[5]和原因分析[6-8]及其對氣候[6,9-11]、流域環境[12]、水文過程[13]等方面的影響都做過探索[14]。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中國土地結構顯著改變,許多地區的森林資源遭到嚴重損失[13-17],由之引起的生態安全問題也日趨嚴重。因此,加強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將會對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有力的理論參考。
位于中國南部亞熱帶和熱帶地區的東江流域,光、熱資源充足,雨量充沛,是植被極易繁衍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東江流域自1980年以來受到人類活動的強烈影響,土地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目前國內對于東江流域土地利用的研究多集中在研究時空變化[17],且多將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系統相聯系[18-20],但對于研究地研究時間跨度不夠大。此外,將東江流域森林資源置于探討重點的研究不多,張宏鋒等[21]應用InVEST模型評估了東江流域森林水源涵養功能的空間分布,Li等[22]基于過程和關系的方法研究東江流域徑流變化和森林變化之間的關系。同時,目前國內外對于森林林地質量高低劃分的研究不多,Burger等[23]以土壤指標為例,評估了集約化管理森林的站級可持續性;董希斌等[24]對低質林林分的評價及分類,低質林生態系統的評價與恢復、誘導改造和立體化管理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前人的研究雖從不同角度對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進行了分析,但聚焦于某一典型生態系統類型,圍繞該生態系統的土地覆蓋變化及其與社會經濟之間的驅動機制開展的進一步探討研究仍然較少,無法很好地為流域的生態環境綜合管理提供理論支持。同時,自從廣東啟動四大生態建設工程以來,全省對于森林資源的重視程度逐漸增強。目前對于東江流域高低質水源林的研究較少,該研究有利于當地的森林資源保護,并將對其流域的生態效益產生巨大的影響。
因此,近40 a來土地利用特別是森林資源上究竟有哪些差異特征?土地利用變化受哪些因素影響?東江流域造林潛力還有多大?未來還有多少水源林適合改造?基于這些問題,本研究聚焦森林資源,通過遙感和GIS技術,從東江流域1980、1990、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及社會經濟數據入手,對東江流域近40 a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機制進行了對比和分析,建立東江流域森林潛在分布評估體系,評估東江流域水源林未來改造潛力,以期為東江流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優化和流域造林規劃的改善提供理論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東江流域(東經113°25′50.32″~115 °52′36.16″,北緯22°23′31.93″~25 °12′35.28 ″)位于珠三角東北部,南臨南海和香港,西南與廣州、深圳等華南經濟核心及廣東北部韶關、清遠接壤,東部是廣東東部的梅山(圖1)。在廣東省內涉及梅州、惠州、韶關、東莞、河源、廣州、深圳等城市,在江西省內涉及贛州市。2020年,東江流域總人口達到3 908.28萬,地區生產總值在1980—2020年從341.112億元增長到234 916.477億元,經濟增長快速。東江流域總面積為35 340 km2,地勢東北高西南低,高程最高為1 423 m,年降水量在1 000~ 2 300 mm,年平均氣溫在20~22 ℃。流域內林地面積為23 634 km2,占流域面積的67%。

圖1 東江流域區位示意
1.2 數據來源
使用的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分辨率為30 m。從和諧世界土壤數據庫( Harmonized World Soil Database)中獲取1∶100萬分辨率的土壤數據。1980—2020年氣溫、降水等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分辨率為1 km。東江流域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來源于1980—2020年各省地市級統計年鑒。
1.3 數據預處理
本文所用的是地級城市的社會經濟統計資料,為了確保其科學性,采取了區域權重法,計算流域內面積所占其地級市面積與流域各個地級市面積之比,以此作為面積加權參數,按面積比重計算得出流域尺度的社會經濟統計數據[25-26]。
1.4 建立水源林可改造潛力評估指標體系
依據Hua等[27]對人工林和天然林在地表碳的存儲、涵養水源、木材產出等生態系統服務和生物多樣性上的效果比較,參考張丹妮等[28-29]對三北防護林宜林性分析所使用的指標體系,發現不論人工林還是天然林,如從單個指標評價,如森林蓄積量、固碳量、木材產量,或者從綜合指標評價,比如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等,喬木林的各項指標都優于灌木林和疏林地[27]。因此,假定喬木林是最優的森林生態系統,參照喬木林的分布條件,對東江流域森林資源進行系統評估。依據適宜的條件來建立評估指標體系,使用極限條件方法劃分指標,用1為可改造區域賦值,用0為非可改造區域賦值,劃分出滿足喬木林生長條件的區域,建立水源林可改造潛力評估體系。
1.4.1土壤類型評估指標
不同土壤對喬木林生長條件影響不同[30-32],本研究根據喬木的生長條件,將不同土壤類型分為可造林土壤和不可造林土壤。在世界土壤數據庫(HWSD)分類系統中,薄層土土壤深度為300 mm,而喬木的根系分布深度為1 000 mm以上,不適合造林。鹽脅迫對部分林木生長有抑制作用[33],造林效益低,故劃分為不可造林土壤。土壤類型評估指標見表1。

表1 土壤類型評估指標
1.4.2土地利用類型評估指標
表2所示,灌木林、疏林和其他林地內林木不飽和,可對其進行改造,劃分為可造林用地。而有林地內種植密度較高,將其劃分為不可造林用地。河渠、水庫坑塘、湖泊等水體,由于內部的造林活動對樹種限制較大,故被歸類為不可造林區域。城鄉、工礦、居民用地為人類生活用地,改造受限,故將其劃分為不可造林用地。

表2 土地利用類型評估指標
1.4.3干燥指數評價指標
采用De Martonne提出的由溫度和降水計算的De Martonne干燥度(IDW)計算方法[33-34],使用年均溫和年均降水量為指標進行計算。10 ℃為喬木(喜溫作物)適宜生長的最低溫度,高于這個閾值溫度的累計溫度,是衡量喬木所需熱量資源的重要指標,見式(3):
(3)
式中I——干燥指數;P——平均年降水量,mm;t——年平均溫度,℃。
干燥度數值在10以下為嚴重干旱;在10~30范圍內屬中度干旱,適宜的植被類型為草原類型;數值高于30的屬于濕潤地區,適宜的植被類型為森林類型[33]。將干燥度30作為分級指標,干燥度高于30賦值為1,干燥度低于30賦值為0。
1.4.4海拔評估指標
參考張丹妮等[28-29]指標設置(海拔高度特征基本相似),設置3 000 m為海拔分界線,3 000 m以下賦值為1,3 000 m以上賦值為0。
1.4.5坡度評估指標
參考張丹妮等[28-29]將造林活動的坡度上限設置為40°,坡度小40°的區域賦值為1,大于40°的區域賦值為0。
1.5 土地利用驅動機制分析方法
1.5.1指標選取
LUCC(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驅動力系統可分為自然和人文兩大驅動力系統[34]。在短期內,自然驅動力較穩定,具有一定累積作用。因此,前人對驅動力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文驅動力的角度[35]。本研究以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數據為基礎,定義了6類驅動因子:人口數量及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及結構、基礎產業發展、財政水平、生態和氣候。針對以上6類因子選取22個社會經濟和自然指標(表3)對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進行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表3 土地利用驅動機制因子指標
1.5.2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將多個相互關聯的因素轉換為若干獨立的綜合指數的分析和統計方法,其在研究區域土地利用變動的動態機制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35]。主要步驟如下:①對各土地利用類型和相關性較強的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了特征值、特征值貢獻率和載荷矩陣,其中累積貢獻率大于85.00%的設為主成分;②對各個主成分進行綜合評價(圖2)。

圖2 主成分分析流程
2 結果與分析
2.1 東江流域森林時空演變特征
2.1.1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分類下森林的演變特征
根據東江流域1980、1990、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結果(圖3)可以得出東江流域森林變化具有以下特征:①1980—2020年林地面積持續減少且減少量明顯僅次于耕地減少量,為998.81 km2;②1980—2020年東江流域林地減少土地中有林地最多,流失的林地主要轉化為城鎮用地。

圖3 1980—2020年各Ⅱ級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面積
2.1.21980—2020年的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矩陣
東江流域在1980—2020年土地利用轉移特征見圖4。可以明顯看出,土地利用變化多集中在流域北部贛州市和南部東莞市、深圳市和廣州市,土地利用變化顯著;北部以林地-耕地方式轉變為主,南部以林地、耕地、水域向城鎮用地的變化為主,城鎮用地面積急劇增加。由圖4可知,1980—2020年東江流域林地的變化以林地-城鎮用地及林地-耕地的轉化為主。其中,1980—1990年,流域林地的面積變化較明顯,南部林地到城鄉、工礦、居民用地的變化較顯著,流域北部存在小部分林地轉變為耕地的情況;1990—2000年流域林地變化較之前10 a較不顯著;2000—2010年,林地-城鎮用地的變化量較前10 a有所增長,主要發生在流域南部東莞市、深圳市及惠州市南部;2010—2020年流域北部贛州市大量林地轉化為耕地,變化較顯著。

FL—林地;GL—草地;CL—耕地;W—水域;RL—城鎮、工礦、居民用地;UL—未利用土地。圖4 東江流域1980—2020年各土地利用類型轉化
2.2 東江流域1980—2020年森林演變的驅動機制
將1980、1990、2000、2010、2020年的各項因子(表3)與流域內不同的林地類型面積分別進行數據標準化后,兩者做皮爾遜相關性分析處理,得到東江流域內的林地類型面積比重與因子相關系數矩陣(因篇幅有限本文未列出)。選取相關系數矩陣中r≥0.8的對應變量,運用SPSS軟件實現主成分分析,其中主成分提取采用最小特征大于1法,并且采用主成分旋轉最大方差法確定數量。經SPSS計算,得到東江流域林地類型的特征值及主成分貢獻率(表4)。由表4可知,在每一種林地類型中,主成分1、2、3的累計貢獻率超過99%,即說明主成分1、2、3對于闡述林地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解釋能力超過了99%,滿足主成分提取要求。主成分對數據變異的解釋程度可由主成分特征值表現,若特征值小于1,其解釋程度小于單一變量,需要剔除。由表4可看出,在土地類型為有林地的3個主成分中,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為1.026,大于1;第三主成分的特征值為0.384,小于1,即應該保留前兩位的主成分,剔除剩余部分,所以有林地土地類型用于因子分析的主成分為第一和第二主成分。依照此類推,可得林地類型土地因子載荷矩陣(表5)。

表4 東江流域林地類型的特征值及主成分貢獻率
有林地面積變化的第一主成分變量影響因素中,人口數量及結構因子影響占比最高,達0.991;GDP、第二產業產值其次,影響占比0.981;第二主成分中人均糧食產量影響占比最大。灌木林面積變化的主成分變量主要由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第二產業產值決定,影響占比分別為0.995、0.993、0.989。疏林地面積變化影響因素中人均耕種面積和人均糧食產量與之呈正相關關系,而人均GDP、第一產業產值、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解釋程度呈負相關關系。影響其他林地面積變化的因素中,地區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影響占比達0.998、0.997,相關程度較高,其次為第二產業產值,影響占比0.993。
2.3 東江流域未來低質水源林改造的潛力分析
2.3.1單因子評估結果
在氣溫和降水數據中可發現,東江流域年降水量均大于800 mm,年均氣溫均大于15 ℃,氣候濕潤溫暖,適合林木生長。干燥度計算結果均大于30,可以判斷該研究因子非影響東江流域是否可造林的制約因素。東江流域海拔最高為1 432 m,均小于3 000 m,故海拔非影響東江流域是否可造林的制約因素。東江地形坡度變化在0~57°,40°以上坡度面積極小,可忽略不計。根據圖5a,東江流域土壤可造林區域較大,且較為均勻覆蓋整個流域,非可造林區域中,除水體外,薄層土面積為72.955 km2,鹽堿土面積為54.075 km2,不可造林區域較小。從行政區劃角度看,薄層土集中在東莞市和河源市西部,鹽堿土分布于廣州市河流周圍及惠州市中部;從整體來看,薄層土多分布在東江流域南部及中部西側,鹽堿土多分布在東江流域南部。綜上所述,從土壤類型單因子評估分析,東江流域造林體系具有較為優良的條件。由圖5b可以看出,東江流域土地利用類型分布較為規律,整個東江流域有林地面積占比最大,有林地大面積覆蓋,南部多為城鎮用地及其他建設用地覆蓋。水田較為零散分布于流域中部,在城鎮用地周圍較多。水源林中可改造的低質林區域多集中在流域東北部及流域腹部。

圖5 水源林改造潛力評估結果
2.3.2綜合評估結果
由各因子疊加分析得到的綜合評價結果可得圖5c,東江流域總面積35 340 km2,可改造區域面積5 365 km2,不可改造區域面積29 908 km2,可改造區域面積占總流域面積1/7。東江流域低質水源林區域較為均勻分布在流域內,多集中在流域東北部及流域東南部,西部地區可改造水源林區域分布較少且分散。在行政區劃尺度多分布在贛州市及惠州市,惠州市可改造水源林多分布在東南部,且較為顯著地沿東江支流呈帶狀分布。河源市南北部可改造區域分布差異較大,南部較少。廣州、深圳和東莞三市可改造水源林區域較為分散且面積較小。水庫附近多分布高質林,可改造水源林區域多分布在東江干流或支流附近。并且,在城鎮用地分布較多的東江流域南部,即廣州、深圳和東莞三市,仍有可改造水源林分布,有一定的發展潛力。
3 討論
研究表明,東江流域近年間土地利用變化顯著。結合各省市統計年鑒可知,1980—2020年東江流域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土地利用類型也因此發生劇烈變化。研究期內,大面積林地、耕地轉移為城鎮用地,城鎮用地和其他建設用地擴張明顯,與任斐鵬等[17]對于1990—2010年的研究結果一致。其中離不開的是人口變化、地區生產總值提高以及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增長等帶來的社會效益,這說明了與東江流域同期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契合,反映出生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性。研究發現,社會經濟生產和人口數量變化為主要推進東江流域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進程的因素,該結果回答了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受哪些因素影響的問題。社會經濟因素對林地土地利用類型變化影響最大的是有林地和其他林地,灌木林和疏林地位列其次。而疏林地面積變化還與人均耕地面積等指標掛鉤,反映出林地、耕地與城鎮用地的轉化矛盾。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數量增加,作為東江流域土地利用占比最大類型——林地,雖減少面積較大,但動態變化度小至0.1%,對于林地的體量來說變化較小,反映出東江流域生態建設在林業發展上有一定側重,對林業發展規劃較為重視。南部多為城鎮用地及其他建設用地覆蓋,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吻合;水田較為零散分布于流域中部,在城鎮用地周圍較多,便于糧食生產供應。
研究中,東江流域可改造水源林多集中在流域東北部及流域東南部,與土地利用類型評估結果高度一致,說明在可改造水源評估體系中,土地利用類型評估區分度較高。結合東江流域土地利用類型來看,在流域東南部地區分布較多的可改造水源林的類型為旱地,且沿河流分布,滿足造林所需條件(濕度、水源等),故此處改造潛力巨大,結合該處惠州市經濟活動分布,其地理位置較優,周圍城市用地覆蓋較多,可猜測其未成林原因是人類活動,反映出生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性。流域東北部贛州市分布較多的可改造水源林,其土地利用類型為疏林地,林木種植密度稀疏,改造潛力巨大,但不可盲目增加林木種植密度,還需結合水資源承載力及土壤承載力進行評估,探索林水土協調的林木種植模式。目前,贛州市林業實行“多措并舉”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更優的營造林技術[35],本研究回答了東江流域未來造林潛力有多大、在哪些地區的問題,以期為林業規劃、造林技術的改進提供理論參考,創造出更大的生態效益。
國內學者對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研究不少[30-35],但研究時間跨度較小。在東江流域水源林可改造潛力方向上國內外研究較少,且多針對西北、東北等區域[31],對南方區域研究較少,故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此方面研究的缺失。
未來東江流域的森林演變和水源林改造研究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和深化:①在研究東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機制時僅完成因子載荷矩陣分析,因篇幅所限未將主成分綜合得分納入研究考慮范圍;②在進行水源林改造分析中依據喬木林特性簡單將喬木林定義為高質林,雖然依據的文獻是國際頂級權威期刊發表的結果,但研究的系統性方面仍有待深化。但目前對大尺度的研究方面,本文有其創新性和可取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對優質林與低質林的評估體系重新構建,結合實地情況實地考察,將各項指標重新細化,可采取各指標加權,以期在該體系的權威性和水源林改造潛力評估的嚴謹性上更進一步,使其能更好服務于土地造林規劃與生態管理。
4 結論
通過對1980—2020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特征及驅動機制以及東江流域水源林改造潛力進行分析與評價,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a)1980—2020年東江流域總體動態變化度為5.85%,變化幅度較大。林地持續減少,其中灌木林變化動態度最高,達到0.26%。
b)1980—2020年東江流域土地利用類型變化多集中于流域南部和東北部。林地/耕地/水域-城鎮用地轉移多集中于流域南部,與經濟發展特征相契合。
c)在研究土地利用的驅動機制中發現,人口數量、人均耕地面積、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總/人均GDP、第二、三產業產值、工、農、林業總產值、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固定資產投資額、財政收支等指標對4種林地變化的影響程度較大,即促進東江流域內4種林地類型發生變化的驅動力是社會經濟和工業高速發展與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d)在東江水源林改造評估體系中土地利用類型因子影響最大,其次為土壤類型因子,干燥度、海拔、坡度因子影響較小。東江流域未來可改造林區域面積5 365 km2,可改造區域多集中于流域北部(贛州市)及流域東南部,改造潛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