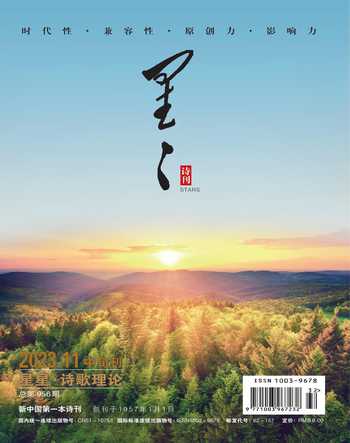第七屆“戀戀西塘”全球詩歌大賽獲獎作品述評
馬迎春
綜觀本屆獲獎作品,我認為有效地傳遞出西塘的文化底蘊,非常好地體現了地理詩歌的特點與成色:
第一,詩人們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著力挖掘西塘人文歷史底蘊,讓詩歌文本具有歷史厚重感。如馮金彥的組章《西塘散記》獲本次大賽一等獎,就著力挖掘西塘深厚的歷史文化,在現實與歷史的時空中穿行,賦予了西塘歷史以可感的藝術形式,對西塘人文歷史及文化內涵進行了詩意呈現。馮金彥在《尊聞堂》開篇寫道:“門前石階上,兩個老人在下棋。風吹動,斑駁的發在風中飛。楚河與漢界,一面是歷史,一面是現實。”由下棋展開藝術聯想,由現實引出了歷史,就像他在《銀杏樹》一詩中寫道的“銀杏的厚重,不是木散發出的味道,是靈魂的淡香。像鳥鳴一樣,很輕,我們卻抱不動。/西塘,有太多的東西,我們抱不動”。
溫勇智的組詩《西塘寫意,抑或五個側面描述》中,“像是誰在撫摸和斑駁這生活的庸常/梁架、梁墊、撐拱、雀替、格窗,都蓄滿了西塘的蕙質蘭心/……/放棄葉子和花瓣,隱于一塊木根的內心/你就會感受到,‘只有以劇疼的方式,靈魂才能植入顫抖的身體”。詩人對木雕的詩意表達從微觀入手,發掘木雕蘊含的文化內涵和人生體驗,尤其最末一句更是從木雕成型過程中發掘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孟甲龍的組詩《天下西塘》中,“令我懷舊的,是西塘超現實的水/……/曾刺痛春秋時期的船夫/……/重返初唐,盛世的鎮還很年輕,妃子吃荔枝/……/烏臺詩案,王安石變法/……//來摸一摸古鎮,替大宋領受后世的作祟/寄身客船,十萬兩黃金贖回春天/謝幕的唐宋在復活”。作品以“春秋的水”開篇,依次經過唐、宋、明、清,直到現代。詩人以現實為基點,俯身歲月長河之中,經過深度詩意開掘,詩歌文本因承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歲月的滄桑而厚重。詩人冰島在紐扣博物館里找到了詩意生發點,從中發掘歷史文化的閃光處,并與現實人生經驗聯系起來,“平靜地接受西塘人小小紐扣中不眠的濤聲/一顆紐扣便是一個人或一個物種的一生”。
第二,以詩歌文本書寫西塘“地理志”,建構西塘印象。詩人們描寫西塘的石皮弄、五福橋、萬安橋、環秀橋、廊棚、塘東街酒吧、木雕館、紐扣博物館、祥符蕩家園、醉園、西園、倪宅、低碳稻、智慧田、陸墳銀杏、烏篷船等具有鮮明西塘印記的事物或地點,逐漸勾畫出一個完整而特色鮮明的西塘。雖然分開來看由于每位詩人的人生閱歷、生命體驗和審美偏好不一樣,詩意的生發和最終呈現也都不一樣,但綜括起來從宏觀層面看,這些詩歌如同拼盤,共同書寫了一部西塘“地理志”,建構并凸顯了西塘印象。
從文旅融合旅游推介的角度講,這種由詩歌文本建構起的西塘印象應該說達到了詩歌大賽的目的。黃世海是這樣寫來鳳橋的,“水的脈動,在來鳳橋下悄然靜謐下來/陽光與水的觸須達成一致/鳥鳴中盛開的紅菱,掛滿西塘”,動靜結合,光色并呈,有聽覺描寫也有視覺描寫,再現了來鳳橋的美。向武華這樣寫雨中過萬安橋的所見所聞,“雨水在飛揚,鳥鳴在滴答/三月已有人穿著雨衣緩行/石竹悄悄地開出小花朵”。王超以廊棚作為詩意構造的基點,敏銳的藝術觸覺和深刻的人生體驗賦予了廊棚濃厚的歷史感和內在意蘊,渲染出動人意境,“在人世起伏的劇情中,一次次/捕捉到煙雨蒙蒙,或一卷/紙上搖曳的水墨,暈染平生”。熊鋒筆下的石皮弄則是純粹主觀化的一條巷弄,“狹窄,是巷弄的/一再提醒//你輕易地踏入了一條巷子/你便放棄了所有后路。//你只能向前”。熊峰將自身的生命積淀和審美體悟賦予石皮弄,具有漫長歷史和滄桑記憶的石皮弄就和現代經驗匯合,不僅呈現出鮮明的在場感,而且飽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第三,詩人們熱衷抒寫“水”這一意象,賦予其濃厚的象征含義。他們從各自的藝術經驗出發去接近西塘的“水”,寫出了風格各異、內蘊豐富和具有極強審美價值的詩篇,賦予了西塘的水以動人的詩意內涵。
陳茂慧的散文詩直接以《水境》為題,描繪了天水同輝、人水相依的動人畫面,并將水人格化和象征化,“西塘的水,是從春秋時期沿著光陰流過來的水”,是歷史,是現實,也是人或人生的寫照。薛菲的《西塘,或水的紙上書》中,“水是其中無法忽略的血脈”,這是血脈之水、歷史之水、生活之水、生命之水、古典之水和現代之水,或清麗婉轉,或洶涌澎湃,薛菲將自身的審美經驗和藝術思考融于西塘之水,呈現出鮮活的西塘詩意。黃睿的《水墨西塘》中,“花追著花開,水逐著水流/這不就是散金碎銀的水墨和一甩千年的水袖嗎?”突出了水的綿長歷史和重要地位。周啟垠的《西塘:藏著能被心靈打開的密碼》中,“一村的水,在暮色里越來越透明/一抬眼,就看見水底/——浙江的天空,嘉善的天空/西塘的天空,種滿神秘種子”,更是以水來呈現西塘的歷史、人文和地理。
第四,重視語言運用,大力發掘語言的詩性功能。雖然這次是所謂的征文體詩歌,但詩人們大多具有深厚的情感積淀和良好的藝術修養,從自身的審美經驗和生活感悟出發,在語言的詩意化上做功夫,創造出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作品。
蔡秀花的《行吟西塘》中,“一道千里廊棚,是西塘古鎮的對稱軸/隔開了山水詩里白墻墨頂/舟影波光,放大石皮弄里的吟哦/水聲滴答,寥落的星辰交出最后的一絲溫度”。詩人在抒寫西塘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人文內涵的同時,在語言的運用上注意節奏、韻律和畫面感,加上具有創意的語言運用及操控能力,裹挾著一股江南水鄉的氣息撲面而來,而那“‘吳越文化/走過一個又一個朝代,在平淡無奇中/演繹著離奇曲折的釋義/……/每一縷煙霧,都是沉默的/被激活的流水,以詩的名義在大地行走”,既寫出了歷史厚重感,用語還考究,語言本身就給人一種強烈的詩意感受。
其他詩人也都十分重視語言的詩意挖掘,呈現出風格特異的語言景觀。例如:無非的《在西塘的一滴水里修行》中,“月光輕扣瓦當,月光織藍印花布/月光把樹下花瓣,一遍遍掃凈/一把鑰匙打開巷弄的盤扣”;趙妮妮的《西塘慢》中,“水墨肖像,如落葉更迭/而流水,依然是根根碧玉簪/恍惚千年,還沒走出斜塘云鬢”;李萬峰的《西塘之思——彌補未來的事物》中,“云彩內有琴聲/傳自常去井邊打撈波紋的母親/……/汽車停于窗格外、糧食外/關于糖畫的主張隨風起舞/口銜冰塊的同學/迅速認識了平原”;高璐的《在西塘,采擷煙雨江南的背影》中,“撐舟的竹篙/一半在水里,一半在人間/他和漁火無話不談/茶盞戴上斗笠/一遍遍在水墨閬苑拓印自己”。這些作品或比喻,或擬人,或詞語超常組合,詩人們用生花妙筆在語言上下功夫,奉獻出了極具審美價值的詩歌文本,給人強烈的審美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