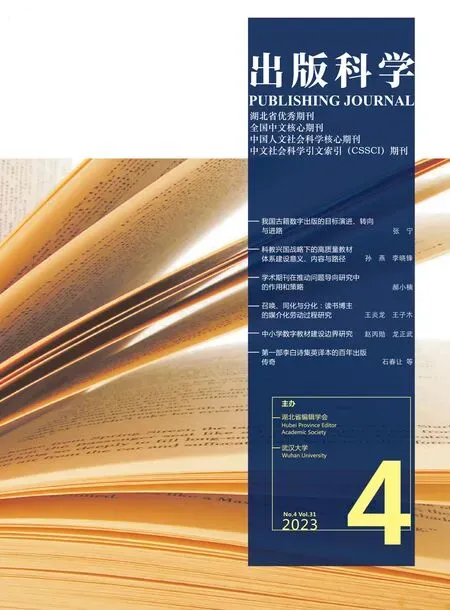中國古農書傳播對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多維影響研究
莫鵬燕 李 潔
(鄭州師范學院傳播學院,鄭州,450053)(鄭州師范學院文學院,鄭州,450053)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重農抑商”的小農經濟不斷孕育出農耕文明的智慧結晶。相對先進的農耕文明通過對外貿易及外交活動,除輸出至中國西部貿易線上的阿拉伯、印度等地區,更是東傳至當今日本、韓國、朝鮮等鄰近國家。不論是農作物、農具的使用與普及,還是《氾勝之書》《齊民要術》《陳旉農書》等可考農書書目的傳入,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東亞國家的農業文明、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甚至政治變革。日本史學家藤間生大曾言:“日本民族從未開化的世界,進入到原子能時代,其間必須經過數千年的歲月,以及許多重要的發展。作為這種發展的第一步,是從中國輸入水稻開始。”顯而易見,中國農業成果的傳入,對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的社會發展舉足輕重。本文大致以中國古農書東傳概況、東傳影響及日韓農史學家對中國古農書的研究三方面為切入點,淺談中國古農書在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動態傳播概況。
1 中國古農書的對外傳播
中國古農書東傳是“親仁善鄰”式的文化東渡,是東亞文化圈內自然的農學輻射。
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依黃河、長江兩水發育,農業文明起步較早。戰國以降,鐵犁牛耕的普及更是極大地提升了社會生產力,有助于小農經濟的迅速成長。在“重農抑商”的社會大環境下,在迅猛成長的農業實踐中,一批批農學家展露鋒芒,擔任起理論總結的工作。自可考的戰國《神農》《野老》始[1],西漢氾勝之有《氾勝之書》、東漢崔寔成《四民月令》、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唐朝李石作《司牧安驥集》……朝代更迭,歷史變遷,長期穩定的小農經濟社會的農書出版未曾間斷。
中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引入著沿途國家的農作物品種和種植方式,也在東亞文化圈內充分發揮輻射作用,輸出自己的農業技術、農業成果和農耕文明。隋唐—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期,我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地的交流愈加頻繁。《行走的作物:絲綢之路中外農業交流研究》一文中寫道:“中國古農書通過絲綢之路傳播至世界各國, 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2]尤其是造紙術、印刷術的應用和普及,使外來學者向本國輸入中國古農書的載體由個人手抄本升級至官方刊印本,加快了中國古農書“走出去”的步伐。各朝代的中國古農書持續漂洋過海,被東亞文化圈內的日韓等地區廣泛研習,并在其本土扎根成長。以日本為例,漢代《氾勝之書》傳入后,與其本土農業實踐相結合,迅速衍生出具有其本土特色的農書如崗島秀夫、志田容子的《氾勝之書:中國最古の農書》;崔寔《四民月令》則有渡部武《漢時的歲時與農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在日傳播可考藤原佐世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唐李石《司牧安驥集》入日后指導成書平仲國的《仲國秘傳集》及橋本道派的《假名安驥集》,同時代陸羽《茶經》則是榮西《吃茶養生記》的依托;宋樓璹《耕織圖》是日本《四季辨作圖》的前身,《陳旉農書》則為天野元之助《陳旉農書和水稻技術的開展》的藍本;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可考在17 世紀末、18 世紀初傳入日本,同時代日本還有借鑒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農業全書》,參考喻氏兄弟《元亨療馬集》的《馬經大全》。
中國古農書在東亞土地上的傳播是因地制宜的,東亞各國家地區對中國古農書的學習是持續漸進的。中國古農書東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所載農作物種培技術及禽畜養殖方法等的實用性,而因農作物及禽畜物種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條件的約束限制,故日韓等地對中國古農書的學習引入,就呈現出因地制宜的特點。首先,日韓國家國土面積及旱地資源有限,故其引入學習多為米稻等合適的高產農作物;其次,日韓等國區別于中國的氣候特征—海洋性顯著,決定著其引入學習的物種類型;最后,作為彼此長期交流互通的友邦,中華文化的魅力也決定著日韓等國學習的深入性與持久性。
以日本為例,就其引入的部分代表性書目,可看出學習的持續性和因地制宜性。以時間為線索,縱觀其引入中國古農書,從被稱作“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農業科學著作”[3]的《氾勝之書》,到被譽為“中國17 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天工開物》,貫通漢、唐、宋、元、明五代,易看出其學習的不間斷性。再考其所習古農書的適用地域及內容概況:漢代講黃河中游地區耕作原則、作物栽培技術和種子選育等農業生產知識的《氾勝之書》,記洛陽地區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發展狀況的《四民月令》;北魏載黃河中下游地區農牧業生產經驗、食品加工貯藏、野生植物利用及治荒方法的《齊民要術》;唐代適用于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東、黔中、江南、嶺南等地,講茶葉生長規律、品質優劣、加工烹煮、茶具制作等知識的《茶經》;南宋總結南方地區水田農事、養牛、桑蠶良方的《陳旉農書》;明載錄許多江南濕潤地帶農政措施和農業技術的《農政全書》……多吸收中原地區黃河流域及以南地區的農耕文明成果,而對西北內陸亦或東北地域的農業成果收錄難覓只言片字,可發現日韓農史學家對于生物地域適應性的考慮。
從中國古農書的傳播背景到其入外壤的傳播特點,這中間的傳播途徑是實踐與理論并舉,主動與被動共存的。實踐與理論并舉有兩層含義。一為實踐主導下的間接傳播:日韓使者來華,親身投入中國古農書指導下的農業生產實踐,充分感悟中國古農書中相關知識,在切實掌握技術后,返鄉二次總結普及。比較有代表性的屬榮西與其所撰《吃茶養生記》:榮西作為來華修習佛法的日本僧侶,鉆研佛法之余潛心研究中國的茶葉種植及飲茶之道,最終回國著成《吃茶養生記》[4];二為理論發力下的直接傳播:中國古農書通過海上通道,直接被東渡華人或日韓回國使者引入,逐漸影響當地農業活動。如以手抄本形式在日本流傳的《齊民要術》,有寫于文永十一年 (1274 年)的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本,還有據北宋本過錄的金澤文庫本 (缺第三卷)—現存最早抄本[5]。這些書刊在很長一段時期的傳播中,深深影響其農事活動。
主動與被動共存亦分為二說。筆者在此視日韓為接收主體,將“被動”釋為中國官方貿易或私人東渡時對古農書的輸出,而“主動”則為日韓使者對中國古農書的直接或間接引入。比如世人熟知的“鑒真東渡”,即日本對中國相關文化的“被動”接收,在此過程中鑒真為日本帶去了眾多書籍,其中不乏與農事相關書目,日本《本草醫談》所載木本藥草種植知識,就與鑒真對《鑒上人秘方》的傳播息息相關。“主動”則不可不談朝鮮半島地區,其對陸羽《茶經》精神—“儉”和“全真”的學習與本土化發展極具代表性。李崇仁、李行以及鄭夢周等人不僅學習種茶制茶,更研究其中延展開來的茶文化,直至熱愛茶道的大詩人李奎報時代,當今韓國的茶文化在那時漸成體系,發展至巔峰[6]。
2 中國古農書對日韓等東亞國家的影響
中國古農書東傳,從微觀處百姓的農業生活,到宏觀上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它的影響是由點及面、多層漸進的。在農業方面增物種,拓領域;對文化陶染由表及里,潛移默化;就經濟來說發展小農經濟,催進商品經濟;而以上生產力進步又律動著政治變革的必然性—社會變革。
就本土農業生活來說,隨古農書一同入駐的生物豐富了物種,拓展著農業領域。以高麗為例,《世宗實錄》載:“傳旨戶曹,各道移蕎麥耕種,考《農桑輯要》《四時纂要》及本國經驗之方,趁時勤耕”[7]這說明其蕎麥種植領域出現之源為中國。另有高麗毅宗13 年(1159)所譯北宋《孫氏蠶書》,向本土介紹普及了養蠶技術,開拓了桑蠶養殖領域。
對文化領域,從表層的圖書編撰到深層的社會文化,再到更高一度的農耕文明,中國古農書在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影響是“層林盡染”式的。
第一,影響著類似圖書的編撰風格方式。最顯著的屬被日本譽為“人世間一日不可或缺之書”的《農業全書》,在編撰風格上,《農業全書》習《農政全書》的總論—分論的結構,效《農政全書》的“農本思想”,在首卷就點明闡述了農事的重要性;從編撰方式來看,中國《農政全書》采改前代所著而加作者評注闡釋所成,日本《農業全書》則遴選徐書章節并附己所釋而作。窺斑見豹,對比兩書目錄便可形象品悟:作者宮崎安貞大膽學習我國《農政全書》的體系和格局著成此書,可以說是對《農政全書》的本土化。
第二,促使其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展。《茶經》與《碧巖錄》東傳日本,其文化中從此多了“茶道”;《元亨療馬集》指導下《馬經大全》的出現,見證著日本育馬文化的成長;《農政全書》除對日本農業有指導性意義外,更促進了其國本草領域的學術研究工作,松崗玄達就在對此書“荒政”思想的研究下,于享保元年(1712)將書中的《野菜譜》《救荒本草》加“訓點”并詳注后刊行,1799 年,日本著名本草學家小野蘭山又進一步刊行《正救荒本草、救荒譜》[8]。
第三,形成了類似于中國長期穩定的農耕文明。日本學術界普遍認為,日本稻作農業系中國傳入。稻米種植傳入日韓之前,其社會長期滯于漁獵采集時代。而水稻和中國古農書漂洋過海,使這些民族擁有了種植產物和日趨進步的生產技術,應運促進其社會文明的進步。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中表示,比絲綢之路意義更重要,“稻米之路”是百姓之路,是人類大眾生存繁衍的生命之路。這生動展露著中國稻米文化對日本社會的深刻影響。
在經濟方面,中國古農書的傳播促進著傳入地生產力進步,帶動了手工業發展,使小農經濟活躍升級,也環環相扣地催進商品經濟。
《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等書目在日本的廣泛傳播,促使日本出現了像貝原益軒、宮崎安貞、佐藤信淵這些杰出的本土農學家,他們立足本國農業實際,對從中國傳入的古農書或加以翻譯總結、或作解讀延伸,對本國的農業技術革新發揮著舉足輕重的推動效應,增加了土地單位面積內產出,極大地提升了農業生產力[9]。以輸入中國古農書為基礎,日韓等國將書中理論深入應用到生產實踐中,不僅漸形成本國的種植業、養殖業,還在這些日趨成熟的基礎農業系統上發展出相關手工業,如上文提到的種茶烹茶、養蠶繅絲等。牽一發而動全身,生產力進步推動手工業衍生,小農經濟的繁榮又悄然孕育著商品經濟。長期較為穩定的小農經濟社會在江戶時代幾近繁榮頂峰,和平的社會環境、繁榮的農業經濟,此時人們手中的生產資料富足甚至盈余,再加上身份統制令[10]的催化,商品經濟自然發育成長。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變革是生產力進步下政治進步的必然表征。日本學習中國谷物種植初期,先是由繩紋時代進入農耕社會。《〈農政全書〉在近世日本的影響和傳播:中日農書的比較研究》一文還指出:“《農政全書》直接或間接地對日本近世農書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日本當時得到了廣泛地普及和傳播, 并對推動當時整個日本農業技術發展、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也是促成日本當時展開‘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運動的一個遠因。”[11]對于當時深受中國古農書影響的朝鮮半島地區來說,亦如此理。
3 日韓農學家對中國古農書的研究
日韓農學家對中國古農書的研究聚焦于農書記載的農業概況及適用范圍、成書體例及載錄方式、中國古農書的本土化發展及本國農書的改進創新三方面,是秉持著因己制宜、創新發展的原則進行的。其研究大方向從未偏離因地制宜:他們研習中國古農書所載農業概況,又從中篩選適合本土自然及人文國情的部分引入。
韓國釜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崔德卿曾寫道:“高麗后期曾兩次再版(1349 年、1372 年;后者是慶南陜川本)元朝(1264 年)的《農桑輯要》,并且從中只挑選符合韓國現實的內容,之后又在14 世紀中期發行了《農書輯要》。”[12]日本亦如此,考慮到本國氣候與土地資源限制,對中國古農書中水稻種植部分的學習便更濃墨重彩。如天野元之助的《陳旉農書與水稻技術之展開》與《火耕水耨之辯:中國古代江南稻作技術考》[13]。
《從幾部農書的傳承看中日兩國人民間悠久的文化技術交流(下)》一文中說:“宮崎安貞編著《農業全書》,在體系、格局方面,大都仿照《農政全書》。”[14]的確如此,通過中國《農政全書》和日本《農業全書》目錄比較,可以直觀感受日本對中國古農書成書體例及記載方式的模仿學習。語言風格上,兩書均節節平實凝練,字字懇切,既講農業技術,又強調農業重要性;內容布局上兩者都圖文兼具,相互詮釋;書目思想則都強調農本,唯一有區分的一小點是《農政全書》貫穿“以農為政”的線索,《農業全書》“貫徹”以農為業的觀點。類似的模仿學習在日本借鑒中國成書的農業著作中均有體現。
中國《齊民要術》序講,“今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于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榖之道。”而日本寬保四年(1744 年)榮堂本《齊民要術》的《新刻齊民要術序》寫道:“民家之業,求之要術,驗之行事,無不可者矣。”山田蘿谷還在此提出,譯注刊刻此書是“欲使本邦齊民有治生之要術,尚亦有利哉”。兩者對比,不難發現日本對中國農業著作語言風格之效仿和對重農為業、勸民務農思想的貫徹。再比較日本寶歷十三年(1763 年)平賀源內《物類品》與中國宋應星《天工開物》的軋蔗取漿圖等[15],也易觀察出日本對中國古農書內容布局方面的學習和精進。另載錄方式上,若為書目,農學家便以文字記錄的形式傳抄;若為圖畫,農學家們便孜孜不倦地兼職畫手,對其進行加工復刻,如以樓璹《耕織圖》為藍本的《四季辨作圖》。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適當地借鑒有利于取長補短,一味地模仿只能滑向悲劇的深淵。作為自古以來對中國優秀文化虔誠見習的日韓先進知識分子,他們同樣深知學習中國古農書的奧義。是故這些農史學家不只對中國古農書進行簡單的翻譯引入,更在傳播過程中將其加以優化升級,進行本土化地創新發展。
就朝鮮半島地區言,可考“茶”在陸羽《茶經》中稱“嘉木”[16],而在草衣的《東茶頌》中謂“嘉樹”[17],窺一斑而見全豹,這印證其對中國古代農書的學習借鑒。被譽為“茶學泰斗”的韓雄斌先生更是將陸羽《茶經》直接譯為朝鮮文。在這些基礎上,朝鮮半島地區對中國種茶、制茶以及禪道與茶道的融合學習,從而產生的總結手冊、禮儀典籍等,都可視為對種茶用茶的本土化衍生。
還有高麗對《農桑輯要》中元朝棉花種植的本土化適應。最初,高麗地區直接將《農桑輯要》直譯為本土俚語刊行學習,但隨著百姓將其適用到實踐中,不斷發現問題,李朝世宗王便要求三南各道訪問有實踐經驗的老農并撰寫勘察報告,命崔南善將這些報告匯集整理,于1429 年印出1000 冊頒發各地[18]。亦有李朝后期為解決大規模饑荒問題,徐有榘將《農政全書》相關內容結合當時朝鮮實際,編撰成書《種薯譜》指導實踐。
再如日本,中國北方旱地農業技術為中心的農書—《齊民要術》, 對日本濕地農業來說實際借鑒意義偏低,但為什么仍被國民傳承發展呢?其承襲的,便是適合當時日本社會的“農本”思想。觀日本“花道”,也是由中國佛教中關于花卉養殖及佛堂供花等書籍影響而萌芽成長的。拿早期中國流傳的《妙法蓮華經》來說,此書見證著花與佛的不解之緣,而日本也對諸如此類的經文積極學習引入,比較典型的有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他們將中國佛前供花的文化滲透到了本民族文化中去。《由“佛前供花”到日本花道》一文中就有如此分析:“……《仙傳抄》中有關‘唐樣花(中國插花)’的記錄,其中所記載的‘橋(階梯)之花事’‘柱花瓶之事’‘橫梁(梁柱)之花’等,與《清異錄》中所記錄的李后主在家中窗柱、階梯等地方,以壹、簡等插花裝飾基本類似,這正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將中國插花藝術傳播回國的結果。”[19]再到宋明后世,由于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影響,佛教中的花文化也蒸蒸日上,我國農業著作中更是出現了育花的專題,譬如宋人溫革所撰的《分門瑣碎錄》,詳細載錄了牡丹、芍藥、荷花、水仙等多種花卉養育之法。作為中國花文化的學習者,日本當然毫不落下,相近時期日本的書籍中也出現了花朵專題板塊,例如櫻田絢的《花譜》。諸如此比,皆為東亞各國農史學家結合本土特色對中國古農書的衍生發展。
中國統一的歷史相對較早,在長期中央集權制的穩定社會環境中,小農經濟成長壯大,農業文明長期繁榮。作為農耕生活智慧結晶的各代古農書經久不衰,被不斷東傳至日韓等東亞地區,被當地勞動人民傳誦借鑒,與其地農業實際融合發展。從華夏土壤到東洋島嶼,藕斷絲連的農事生產經驗,見證著中國古農書踏上的土地;從農業水稻種植到朝代政局革新,社會各維度以歷史車輪的前進,講述著自己在中國古農書影響下的升華;從漢代氾勝之的《氾勝之書》到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時代更迭中接續的傳播節奏,訴說著歷史長河里中國古農書的“川流不息”。中國古農書的傳播是寬領域、長時期的,它似一石激起千層浪,由點及面,多維立體地作用于當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