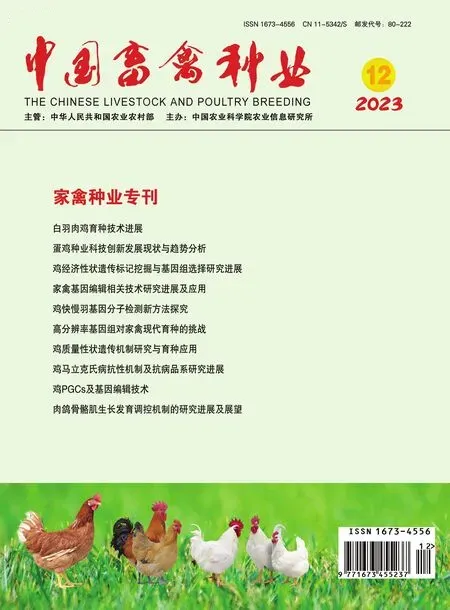白羽肉雞育種技術進展
安炳星,李政達,張 琪,王夢杰,朱雨晴,趙桂蘋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北京 100193)
1 國際白羽快大型肉雞發展情況
雞肉是世界第一大肉類生產和消費產品,全球雞肉產量約70%來自白羽肉雞。現代白羽肉雞脫離了標準品種名稱,以配套系形式存在,其主要父系來自白科尼什雞(White Cornish),母系來自白洛克雞(White Plymouth Rock)。目前,全球商品白羽肉雞生產使用的品種主要有AA+、ROSS、Cobb 和Hubbard 等少數品種,被德國EW 集團和美國Tyson 公司壟斷,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市場[1]。國際育種巨頭擁有成熟的金字塔式良種繁育體系(育種核心群—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代),掌控育種核心技術,育種綜合創新能力強,培育出了AA+、Ross 308、Cobb 500 等著名的肉雞配套系。
Ross 308 是由英國Ross 育種公司育成的四系配套肉雞,Ross 308 育種過程中綜合考慮肉雞活重、種雞產蛋量、飼料轉化率(Feed conversion rate,FCR)、骨骼強度等相關性狀,開展高強度選育以適應市場需要。如圖1 所示,Ross 308 父母代種雞2011 年與2021 年產蛋性能比較,43 周產蛋數年平均進展為0.14 枚/ 年(圖1d),63 周產蛋數年平均進展為0.29 枚/ 年(圖1f);2015年與2022 年生產性能比較顯示,42 日齡體重年平均進展為23.63g/ 年(圖1a),FCR 年平均進展為-0.020(圖1c)。

圖1 Ross 308 父母代種雞產蛋性能與生產性能變化
如圖2 所示,美國商品雞47 日齡體重年平均進展為29.9g/ 年(圖2a),FCR 年平均進展為-0.013/ 年(圖2b),受禽流感連續影響,全期成活率以每年0.14%逐年下降(圖2c)。

圖2 2011—2021 年美國商品肉雞生產性能
白羽肉雞是我國所有畜禽品種中FCR 最低、規模化養殖程度最高的品種,具有生長速度快、生產效率高等優勢,2022 年我國白羽肉雞出欄達61 億只,提供了全國63%的雞肉產品。但我國長期面臨白羽快大型肉雞祖代雞依賴進口的問題,為此農業農村部先后發布 《全國肉雞遺傳改良計劃(2014—2025)》[2]《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推動了肉雞種業快速發展。2021 年12 月,“圣澤901” “廣明2 號” “沃德188” 等3 個快大型白羽肉雞品種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我國白羽肉雞自主育種從此實現零的突破。隨著我國養殖技術、環控管理的成熟及籠養比例增多,白羽肉雞商品雞的生產性能與成活率提升較快,如圖3 商品雞2012—2022 年的生產性能數據顯示,42 日齡體重年平均進展為32.9g/ 年(圖3a),FCR 年平均進展為-0.034(圖3b),全 期成活率年平均提高0.44%(圖3c)。
2 育種技術進展
2.1 高通量、智能化新表型發展
在育種工作中,及時、準確地記錄種雞的各類表型數據,如生長發育、飼料轉化率、屠宰性能、骨骼強度等相關性狀,是選育取得預期進展的重要基礎[3]。目前基因組學數據對畜禽遺傳改良的貢獻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大量可靠的表型數據導致的,當前畜禽育種工作的重點也正在從基因分型轉移到高質量的表型分型[4],新表型及高通量自動化表型精準測定技術是未來品系選育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
2.1.1 生長發育相關表型精準鑒定
生長發育性狀是白羽肉雞最受關注的經濟性狀,傳統方法是逐只稱重,工作量大,且易造成雞只應激。近年來,射頻識別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云技術、人工智能、計算機視覺(Computer vision,CV)等技術不斷發展,研究人員得以開發出一系列采食行為圖像處理技術和自動稱重系統。Mortensen 等[5]、Dong 等[6]、沈明霞等[7]將圖像識別與支持向量回歸、貝葉斯人工神經網絡等機器學習算法相結合,使用3D 計算機視覺算法實現公母識別與體重預測,誤差降低到7.8%。另外,Ma 等[8]基于RFID 提出一種使用S 型稱重傳感器和無線傳輸模塊的低成本、高精度、高穩定性的稱重系統,其主要方法是肉雞在通過稱重托盤時逐只稱重,采集的數據通過無線傳輸模塊傳輸到遠程服務器,并將限幅濾波算法與反向傳播神經網絡結合應用于自動稱重設備中,可將誤差減小到6%。也有研究將RFID 電子翅號與自動稱重秤結合,通過RFID 實現種雞體重智能采集,并在育種和生產中進行應用時稱重準確性可達到100%,種雞稱重的效率和準確性得到極大提升[9]。
肉雞的飼料轉化率直接影響養殖成本和效益,而采食行為是判斷雞群健康狀態和生長狀況的重要指標,明確雞只采食量對了解雞群健康狀況及選育飼料轉化率等經濟性狀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肉雞采食量(料重比)主要測定方式為人工測定,耗時費力且效率低下。隨著自動化管理技術、RFID 技術及計算機設備等在畜牧領域的應用,出現了基于RFID 的雞只采食和體重記錄系 統[10]。陳君梅 等[11]利 用RFID射頻無源電子標簽的識別技術開發的雞個體采食量和體重自動測定系統,從群體中識別出每個個體的身份,并對每個個體的采食行為進行動態測定和記錄。也有研究基于音頻技術開發的肉雞采食量檢測方法,其原理是使用單分類支持向量機對雞采食時的有效聲音片段進行分類識別,經音頻技術檢測的肉雞啄食次數與采食量高度相關,決定系數為0.9825。啄食次數計算正確率為94.58%,采食量計算正確率達到91.37%[12,13]。
2.1.2 屠宰表型活體測定技術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屠宰加工性狀開始受到重視,如凈膛重、胸肉重、腿肉重等,傳統方法為屠宰個體后進行人工稱重,數據準確性受分割水平影響較大。近年來開始使用超聲診斷系統測量活體胴體重、胸肌重、胸肌厚、胸肌體積、皮下脂肪厚度等性狀[14,15],同時利用回歸模型和機器學習算法預測腹部脂肪含量和產肉量[16]。
另外,隨著白羽肉雞選育強度的不斷增加,木質肉、白條紋肉等新型劣質肉的發生率也逐年上升。木質肉即木質雞胸肉,特點為整體顏色蒼白、厚度增加并在尾部有明顯的脊狀隆起,觸感堅硬。白條紋肉則是肌肉表面出現平行于肌纖維的白色條紋。常用的檢測劣質肉方法有表觀評分法和壓縮力評分法,表觀評分法主要用于屠宰現場,測試人員根據胸肌觸感的堅硬程度和胸肌表面白色條紋的數目和寬度劃分肉的等級。壓縮力在正常肉和劣質肉組間差異顯著,且隨著病變嚴重程度而增加,因此可作為評估胸肌劣質肉發生程度的客觀和定量指標[17]。正常胸肌肌纖維排列緊密,而木質肉和白條紋肉的肌纖維組織學形態相似,表現為周圍結締組織增生、炎性細胞和脂肪滲入,圓形肌纖維數量增加,肌纖維發生變性、壞死溶解,并伴有肌纖維再生[18]。近年來也有研究通過組織學特征和生物標志物檢測劣質肉的方法。白露等[19]對木質肉等劣質肉的組織學變化給出了量化指標,中度木質肉組肌纖維面積、直徑和肌內膜厚度與正常肉相比分別增高約45%、20%和75%,可間接作為衡量木質肉發生程度的量化指標。孔富麗等[17]研究發現,白羽肉雞異質肉個體血清肌酸激酶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血清肌酸激酶可以作為預測活禽木質肉和輔助肉雞遺傳育種選擇的候選生物標志物。劣質肉的出現通常伴隨代謝異常,通過代謝組學方法分析,使用機器學習發現到通過檢測3-甲基組氨酸、N-乙酰基-L-天冬氨酸、甘油酸、N,N,N-三甲基-5-氨基戊酸、丙氨酸和O-磺基-L-酪氨酸,這6 種代謝物的含量就可預測木質肉,判斷活禽木質肉化的嚴重程度,準確率為94%[20]。高胸肌產量肉雞群體的胸肌厚會隨著木質肉發生嚴重程度而逐漸增加,但木質肉的胸肌長和胸肌寬顯著低于正常肉,所以胸肌的厚、長和寬的情況也可作為評定木質肉發生程度的標準[21]。
2.1.3 骨骼強度及福利性狀測定技術
現代家禽生產性狀受到巨大的選擇壓力,骨骼正常生長發育和穩態的平衡非常脆弱,當平衡被破壞時,會發生骨質量惡化、骨骼礦化過程不完全、骨代謝紊亂失衡等問題,進而引發腿病[22],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和動物福利問題。研究人員通常使用 “步態評分” 法判斷骨骼強度,將肉雞的運動能力作為腿部健康的標準,但該方法不考慮骨骼病理或骨骼異常情況,耗時且受到操作者主觀性。基于此種方法的缺陷,出現了利用計算機斷層掃描、核磁共振成像、超聲波、熱成像和X 光測定技術測定活體肉雞的內部骨骼強度、發育形態等性狀的新方法。
形態學評分通過檢測骨骼形態結構以判斷健康水平,比 “步態評分” 更客觀,Pulcini 等[23]基于形態學開發了一種采用標記和半標記混合模型檢測早期脛骨形態,發現體重增加與脛骨前后軸彎曲度呈正相關,脛骨形狀與主動行走行為顯著相關。Wilson 等[24]建立了一種結合固定、放射線照相和數據采集的數字X 射線方法,對肉雞骨骼質量進行檢測并量化骨密度。Salah 等[25]利用微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進行脛跗骨的宏觀、微觀結構和力學性能檢測,發現脛跗骨斷裂強度和生長速度呈正相關,骨體積分數隨年齡增長而降低,小梁數量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從而導致骨強度降低。鄭炬梅等[26]對廣明2 號白羽肉雞采用便攜式X 光機設備對肉雞腿部健康狀況進行精準評價,X 光片可判斷腿部骨骼的健康狀況和骨骼病變的各種類型,按照骨骼形變程度區分為健康、輕度患病和重度患病個體,以實現對活體肉雞腿部健康的精準評價。
目前,有研究開始關注骨骼發育相關的血清學指標和代謝物。Liu 等[27]對患有股骨頭壞死的肉雞的骨代謝進行研究,發現其軟骨組織穩態受損,相關靶點數量顯著降低,血脂高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代謝水平異常[28]。Reis 等[29]開發了一個用于估計肉仔雞鈣磷消耗去向的模型,通過鈣和磷的消化吸收、軟組織和羽毛中鈣磷的動態變化及骨骼灰分動力學,預測肉仔雞對飼糧鈣和磷的反應,為探究腿病肉雞骨代謝的病理過程提供新的技術手段。康相濤等[30]通過高通量測序方法分析了腿病和健康肉雞脾臟的RNA,共發現50個差異表達的甲基化基因,在代謝途徑、2-氧羧酸代謝、肌動蛋白細胞骨架調節、嘌呤代謝、內吞作用等11 條信號通路中顯著富集,其中免疫信號通路MAPK、Toll 樣受體、P53 和其他單一通路參與骨骼疾病的發生。韓瑞麗等[31]用全基因組亞硫酸鹽測序繪制肉雞腿病獨特的全基因組DNA 甲基化表達譜,共檢測到4315 個差異甲基化區和2326 個差異甲基化基因,鑒定到與腿部健康表型重要的表觀遺傳基因ESPL1。郭麗萍等[32]基于高通量全基因組測序進行全基因組關聯研究,共鑒定到24 個腿病候選基因,注釋發現與血清堿性磷酸酶相關,并通過功能分析發現與骨骼疾病和骨質量相關的蛋白BARX3(BARX 同源核3)和Panx1(膜聯蛋白1),為解析肉雞腿病的發生機制和降低腿病發生率提供重要遺傳參考。
2.1.4 新抗病表型及適應性性狀表征
抗病表型的精準鑒定一直是抗病育種的難點,肉雞抗病力是多基因調控和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性狀,除了疫苗和藥物防治,培育擁有疾病抗性的優良品系一直是肉雞健康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嗜異性細胞/ 淋巴細胞值(Heterophil/Lymphocyte Ratio,H/L)最初作為雞的應激評估指標[33],后來被發現可以反映雞的強壯程度和免疫系統狀況[34]。有研究利用16S rRNA 和宏基因組測序技術分別對高、低H/L 比值雞的盲腸微生物群進行功能比較分析,發現與高H/L 比值雞相比,低H/L 比值雞有更豐富的免疫途徑、更低的抗生素耐藥基因和毒力因子,這些結果表明,H/L 比率低的雞對腸炎沙門氏菌的抵抗力更強;同時通過評估7 日齡雛雞的H/L 與沙門氏菌感染后(1、3、7 和21dpi)的組織載菌量和炎癥反應之間的關系,確定了H/L 可以作為生物標志物預測雞對腸炎沙門氏菌感染的抵抗力和炎癥反應[35]。王杰等[36]結合選擇信號、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和RNA-seq 結果,繪制了H/L 的基因組變異圖譜,鑒定到PTPRJ 基因是H/L 的調控因子,而位于PTPRJ 下游的SNP rs736799474 與中國土雞外周血的H/L 降低有關。
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是先天性免疫的基礎。有研究比較了不同雞種巨噬細胞的mRNA 表達譜,發現有1136 個差異表達基因,其中H2AFZ、SNRPA1、CUEDC2 和S100A12 是通過參與不同的免疫生物信號通路來調控吞噬作用的樞紐基因,通過整合轉錄組和基因組確定了與吞噬作用相關的靶基因H2AFZ[37]。Zhou 等[38]從體外和體內水平分析了H9N2 病毒對雞紅細胞中補體相關基因表達的影響,發現H9N2 病毒與雞紅細胞的相互作用,進而調控雞紅細胞補體相關基因的表達。Klein 等[39]利用原位低溫電子斷層掃描捕捉到了干擾素誘導跨膜蛋白3(IFITM3)介導的甲型流感病毒膜融合阻滯,表明IFITM3 能誘導脂質分選以穩定半融合,防止病毒進入靶細胞。Tang等[40]通過LC-MS 代謝物分析,RT-PCR 等方法證明了NDV 依靠氧化磷酸戊糖途徑(oxPPP)和葉酸介導的一碳代謝途徑來支持復制,而病毒復制的核苷酸合成機制受亞甲基四氫葉酸脫氫酶(MTHFD2)的調控。
2.2 遺傳育種技術發展現狀
肉雞種業技術發展從1900 年至今經歷了多次突破性發展。起初以個體或表型大群體選擇,這種方法僅對中高遺傳力性狀起到較好的選育效果。20 世紀中葉,開始利用標準品種生產的專門化品系,考慮個體體重、產蛋等指標,通過雜交組合選擇性能好、遺傳性狀穩定的家系生產商品代。1990 年后將最佳無偏預測(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BLUP)納入肉雞選育中。目前,現代肉雞育種以全基因組選擇(Genomic selection,GS)為主,白羽肉雞育種方案主選性狀從過往的產蛋量和生長速度轉變為到現在的生長速度、飼料轉化率和產肉性能。隨著現代育種技術(如基因組編輯和基因組重測序、轉錄組、代謝組技術)的飛速發展,白羽肉雞育種已經從傳統選擇向分子育種水平發展。
2.2.1 基因組學測序和多組學技術
肉雞大部分復雜性狀遺傳力較低,通常難以通過常規育種方法進行選育,因此挖掘與性狀相關的功能基因和關鍵變異位點對開展標記輔助選擇或GS 具有重要意義。變異是導致基因組差異的最重要因素,隨著二代測序技術的推廣,SNP變異被廣泛應用于群體遺傳學及基因組選擇研究中。2017 年我國自主研發了55K SNP 檢測芯片(京芯1 號),目前已更新至3.0 版本,補充GWAS 鑒定到的新肉品質、抗病性和產蛋量等性狀關聯SNP 位點,使SNP 數量增加至60K,且檢測成本進一步降低。近年來,大量研究開始關注單核苷酸變異、結構變異、全外顯子組測序、全基因組重測序和多組學變異。結合表型組、轉錄組、代謝組、蛋白組等多組學分析挖掘復雜性狀的主效基因和關鍵變異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2.2.2 白羽肉雞重要性狀的候選分子標記挖掘
鑒定挖掘白羽肉雞生長、肉質、抗病、飼料轉化等經濟性狀相關候選基因和關鍵變異位點,進行GWAS、性狀精細定位和性狀遺傳機理解析,為高產優質專門化品系的培育提供參考。在生長性狀相關研究中,Tan 等[41]以3 個純種肉雞和6 個地方品種個體進行全基因組重測序,結合2 個發育階段的6 種組織轉錄組測序,發現MYH1 基因家族在純種肉雞的肌肉中特異性表達,致病基因SOX6 影響胸肌產肉量,并與疾病的發生相關。張高猛等[42]利用京芯1 號芯片對白羽肉雞40 周齡種蛋受精率和孵化率鑒定到12 個SNPs;Ding 等[43]利用重測序數據進行meta 分析、選擇信號分析等手段定位到Z 染色體上一個QTL 區間,鑒定到了26 個SNPs 對產蛋數有顯著影響,其中rs318154184、rs13769886 和rs313325646 這3 個SNPs 位于PRLR 基因及其附近,這些研究為白羽肉雞孵化性狀的遺傳改良提供了重要的分子標記。在飼料轉化相關研究中,He 等[44]以多世代選育的廣明2 號白羽肉種雞群體為素材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和盲腸微生物、短鏈脂肪酸檢測。定位到4 號染色體上與丙酸顯著相關的基因組變異區間,其top 位點(Chr4:29,417,189:G>A)基因分型對飼料效率性狀和微生物群有顯著影響,為解析飼料報酬性狀調控機制和高效選育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44]。在肉品質相關研究中,Trevisoli等[45]以巴西TT 肉雞品系為素材,通過GWAS 分析定位到與胸肌、腿肌和腹脂相關的19 個QTL,鑒定到MYBPH 基因中的c.482C>T SNP 是肉用型雞脂肪沉積的因果突變。腹脂沉積會影響飼料效率、肉類生產成本和質量,為雞肉品質的遺傳改良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除生產性狀外,肉雞的主要經濟性狀如皮膚毛囊密度、膚色、脛色等屠體外觀性狀難以通過常規選育方法進行提升。Davoodi 等[46]利用雞Illumina 60k 高密度SNP 芯片研究影響雞羽毛顏色變化的全基因組的加性變異和上位性變異,篩選到HNF4beta、OPTN 和MIR1709 等18 個潛在影響雞羽色的候選基因,以及89 個與羽毛顏色變化有關的基因與基因組合,為雞羽色性狀研究提供了新的參考依據。
2.2.3 基因組選擇技術
隨著可檢測SNP 數量的不斷增加,與數量性狀位點(Quantitative trait loci,QTL)形成連鎖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LD)程度更高,更易捕獲到控制性狀的基因,Meuwissen[47]提出覆蓋整個基因組的遺傳標記來進行個體基因組育種值估計,即GS,也被稱為全基因組范圍內的標記輔助選擇。GS 可捕獲更多的遺傳效應,基因組育種值(Genomic estimated breeding values,GEBV)的估計準確性更高,且不依賴被預測個體的表型,可以直接實現早期選種,縮短世代間隔,進一步加快遺傳進展。近年來,大量GS 研究為基因組育種的數據輸入結構、模型構建、性狀特異性策略選擇等方面提供源源不斷的參考。近年來,大量GS 研究在數據輸入結構、模型構建、性狀特異性策略選擇等方面進行不斷的優化,以期進一步提高GEBV 預測準確。
有研究比較了基因組選擇中不同候選群結構對選擇準確性與預測平偏差的影響,發現添加商品代的信息會讓預測效果產生明顯的改善[48,49]。Abdollahi 等[50]使用一步法(Single-step BLUP,ss-BLUP)與常規BLUP 法分別對純系進行選育,發現在第6 個育種周期之后,2 個生產性狀在族群之間表現出強烈的分化趨勢,表明了ssBLUP相對BLUP 在育種改良上的優越性,并提出可以利用孟德爾抽樣(Mendelian sampling,MS)檢測基因組選擇的有效性。朱墨等[51]對比了基因組最佳線性無偏預測(Genomic BLUP,GBLUP)與貝葉斯回歸對肉雞胸肌率,腿肌率等性狀的預測性能,證明使用貝葉斯回歸法可以取得比GBLUP 更高的預測準確性,這與現有研究結果一致,貝葉斯回歸的預測準確性更高,但耗時更長,需要根據生產實際進行權衡。尹暢等[52]將55K 芯片填充至重測水平,對填充準確性與育種值預測準確性進行評估,發現填充對于白羽肉雞產肉性狀的育種值預測準確性提升并不顯著。而Herry 等[53]對不同的輸入數據類型進行對比,評估了ssBLUP 模型下不同數據對于選留結果的影響,認為可以使用限制性位點相關DNA 測序替代低密度SNP 芯片向高密度數據進行填充,可以降低成本的同時保證填充和基因組選擇的準確性。杜永旺等[54]將GWAS 結果與GBLUP 相結合,發現將GWAS 前top 10%~15%的SNPs 作為先驗信息整合到模型之中可以提升剩余采食量(Residual feed intake,RFI)的育種值預測準確性。Abdollahi[55]將GWAS 中前20 的顯著位點作為固定效應添加進BGBLUP 中,提升了對白羽肉雞體重與產蛋數的預測能力,表明GWAS 與GBLUP 進行關聯分析,可以大幅加快白羽肉雞的選育進程。Tan 等[56]對商品肉雞在基因組選擇下表型與基因組變化的影響,發現了多種產肉性狀在幾個世代間伴有相似的遺傳趨勢,同時出現了輕微的基因組分化,并猜測分化區域中對選擇有反應的基因可能與動物生產性能相關。
如圖4a 所示,廣明2 號父系純系公雞FCR年平均進展0.052/ 年,商品雞年平均進展0.03/年,2017 年使用基因組選擇后,FCR 進展速度提高33%(圖4b)。
當前商業育種的白羽肉雞基因組選擇技術包括DNA 自動提取、飼料轉化率及產肉率基因組選擇方案、芯片開發、升級及應用、育種值估計以及選留繁種幾個步驟,從生物樣本到基因組育種值選種可在2~3 周完成,技術流程穩定、高效和標準化。
2.2.4 基因編輯育種技術
基因編輯技術是在DNA 水平上引入優良個體或外來物種的特性基因,或是敲除致病基因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如CRISPR/Cas9。與傳統育種方式相比,CRISPR 基因編輯可以根據育種需求實現精準高效的基因定點編輯,從而縮短育種周期,降低生產成本,改善動物福利等。近些年飛速發展的CRISPR 技術已成為研究畜禽疾病機制,培育良好品種的新方法。
禽白血病病毒(Avian leukosis,ALV)一直是肉雞產業重點關注的傳染性疾病,基因編輯抗病雞種在禽白血病抗性研究中效果顯著。雞Na+/H+交換器chNHE1 是ALV-J的受體,細胞外部分的38 號色氨酸殘基chNHE1(W38)是病毒進入的關鍵氨基酸。Lee 等[57]通過CRISPR/Cas9 技術在雞成纖維細胞(DF1)上修飾ALV 病毒復制位點(tvb),成功建立對病毒感染具有抗性的基因編輯細胞系。病毒及其病毒聚合酶(vPol)利用宿主細胞機制能有效抑制病毒復制,通過CRISPR/Cas9 系統同源定向修復雞ANP32A 蛋白的精確替換,能有效抑制DF1 細胞中的病毒復制[58]。借助CRISPR 技術,Anna Koslová 等[59]在雞原始生殖細胞中實現了對W38 的精準敲除并成功制備抗禽白血病的基因編輯個體,是基因編輯抗病育種的重大進步,為家禽抗病品系的培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抗病基因編輯育種的第一步是需要得到安全可靠的抗病基因。因此,高通量篩選功能基因成為急迫需求。快速發展的CRISPR/Cas9 技術將候選基因的篩選擴展到了全基因組層面,使實現功能基因的高通量研究成為可能。目前,在人和小鼠上已有大量成功案例,在家禽上目前已成功構建全基因組敲除細胞系,如雞成纖維細胞系(DF1),雞肝癌細胞系(LMH),雞巨噬細胞(HD11)等,將成為抗病基因挖掘的重要工具。第二步就是確保整合到基因組的基因修飾能準確遺傳給下一代。鳥類原始生殖細胞(Primordial germ cells,PGC)介導的生殖系傳遞系統被認為是將遺傳信息傳遞給下一代的最有效的方法。Dimitrov 等[60]使用CRISPR 靶向PGCs 中的雞免疫球蛋白重鏈基因座,并產生健康的轉基因后代,驗證了編輯系統的有效性。Challagulla 等[61]敲除PGCs 的ICP4 基因,并產生能抵御馬立克氏病的基因編輯后代。但PGCs 分離技術要求高,從體內分離的數目有限,PGCs 培養和大量繁殖在技術上仍有難度。
3 基因組選配技術
基因組選配技術是指利用基因組信息確定最優親本交配組合,保證后代最佳的生產性能,即雜交優勢最大化[62]。在白羽肉雞育種技術中,配套系是雜種優勢利用的深入,是雜種優勢利用的高級形式。
當前對雜種優勢的研究和利用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對雜種優勢機理的探索,內容包括雜交組合的顯性、超顯性效應形成機制。Chunning 等[63]在以科尼什雞和羅德島白雞為親本的雜交雞研究中,發現體重性狀在雞的早期生長中表現出負優勢,特別是胸肌重。通過全基因組基因表達譜進行機理分析發現,非加性基因(顯性基因和超顯性基因)及其相關的氧化磷酸化是影響雞生長負優勢的主要遺傳因素。二是進行預測雜種優勢的算法開發。Amuzu-Aweh 等[64,65]使用全基因組SNP 標記信息研究等位基因頻率差的平方(Squared difference in allele frequency,SDAF)和雜種優勢之間的相關性,證明SDAF 是商業蛋雞雜種優勢的有效預測因子。
基因組選配是相比基因組選擇更復雜的育種策略,不僅對近交衰退進行規避,還考慮了顯性,上位等非加性效應,最大程度地發揮親本的遺傳潛力,在實際生產環境中具有更加廣泛的應用前景,將會成為未來肉雞育種的重要研究方向。
4 小結
從整個國際形式上看,國際育種巨頭有長期的素材積累與技術優勢,引進品種短期內在我國市場上還將占據主導地位。國內白羽肉雞育種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隨著政策的支持與分子育種技術的不斷應用,國產白羽肉雞種源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我國已經走出了育種的自我摸索的階段,但育種是長期任務,未來仍需要技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