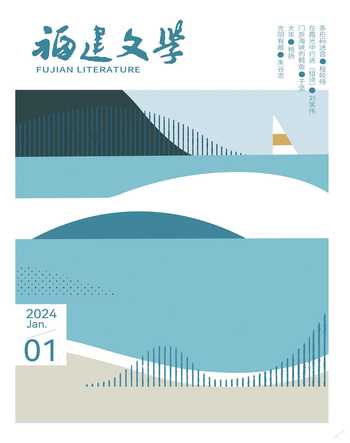長白或太白
趙燕飛

從沒見過那樣的夜空。
天還沒有黑透,所有的晚霞糾結成團,似要擰成一支巨大的火炬,點亮即將到來的暗與黑。火炬的背后,隱約浮現幾抹麥苗般的新綠,夾雜濃重的深紫。這一切,不過是序曲,而高潮,是星星,密密麻麻擠滿蒼穹的星星。
從沒見過那樣的明鏡。
四周是高聳的山峰,那些山峰堅硬得寸草不生,卻在夜的溫柔圍困之下失去了斑斕的色彩。它們沉默著,俯視腳底那塊明鏡。那是怎樣的一塊明鏡啊,仿佛所有的繁星不是閃爍在夜空,而是在鏡中競相綻放;它們照見宇宙的過去,也照見宇宙的未來。流星從不可知的遠方飛來,一頭扎進鏡子的深處。一顆流星是雨滴,一串流星是小溪,一路流星是瀑布,它們不管不顧,要和鏡中的另一個自己緊緊相擁……
這一切,來自朋友轉發的圖片。我有些疑惑,明鏡般的天池怎么美都說得過去,那樣光禿禿的碩大的石峰,竟是長白山的一部分,好沒道理。我想象中的長白山,高處終年積雪,低處流水淙淙,飛禽走獸在密林里自由穿梭,慵懶的山參在地底下緩慢生長直至變成人形。長白之巍峨,即便火山噴發,也只是短暫的死寂,一場甘霖就可使萬物重生。我寧愿自己缺乏科學常識,唯有這樣,我才能違背所謂的規律或邏輯,一廂情愿地想象世間的百般從容與千般美好。
不愿將日子過成一潭死水的人,大多向往詩,向往遠方。
長白山于我,是詩,更是詩一般的遠方。
當我跟隨眾人坐上景區的中巴車,從天文峰的腳底一路往上攀爬,我還有點不敢相信,長白山從虛幻的想象中走出來,真真切切地展現在我的面前。
準確地說,從長春出發坐車前往二道白河時,我們就已經進入了長白山,這是當地的朋友告訴我的。作為南方人,我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以為一座山就是一個凸起的大山包,再高也不過是一個大山包。我原諒自己的無知,又指著車窗外的田野,問那些或青或黃的植物是什么。朋友瞥了瞥我指的方向,很篤定地說:“都是玉米,我們這邊叫苞米,也有叫苞谷的。”
我沒好意思再追問,事實上,我確實連一個小玉米棒子都沒看到。我的視力不太好,以前不過有點小近視,現在慢慢老花,以至于遠的近的都看不清楚了。某天,我要釘一粒襯衣扣子,穿針時,發現針眼小得離譜,線頭被我擰得尖尖的,幾乎比一根頭發絲還要細,我的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總算將線頭塞進了針眼,忙不迭抽出線頭來,卻發現自己不過是空歡喜一場,線頭壓根就沒進針眼,或者進了針眼又擅自原路返回了。我從小就執拗,哪怕屢試屢敗,也要不撞南墻不回頭。我揉了揉酸脹的雙眼,邊揉邊暗暗發誓,今天非得將這根線穿進這根針不可。重來一次,沒進;還來一次,沒進;再來一次,依然沒進……大概折騰了半小時,我終于如愿以償。取得勝利的我,心里卻被什么堵得嚴嚴實實的,唯有張開嘴,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那種窒息感才會略有緩解。是的,我沒法寬慰自己。再愚蠢的人,也懂得這樣的勝利經不起任何推敲。
快到二道白河時,天完全黑了,兩旁的路燈安靜地亮著,尾巴蓬蓬的松鼠站在燈的左側,層層裂開的松果坐在燈的右側,松鼠的一雙眼睛滴溜溜的,松果的無數眼睛一眨不眨,我們在它們的夾道歡迎中飛馳而去。我回過頭,想著有沒有松鼠從燈桿上一躍而下,追咬汽車發動機的聲音。
二道白河,本是一條河流的名字,依河而生的小鎮,也取了這個名字:二道白河。長白山管委會就位于二道白河鎮。作為一條河,它的出身頗為“高貴”。天池被群山環抱,但在北側天文峰和龍門峰之間,卻有著一處小小的缺口,天池之水從那個缺口溢出,沿著補天石慢悠悠地流啊流,乘槎河就這樣誕生了。這條河又名通天河。通天河在懸崖峭壁之中流到伏牛石時,河水被分成大小不等的兩股,從一千二百多米的斷崖處突然跌落,掉入下方的深潭,落差六十八米的長白瀑布由此誕生。長白瀑布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口瀑布,當它奔涌而下時,只見潭水飛濺,白浪滔滔向前,形成一條綢帶般的河,這就是二道白河了。
那天,我站在距離長白瀑布幾百米遠的水文觀測臺上,仰望來自天池的水變成乘槎河變成瀑布變成深潭又變成二道白河。這座水文觀測臺其實是一座平緩的小坡,坡上蹲著很多石頭,石頭上面趴著墨綠色的苔蘚,那些墨綠里綴著星星點點的紅,湊近去看,才發現那是苔蘚所開的花,小小的紫紅色的花,每一朵都像新生嬰兒般惹人憐愛。石頭與石頭的縫隙間,偶爾鉆出一朵或黃或藍的野花,有一種嫩黃色的野花格外嬌艷,打開手機里的識花軟件,說是“長白罌粟”,忍不住驚嘆了下,這么美的花,的確配得上如此獨一無二的名字。就在長白罌粟的邊上,我發現了一株多肉。那株多肉葉片肥厚,葉片一層一層往上疊,形成一座蓮花臺。我很想將這株多肉帶回家,當地的朋友卻連連搖頭,說:“你弄錯了,這不是多肉,它的名字叫鈍葉瓦松,你帶回去也養不活的。”
鈍葉瓦松?我從沒聽說過,是不是朋友記錯了?上網一搜,果然有這種植物,長得像多肉的瓦松,猶如人類的童年。當它們抽出長長的松果般的花箭,開出或紅或黃的花,那是它們的盛世華年。花箭枯萎成黃褐色的直直的“狗尾巴”時,意味著瓦松匆匆過完了它們的一生。有人瞧不起瓦松,以為它們開花雖有氣勢,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既成不了棟梁,也當不得飯吃,甚至做不了柴燒,幾乎就是“廢物”。它們還喜歡長在高高的屋頂,睥睨世間蒼生,仿佛自己有多大本事似的,哪里像低調的菊花,寄身低洼之地卻永葆高潔之志。對于這些鄙視,瓦松從不解釋什么。不管它們生在哪里,都是餐風飲露,都是默默長自己的葉悄悄開自己的花,它們才懶得計較世人的一時之好惡。
瓦松已經很稀罕了,沒想到還有美人松。作為“長白山下第一鎮”,二道白河還是美人松的“故鄉”。
剛剛走進位于二道白河鎮的美人松公園,我就舉起手機四處拍攝。那些千姿百態的松樹們,或挺直腰身探向蒼穹,或枝葉婆娑笑看異鄉之客,隨便選個角度,都是一張絕美的風景照。
松樹原本很普通,我的故鄉到處可見馬尾松。小時候去奶奶家玩,我最愛跟著堂哥去山上拾柴,那些干柴中,就有枯死的馬尾松,或是一根枝條,或是半截樹身,奶奶說這樣的柴火煮出來的飯菜格外香。一眨眼就是幾十年,奶奶早已過世。若是奶奶知道世間竟有身姿曼妙美人般的松樹,她會生出怎樣的感慨?奶奶九十九歲的時候,她的腰身仍像這些美人松一樣筆直。在我的童年記憶里,奶奶的個子很高,我得抬起頭來仰望她的臉。此刻,我抬頭仰望一棵美人松。離地二三十米的高度,她的身體長出許多枝丫,那些枝丫形狀各異,有的像碧綠的扇面,有的像張開的黛色裙裾,有的像遺留在白天的某片蒼茫夜空;還有兩根光禿禿的黑色枝丫,可能已枯死多年,一根仍微微上舉,似是不肯放棄塵世的掙扎;另一根決絕地斜伸出去,仿佛已經打定主意坦然認領自己的命運……
不知天文峰上有沒有瓦松,有沒有美人松。
坐在中巴車上,我的視線一直朝向窗外:白色樹皮的樺樹,矮矮壯壯的松樹,黃色的山柳菊,紫色的千屈菜,還有開著白花的漆姑草,沒看到美人松,更沒看到瓦松。海拔越高,植被越矮越少。漸漸地,窗外只剩下五顏六色的石頭。我的眼前忽然閃過一塊石碑,扭頭望去,碑上寫著三個大字“黑風口”。憑直覺,這里應有一處景點,但中巴車仍氣喘吁吁往山頂去,我只好再次請教手機。果然,從黑風口的某個最佳觀測位置,可以看到長白瀑布的全景。正遺憾,驀然發現那些五顏六色不僅僅是石頭本身的色彩,還來自附著其上的苔蘚或草本植物所綻放的小小花朵。南方的苔蘚大多為綠色,到了長白山,才知苔蘚的一生也能活得這般多姿多彩。黃色的苔蘚開白色的花,綠色的苔蘚開紫色的花。
因為苔蘚的緣故,黑色的石頭也能開出彩色的花。
不知拐了多少個彎,我們乘坐的中巴車終于抵達天文峰停車坪。直到這個時候,我對長白山天池的想象仍然有些不著邊際。當地的朋友早就有言在先,天文峰并非天池的最佳觀測之地,因為無法看到天池的全貌,即使到了觀測點,能不能看到天池也是未知數。還在長春時,他們就一次又一次查詢近期天氣預報,若按既定計劃登山,我們能夠看見天池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我微微一笑,這樣的概率不理也罷: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臨上山前,大家又開始分析概率,沒想到比之前還要低。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哪怕概率為零,也無法阻擋我們攀登天文峰的決心了。
下了車,沿著天文峰山頂的臺階一步一步往上爬,不知為什么,我的腿忽然有些發軟,站著歇口氣時,同伴問我是不是有點高原反應,我這才醒悟過來,對啊,海拔兩千多米,兩腿發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于是放慢速度,走幾步,扶著腰站一會兒。快到最高處時,發現一群人圍著護欄,有的舉起手機錄視頻,有的擺出勝利的手勢拍照。眾人興奮不已的時候,我還沒意識到懸崖之下就是那個著名的火山口。
出于好奇心,我擠進人群,找到一處可以容身的小缺口,扶著護欄往下望,只見一叢叢白霧撲面而來,看不清那些霧想要遮掩什么,耐著性子等了一會兒,霧忽然散得無影無蹤,一大片波光粼粼似藍還綠的水面驚現眼前。仿佛內心的準備還不夠充分,我張大嘴巴,有些不敢相信,天池以這種捉迷藏的方式與我相見,完全在我的想象之外。作為一座處于休眠期的火山口,天池表面的波瀾不驚更顯神秘。沒有人知道它在暗暗積攢怎樣的力量,更沒人知道它會在什么樣的時刻爆發。可以想象的是,地殼深處的愛恨情仇日積月累,熾熱到頑石都化為熔漿的那一剎,天池所在的位置成了地球表層的軟肋,力與力的對抗找到了最后的突破口,沖天一怒,地動山搖,灰飛煙滅之后,大地的似水柔情撫慰長白山深不可測的傷口,涅槃重生的天池不僅擁有絕世之容顏,還孕育了三條著名的河流:鴨綠江、松花江、圖們江。
山上天氣多變,又有那令人愛也不是恨也不是的大霧企圖阻擋遠方來客的殷切目光。據說有人往返好幾趟都沒能看到天池究竟長什么模樣,那樣的懊惱,想必離開長白山之后仍會耿耿于懷。我們第一次來長白山就能目睹天池的真容,哪怕只是一鱗半爪,也算心想事成,沒什么好遺憾的了。
長白天池有著怎樣驚心動魄的過往,二道白河兩畔的火山石或許知道答案。在河床的干涸處,我撿了幾塊顏色各異的火山石,有暗褐,有灰白,還有深黛。火山石的身上全都坑坑洼洼的。這些坑坑洼洼,既是它們前世的未了情,也是它們今生的墓志銘。
據說唐朝時長白山又叫太白山,長白或太白,又有什么要緊?一切的一切,順其自然便好。
責任編輯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