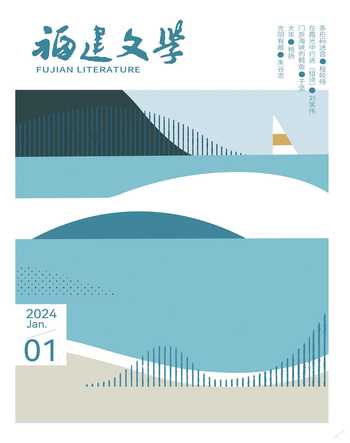他就是詩人魯藜
吳爾芬

近了,近了,故鄉近在眼前。
問故鄉,問故鄉,別來無恙否?
可是詩人的眼前一片模糊,他什么也看不見,縱橫的老淚蒙住了雙眼。
52年,超過半個世紀啊!52年前離開故鄉時,他還是迎風而立的熱血青年,此時呢?詩人已經整整70歲,身形不再挺拔,腰彎背駝,頭發斑白稀疏,步履蹣跚。他需要扶住村口的大榕樹,才不至于跌倒。
這棵大榕樹長在自家的西南側,樹高冠闊,虬髯飄拂,長長的分枝深深地扎進土里,彎成一座榕根“拱橋”,成為一道別樣的風景。詩人不知道它幾歲了,只知道村民都叫它“東角榕”。
當年,詩人在家鄉搞農運,被軍警深夜圍捕,便是踏著這榕樹越墻逃脫,再次離開故鄉的。那是詩人第二次離開故鄉,第一次他太小,才3歲,沒有任何記憶。流落異國他鄉后聽父親說,這個叫許厝的故鄉,是他的出生地。
父親說有一座叫“小盈嶺”的山嶺,上接三魁山,下連鴻漸山,山脈延綿到天邊,神仙都走不到頭。鴻漸山脈的左側有一座香山,北側的山腳下有一座小小的村落,那就是許厝村。
許氏先輩在這貧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按族譜輩分排列,到了父親這一輩已是第十九代,是“派”字輩,父親名叫許派纏,是個寡言少語之人。
宣統皇帝下臺的那一年,恐慌中的許派纏又添加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命運弄人哪,許妻已經生下10胎,這第11胎是個女孩多好,可竟然是倆兒子,這可怎么得了?許派纏橫下心,送出去小的,留下大的,還給他取了個“涂地”的名字,意思是依靠耕種農田養活。雖然母親生了11胎,但許涂地只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兵荒馬亂的,孩子養不活呀。
許涂地3歲那年,張勛留辮子,廢帝又登基,局勢更亂了,兵匪不分,盜賊蜂起,哪有窮人的活路?為了躲天災避人禍,許派纏變賣耕牛和口糧,連一塊山地也轉了,勉強湊上20塊銀圓,買到一張許厝人叫“大字”的出國證書,帶著一家人搭乘木篷船,從沙坡尾廈門港起程,漂洋過海來到越南湄公河畔,落腳在堤岸市邊沿一個唐人聚集的貧民窟。這個當時叫“二十九間”的地方,后來叫胡志明市五區。
父親不識字,做不了體面的事,終日在一家小作坊干粗活。當雜工的母親更累,沒日沒夜地操勞,腰桿沒有直過,肩膀沒有閑過。這個可憐的女人褲管永遠是濕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腫得像兩只爛柿子。她常常累得在爐灶下打盹,東家就往她的腦門上潑冷水,將她激醒。
盡管夫婦倆累得后腳踩前腳,盡管全家饑一頓飽一頓,但許派纏以一個莊稼人的質樸,認定這個小兒子是塊讀書的料,再苦再難,也要供他上學。
于是,年幼的許涂地進了當地一所華僑小學,老師覺得“涂地”兩個字太土,便諧音取了個學名“許徒弟”,要收他為徒的意思。
許徒弟著了魔似的用功讀書,每科成績都拿5分,給許派纏爭了臉,也給二十九間的華僑爭了臉。
然而好景不長,許徒弟上高小第一年,母親又生了個妹妹,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家境更加困窘。父親為了多賺一點小錢,去碼頭扛大包。12歲的許徒弟輟學了,先到一家面條鋪當學徒,學會做面;面條鋪關門,他就在華僑聚居的二十九間沿街叫賣;叫賣不來錢,只好混進碼頭,給父親當幫手。可是人小體弱的許徒弟實在扛不動大包,絕望中沿著湄公河漂泊。
湄公河默默地流淌,一個羸弱的身影悄悄地沿岸行走,那個苦難的少年流浪漢就是許徒弟。許徒弟常常坐在岸邊,注視河水急速地往前,不知道苦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冬天是百業的淡季,家里斷糧是常有的事,母親雖然還在哺乳期,還是自己空著肚子,將最后的食物留給丈夫和孩子們。許徒弟的心揪得更緊了。為了讓母親不挨餓,他自己到河邊轉悠,撿一點能入嘴的東西,植物的葉子和根莖,就是他的佳肴。即使找不到食物,許徒弟也故意拖到深夜才回家。可是,不論夜有多深,母親都坐在家里等他,眼里飽含淚水。
給許徒弟黑暗的生活帶來一絲亮光的,是一位叫陳天助的鄰居。陳天助叔叔來自臺灣,住在一間終年不見陽光的小屋里,他行走江湖,靠拔牙鑲牙賺錢度日。重要的是,這個牙醫識文斷字,能用閩南話吟誦唐詩宋詞。
閩南話保留了中原普通話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唐詩,用閩南話朗讀平仄是最對味的。這對失學的許徒弟來說,吸引力太大了。在陳天助的指導下,許徒弟閱讀了大量古詩文,為少年的想象插上飛翔的翅膀。許徒弟想,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寫詩,那該多好呀!我一定要寫出人間的悲與喜、苦與樂,寫出自己的盼望與期待。
少年許徒弟的內心有太多的苦悶與煩惱,他用最樸素的語言,將詩與歌寫在地上,寫在墻上,寫在紙上,寫在天空。一個流落天涯的詩人種子,在湄公河畔的土壤中發芽、生根,以破土的身姿迎迓東方輝煌的日出。
18歲,許徒弟出落成一個風度翩翩的青年。這個青年帶著夢想,滿懷激情,以超越的目光打量翻天覆地的世界。國內傳來的消息,每一條都讓青年許徒弟震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日軍向遼西發動總攻,十九路軍浴血閘北,溥儀開始滿洲國傀儡生涯……許徒弟多想踏進祖國的土地,成就一番文學事業。
許徒弟做夢也想不到,他會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回國。
這一年,父親許派纏身患重病,魂歸故土成了他最后的夙愿。許徒弟決心幫父親了卻心愿,護送生命垂危的病人回到故鄉。
父子同心,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許徒弟托人幫忙,把父親藏在堆放煤塊的貨船艙底,自己裝扮成船上的伙夫,逃過了關檢,逃過了人頭稅,成功偷渡。
當許徒弟背著父親走進香山腳下的許厝,兵連禍結的故鄉已經是怎樣的滿目瘡痍?到處殘垣斷壁,村民衣衫襤褸,農田拋荒長稗,連骨瘦如柴的狗,見了陌生人都只齜一下牙,沒有力氣叫喚。此時此刻,青年許徒弟才真正理解“窮鄉僻壤”這個詞的含義。
3歲離家的青年腦筋轉不過彎來,難道這就是自己魂牽夢縈的故鄉?如此破敗,如此凋敝,看哪,在那荒草叢中,竟然有狐貍出沒。再看祖屋老家,更是不堪入目:面闊三間其實不算小,進深一間,塊石構砌墻裙,土坯磚墻,卷棚脊,硬山頂。可是厝前野草萋萋,房后的庭院改建成的小護厝已多處坍塌。
還好,淳樸的鄉親見流落他鄉的父子歸來,操上鋤頭劈刀就來幫忙,總算把病重的許派纏安頓下來。
不久,許派纏就告別了人世。許派纏的親屬都在湄公河畔,靈前只有一個對家鄉陌生無知的兒子,后事怎么辦?正好,在集美鄉師當指導員的許有韜老師回到許厝的家,見這個喪父的英俊青年彷徨無措,便帶頭張羅出殯的事。鄉親們有的送米,有的送錢,讓許徒弟有了依靠。
收殮時,許徒弟買不起棺木,左鄰右舍又湊了一點錢,買了四塊松木板,釘成棺。兩個土工抬著薄薄的棺柩,許徒弟哭在其后,鄉親們一起送上山頭。沒錢買石灰,土工只好用常見的赤土堆了一座矮墳。于是,禿嶺上便多了一抔黃土,一個逃難出海、重病歸來的老華僑被埋在里面,落葉總算歸了根。
目睹父親如此悲慘的結局,許徒弟的心底深深扎下憤懣的種子:這個世道潰敗了,得變。如今,父親躺在里邊,母親遠在天邊,祖國處在懸崖邊,放眼海峽兩岸,哪里是我的家呢?身為中華兒女,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不挺身而出,有何臉面在家鄉吃閑飯?
苦悶的許徒弟徘徊在榕樹下,有時仰天長嘆,有時埋頭短吁。許有韜老師看在眼里,明白一個熱血青年的無助。不能改變出身的許徒弟,發誓要靠知識改變命運。關鍵時刻,許有韜給許徒弟指明了一條道路:去集美鄉師讀書。陳嘉庚創辦的集美鄉村師范實驗學校,不要學費,還包膳宿,只是考試嚴格,最適合許徒弟這種會讀書的貧窮青年。
果然,許徒弟憑借自己的努力考入集美鄉師,并在廈門的《江聲報》發表了詩歌處女作《母親》。許徒弟以高挑的身姿、清澈的眼神、溫和的面容、激情的文字,很快就成為同學中的明星。
接著,許徒弟從廈門來到上海,在陶行知創辦的“山海工學團”擔任夜校輔導員。詩歌《我們的進行曲》發表在《讀書生活》時,出于對魯迅的崇敬,許徒弟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魯藜。在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集會上,魯藜巧遇鄒韜奮,鄒韜奮高興地握著他的手,向周圍的朋友介紹說:“他就是詩人魯藜啊!”
從此,許厝村的許徒弟消失了,文壇出現一個青年詩人魯藜。
從此,魯藜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一名戰地記者,成為“七月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呼應“以血淚為文章,為正義而吶喊”的時代要求。他有一顆永恒熾熱的心靈,性情溫和如水,內心熱烈似火。他的詩歌格調清新明麗,有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交融的韻味,自成一家,不但得到朱自清、聞一多、胡風等名家的稱贊,也得到文學史家王瑤的推崇,受到很多關注和肯定。“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經漫長歲月冶煉,你屬于純金。”艾青這樣評價魯藜。
魯藜自稱“憂患的寵兒”,不料一語成讖。
為詩而活的魯藜,為詩而戰的魯藜,在堅硬的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他的人生沒有絲毫詩情畫意,有的只是坎坷不斷,波折不停,不管是感情,還是創作,都是磕磕絆絆、跌跌撞撞、起起落落。他的名字和一個叫“胡風”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他的火熱年華跟國家一個動蕩的年代高度重疊,他的命運怎么能好呢?
經歷了26年的折磨,魯藜身體瘦弱,額紋深陷,風華正茂的青年詩人成了骨瘦如柴的老人,窮得只剩下一雙筷子、一只碗、一個黑乎乎的鍋、一張小行軍床。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魯藜的眼里仍然閃爍著熱情的光芒,眉宇間照樣堆滿童真的笑容。這是一張詩人的臉啊,他的臉就是一首史詩,有艱辛的內涵,有明快的表征。
真的,魯藜的一生就是一首悲壯的詩,只是在他痛苦的深淵里“浮出彩霞的光彩”。
詩人珍惜“命運留給我的一片晚霞”,以衰弱的身軀和剛強的內心不倦地歌唱。他要與死神賽跑,抓住詩神的尾巴,在生命結束之前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于是,詩人發出了最歡愉的聲音:“我只要一滴水/我就可以盡情歌唱/
唱得天地間/只有陽光、花朵與詩歌。”
他頂住了年老多病的困擾,頂住了激情與靈感的瀕臨枯竭,徹夜寫作,滾燙的詩頁如夜幕降臨的倦鳥,匆匆飛向可以棲息的枝丫。短短五年,就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刊物發表100多首詩作,其中一部分結集為《鵝毛集》《天青集》出版。
這是怎樣的晚年呀,魯藜巴不得把輕盈的身體擺上詩歌的祭壇,掏出尚能跳動的心對天起誓:詩神啊,我愛你,勝過愛自己。“詩人老去詩情在”,于是魯藜晚年的詩,進入彌漫著哲理思考的內省天地。
這么一個歷盡苦難癡情不改的赤子詩人,當時隔52年再次重返故鄉,內心會是怎樣的凄凄慘慘,抑或波瀾壯闊?
1984年4月,火紅的鳳凰花在鷺島盛開的時候,魯藜偕夫人劉穎西回來,到廈門大學參加“臺灣文學研討會”。詩人欣喜地看到:故鄉的詩歌活動猶如滾滾海潮,后浪推前浪,一浪高過一浪;青年的詩人們宛若郁郁相思樹,一茬高過一茬。新時期以來,廈門每年都舉辦“鷺島詩會”,恰似鳳凰花開,洋溢熱烈生機。
一個星光璀璨的夜晚,廈門市工人文化宮的大廳燈火輝煌,熱鬧非凡,第三屆“鷺島詩會”拉開帷幕。那是一個詩的時代,充滿詩的激情,詩的表達,詩的遠方。這一屆詩會,因老詩人的歸來而異常鼎沸,詩歌愛好者歡聚一堂,以鳳凰花的絢爛心情、相思林的蔚然陣容、鷺江潮般經久不息的掌聲,熱烈歡迎久經劫難而詩心如磐的新詩先行者——魯藜的蒞臨。面對鄉親們洋溢的笑靨、后來者贊嘆的聲浪,詩人心潮逐浪高,文思勝泉涌,即興朗誦《獻給白鷺詩人的歌》。
他動情地說:“我是寫詩的,今生仍然要為親愛的祖國做貢獻,仍然要為詩而燃燒!”
會議結束后,魯藜歸心似箭,攜妻子返回翔安許厝村。
近了,近了,故鄉近在眼前。
然而,近鄉情更怯,舊時巷陌今何在?親朋故友可安好?詩人展開雙臂,要把故鄉攬進胸膛,他來不及洗去車旅的勞累,就到田間地頭走親訪友。
“我回來了,故鄉!”這是魯藜對所有人的問候。他“迸發著淚花投進”許厝的懷抱。詩人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故土,感慨何止萬千:“我依偎著車窗凝望過去/心濤如澎湃的鷺江/半個世紀緋艷的風云/如同一道瞬息變幻的彩虹。”
夜深沉,寂靜的山村彌漫著流嵐,魯藜躺在木床上,心中涌出從未有過的踏實。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就像成熟的果實,無枝可依,飄落大地是唯一的歸宿。都說葉落歸根,其實真正歸根的是果實,融進泥里,生根發芽,成長為故鄉的風景。朦朧的夜色透進窗欞,如粉般散落床前。屋后的榕樹發出嘩嘩的林濤,那是對游子歸來的問候嗎?
第二天清晨,魯藜牽手妻子在村中漫步,鄉親們見到傳說中的詩人都頷首相迎,用最淳樸的閩南話問道:“吃了沒?”
“吃了。”魯藜用生硬的閩南語應答。
佇立在榕樹下思考,是魯藜的至愛。濃蔭如巨蓋、氣根如飄髯的榕樹是詩人的精神源泉。坐在榕樹下,魯藜可以徹底忘我,像一滴水融入海中,像一口氣呼出空中,像一個詩人融化在詩情畫意中。“樹啊,你能否告訴我/我那些游伴都星散何方/也許都像金色的種子/各自飄落于黑色的土壤去孕育希望。”
這一次,魯藜夫婦在許厝住了7天,正好一周,每一天家里都是高朋滿座;這一次,詩人會見所有慕名前來拜訪的詩歌愛好者,傾其所有指導晚輩;這一次,70歲的老人重修了父親的墳墓,交代了后事;這一次,難道當年的許涂地知道自己是重返家園的最后一次?
1999年1月13日,在漫天飛雪中,魯藜安詳離世。
再過一年,就是人類的21世紀,魯藜離去了,他的詩歌卻在21世紀被傳誦。
在翔安建區20周年之際,筆者來到魯藜的故鄉,看到在內厝鎮政府、在第二實驗小學、在魯藜小學、在許厝村,在每一個顯眼的位置,都赫然立著魯藜的半身塑像。在廈門,他的詩作代代相傳;在翔安,他的故事為人津津樂道。
如今,許涂地的故居舊厝,已打造成魯藜紀念館。墻上懸掛詩人自己書寫的代表作《泥土》,每個文友都在這張書法作品前駐足。因為這首短短的四句詩值得每個人銘記,也值得時代銘記。
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
就時時有怕被埋沒的痛苦
把自己當作泥土吧
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
責任編輯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