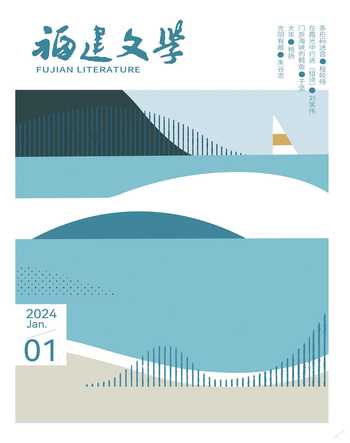風吹塔里木
張揚

1
到新疆的第一夜,入住在庫爾勒市。較之于內地城市,孔雀河畔的夜色姍姍來遲,天幕上長留銀質般的光芒,人也顯得亢奮。晚風舒緩而柔和,有著近似小提琴曲的節奏與美妙。樹葉在光影交錯中輕舞,發出沙沙的聲響,好似一陣雨來。槐花、合歡的清香幽幽飄散,也有絲絲縷縷匯到一起,凝在行人的鼻尖。
每一種植物,或許都有其生命的胎記與生存密碼。槐樹、合歡以及桑樹等,是南方常見的樹種。它們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東北邊緣繁茂生長,與高低錯落的眾多建筑一樣,讓從內地來的我覺得眼熟,生出親切感。植物如人類一樣,有著漫長的遷徙過程。實際上,桑樹是從高海拔往低海拔移植的,而后又從東往西,遠到異國他鄉。茶葉也是一路遷徙、播種,從中國“移民”到歐洲。亦有從西往東,來中國落戶的植物,比如西瓜、西紅柿、胡蘿卜、仙人掌等。在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太多“移民”故事,包括植物、動物。
庫爾勒曾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座重鎮,現屬南北疆交通樞紐。庫爾勒街頭的香梨樹、楊樹,店鋪中的抓飯、馕餅、羊毛毯、銅茶壺之類,合成一組特殊的意象與符號,也像提示外來者,這里是有別于其他地方的城市。
連續的高溫天氣,忽地戛然而止。出門時,天陰著,雨滴三三兩兩飛落。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風沙強勁。古來萬事萬物難占全,地下累積海量油氣,地表缺著溪流湖泊。若雨量充沛,說不定到處流水潺潺,綠樹蔥蘢,花團錦簇。水草豐茂,物產富饒,人丁興旺,是古國古城的依仗,也是今日城池繁榮的象征。
遠古時期,山崩地裂、海枯石爛的全景,實難想象。在塔里木盆地,曾多次發生地質演變,每一次構造變動,都交替著速亡與速生。滄海桑田之后,海水離場,地層中的油氣聚集埋藏。風不分年月,也不知疲倦,搬動著沙粒、土壤。盆地中,遺存著被稱為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一些山體夾雜著蒼白的貝殼、粗糲的鵝卵石,透著無比古奧與荒涼。
天山,昆侖山,以及阿爾金山,環繞著塔里木盆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這首《白云謠》,傳說是住在昆侖山的西王母,與周穆王訣別時所唱。故事的結局并不圓滿,周穆王未再返回,西王母郁郁而終。依照《山海經》描繪,女神西王母竟是豹尾虎齒,蓬發如戴勝鳥,半人半獸一般。
云天漠漠,極目之下,山大多赤裸,無一草一木裝扮。路兩旁的山,干枯到手一碰即可粉碎似的。實則,刀砍斧削一樣的山體,有的特別堅硬。金庸筆下的玄鐵,也許就潛藏其中。稍遠些的山,籠著蒙蒙塵煙,似有千軍萬馬在奔突、鏖戰。此時,鉛灰色云團緩緩移動,風從地面吹向溝溝壑壑的山里,又在荒無人煙的山谷打著旋,成了天上地下渾然一色的組成。
更遠處的,是隱現在天際的高山。山尖繞云,一束耀眼的光柱從灰色云層中射出,對準山之巔,照得積雪瑩瑩然。那正是蒙著神秘面紗的雪山,猶如遙遠而不可及的古國,突然露出冰山一角。
1946年,于右任至天山南北,望山得句:
雪似山之衣,云似山之冠。
修潔復修潔,容君面面看。
雪山偶現的那一刻,人所能做的,就是不言不語,面向雪山凝神、遠觀。現場情況正是如此,眾人在一瞬間陷入了集體沉思。
雪山亙古沉默。自雪山而下的水,先是勢若猛獸,而后由強到弱,或徘徊不前,或倔強流淌。枯水之季,盆地中的河流,有的明顯變淺,有的似有若無。
2
洪荒遠去,絕處逢生。由盆地邊緣,向盆地中心,亦即塔克拉瑪干沙漠進發。沿途所見,像電影鏡頭,閃現著綠色、灰色、黃色以及紅色。此季的青楊、白楊一律青綠,沒有秋日下那般熱烈絢爛。戈壁灘或沙丘之間的紅柳枝條,近似松柏。其枝葉間,盛開著米粒般的小紅花,密密麻麻,似要證明它們的強大,環境再惡劣,也能綻放其美,沖淡大面積的冷色調與沉悶的氛圍。
以蘆葦編織的草方格,嵌在沙漠公路兩旁的沙丘中,用來阻擋、延緩流沙。車窗外,高壓電線伸向遠方,鉆井、站房不時閃過。風不甘寂寞,一路追隨,無休無止地撲打著車身。車屁股上,啪啦啪啦地響個不停,似雨點猛砸。車窗甫一打開,肉眼看不見的細沙、微塵,隨著一股風,呼地涌入車內。車內的人,趕緊將車窗搖起。一天跑下來,車身便蒙了厚厚一層灰塵。
去往輪探1井的路上,遍地可見枯死的胡楊。這時的風,如染土黃色,充斥著肅殺之氣。它從伏地的胡楊、立著的梭梭上刮過,發出尖厲的呼嘯聲。一不留神,我的右眼迷了沙塵,被磨得生疼,接連幾天,都是紅腫模樣。
連綿不絕的沙丘,是塔里木盆地中心最明顯最厚重的地表呈現,它刺激到人的視覺,讓人震撼、眩暈,也讓人感到枯燥。路越走越遠,天地間的赭黃愈發深重。在這樣的空間中,人的所有想象、欲念與行動,與無垠的沙地糾纏在一起。每一日,人在看沙,沙也在看人。為著油氣勘探、開采的人們,長期身在沙漠,其體會應當更為深刻。
大漠里的天氣,說變就變。一日之中,或晴,或雨,或陰,或為沙塵暴,或復歸于晴天。緊隨變化的,是難以捉摸的風。風有時凌厲如刀,有時如溫熱毛巾敷面,有時干爽不惹塵埃似的。風是無形的,善于變著戲法,又仿佛被灌注神奇力量,幻化出具象,成為長者、詩人、浪子或者魔鬼,忽而和藹,忽而斯文,忽而調皮,忽而森然恐怖。
沙漠遼闊,原本無路可走,憑著人力,硬是從中蹚出寬路、窄路。路平坦或坎坷,俱要人走;沙冷沙熱,也需人來感知。月照千古,風吹萬里,昔日出訪的使者,布道的僧侶,戍邊的士兵,流放的官員,冒險的考古者、旅行家,踽踽獨行有之,三五成群有之,涉足不毛之地,或命喪于此。
風卷起黃沙,駝鈴一聲復一聲。65年前,一支特殊的勘探隊,行進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這支勘探隊規模不小,由320峰駱駝與120人組成,九進九出“死亡之海”。最終,70多峰駱駝倒在了沙漠里,再也沒能站起。今日若立一座碑,紀念這些駱駝和曾經的壯舉,未嘗不可。
此后,勘探、修路乃至運輸物資,動用了多種“重武器”。天上飛機低翔,沙丘上奔馳著特種運輸汽車。塔中1井飛機跑道,是塔里木油田唯一留存的鋼板跑道。這條千米長的跑道,承載過運輸的重任。名為雙水獺的飛機,在這里起起落落,每天載人載物,往返于塔中至500公里外的廓爾勒。
在塔中1井飛機跑道,幾位中年人放下矜持,像孩子一樣撒歡。每個人都張開雙手臂,沿著跑道向前,加速、加速、再加速,想象著自己騰空而起,想象著御風而行。風,微微吹著,有清泠之意。眾人的笑聲,回蕩在湛藍而高遠的天空。時光匆匆,曾經少年,秀眉白面,鮮衣怒馬,為賦新詞,無愁說愁。如今中年,可高歌,可歡呼,可發少年狂。將來老了,也是溫暖的回憶。
在塔里木,油田人日行千余里,家常便飯而已。于我,身體則有些吃不消。有一天,趕了長長的路,途經坑坑洼洼的地方,車顛簸如船行汪洋,全身骨頭被顛得幾乎散了架。往滿深5-H10井的路上,所有人的手機信號都中斷了,失去聯系與導航功能,好像一下子與世隔絕了。行進的路,一再走錯。彎彎繞繞之后,目的地才被找到,一時人困馬乏。
轉來轉去,這一帶的沙漠,光禿禿一片,未見胡楊,也無其他植物。之前下了雨,沙丘半干半濕,像濃釅的咖啡現出拉花圖案。此時此刻,沙海近似枯黃色,呈現出柔美的線條。在風的策動下,它一旦有了動靜,簡直山呼海嘯。
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春季的風沙,尤其頻繁,肆無忌憚。在沙漠中忙碌的人,睜眼有沙,呼吸有沙,張口有沙。每到一處,油田的人,總會提及沙塵暴。未經歷沙塵暴的我,有些無知無畏,甚至期待遇見。
過塔里木河的那天,一開始天陰沉著,雨點飛濺到車窗玻璃上。奔向輪西油田桑吉公寓的路上,煙霧狀的沙塵隨風騰起,由遠及近,越來越濃,直至遮天蔽日,一片昏暗。風沙四面圍合,刮著車頂、車廂、車的底盤,轟然作響。車速不得不慢下來。初見沙塵暴,人很緊張,又有點興奮。逢遇極端天氣,人除了盡力規避、抵御,有時差不多束手無策。幸而,這場沙塵暴的烈度有限,車沖出了其肆虐地帶。重見了藍天,人長吐一口氣。
3
萬頃流沙下,覆蓋著沉積億萬年的巖石。穿越堅厚無比的巖石,開掘出一條萬米深的油氣通道,難似登天。深地塔科1井,中國首口萬米科學探索井。這口特深井的啟動,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探險,地質科學家、工程師、油氣勘探者所要應對的,屬于極限挑戰,包括極高溫、極高壓與極高的地應力等。開鉆前,沙塵暴幾乎天天襲來。太陽在人們的眼里變換著顏色,一會兒是灰的,過一會兒成了黃色,再一會兒,一片紅了。戴上安全帽與護目鏡,工人仍是灰頭灰臉,少不了吃沙土。幾十年前,在沙漠流動作業,遇到沙塵暴,勘探者住的帳篷,呼地就被吹翻了,生活物品也被吹得無影無蹤。現在進行類似作業,以集裝箱組成工作間、宿舍,可擋一擋風沙。
深地塔科1井正式開鉆時,碰上了吉日,當天風平沙靜,一切順順當當,所有人的眉頭都舒展了。鉆井以每天200米左右的速度,向地層深處掘進。要穿越十余套地層,掘至萬米深,如在茫茫夜色中,由珠穆朗瑪峰的峰頂向山麓,作精準投籃。
2023年7月30日,一行十余人,到了深地塔科1井工地。地面上的井塔,高不足百米。井下,已鉆至5856米,觸及5億年前形成的地層。井一段一段掘,地層深處的鉆井動態,自有“火眼金睛”般的監測系統盯防。工地上,擺了一排木盒子,分裝著取自地層深處的巖屑,并一一編了號。從盒子里,我選了一枚巖屑,采自地深5643米,深灰色,指甲蓋大小,用手捏住它,好似觸摸到地球內部秘密。之后,在戈壁灘上,撿到一枚指節長的風凌石,我將它與那枚巖屑包在一起。歷經地火淬煉的巖屑,與經受風侵雨蝕的風凌石,相遇在了浪蕩乾坤。
無風無雨時,一只沙漠之狐躡足而來,在深地塔科1井工地探頭探腦。工人們見了,輕手輕腳干活,生怕驚動了它。有人拿出自己帶的面包,丟在沙地上。狐貍慢慢走近,試探地嗅了嗅,又警惕地往左右看了看,才銜起面包,轉身而去。不幾日,這只狐貍又來工地討食,工人們掰了饅頭,扔給它,它的膽子大了,在作業區轉了轉,才離開。一來二去,這只狐貍踩準了工人作息時間,到了飯點就來轉悠,甚至拖家帶口討食。半年不到,它長壯了,尾巴上的黃毛又厚又亮。
在油田開車的一位司機,遇過沙漠之狼。那天傍晚,他停穩車,下來歇息,就看到一頭狼盯著他。狼看他,他也看狼。狼并無進攻、侵犯的架勢,他也就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機,朝狼拍照。手機閃光時,那頭狼霍地掉轉頭,跑遠了。
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度被稱作生命禁區,縱然如此,也阻擋不了探索者的步伐,又不乏其他生命活躍。那幾日,聽到多樁與沙漠動物相遇、相伴的故事,想看到它們的念頭更強了。
走走停停,幾次遇到蜥蜴。這小動物,跳躍起來,快如疾風,只有當它靜靜地伏在沙石上,才可見其樣貌。空曠的沙漠或戈壁灘上,鳥聲顯得微弱,仿佛一不小心就被風吸走了。白尾地鴉、黑頂麻雀、小沙百靈只管飛來跳去,它們尤其迷戀“沙漠綠洲”,早早晚晚鳴叫不休。
地氣充滿神奇,塔里木盆地物產自有其美。風吹紅了一顆顆大紅棗、金絲棗、沙棗,也吹熟了棉花、玉米、白杏、西瓜、哈密瓜。在塔里木油田,入住的每一處公寓,房前或屋后都有油田人開墾的池沼、菜地。水池里,大魚小魚浮浮沉沉。菜地里,生長著傲嬌的辣椒,紫得發亮的茄子,藤蔓纏繞的南瓜,粉刺滿身的黃瓜,甜蜜蜜的白蘭瓜。沙地上,向日葵開得正歡;場院中,誘人的葡萄綴滿一叢叢葡萄架。
風吹在牧羊人的身上,牧羊人形同一尊雕塑。往塔里木油田大北1202井路上,遇到一位牧羊人。他戴了一頂帽子,滿臉黝黑,絡腮胡黑中泛白,一雙手反背在身后,且橫握了一根白色木棍。牧羊人的身體靠近一處山崖,往前走一兩步,便是漏斗式的山谷與褶皺山脈。放牧時,自家的一只羊走丟了,牧羊人沿著山路徒步找尋,途中向油田工人打聽。在沙漠中,但凡碰見受傷的羊,油田人都會帶回去救治,然后歸還給牧民。山坡上的風,一陣強過一陣,像河流中的旋渦,欲將人卷走似的。站在坡頂的牧羊人,一遍遍掃視著山谷,期望發現羊的蹤影。
少時誦讀古代民歌與邊塞詩,幻想自己奔跑在大漠草原,花鮮草肥,牛羊成群,手把牧鞭高高揚起。待到人至中年,但知事事如意難,人間辛苦多,放牧的活,其實并不輕松。
從大北1202井區返程,顛簸而行。三只野羚羊,不聲不響,從山坡的一側躥出,迅疾不見了,唯余一股塵煙彌漫著。繪畫者善用留白,野羚羊似通其妙,它們現身、遁去,僅僅一剎那間,讓人驚喜,又意猶未盡。
傍晚,回住處路上,見到幾十峰駱駝散在戈壁灘上。落日熔金,戈壁灘閃著金光,瘦而高的駱駝低頭啃食,身上薄薄的絨毛也披了一層金光。風悠悠,駱駝閑閑。
駱駝啃著的,是一簇簇駱駝刺。它們也愛吃梭梭的嫩枝。梭梭貌不驚人,又不同尋常,承受力超強。它耐旱,也耐寒,還抗鹽堿,其根系入地,可深達八九米。正所謂竹竿打蛇,一物降一物,梭梭可用來防風固沙。梭梭的根部,往往寄生著“沙漠人參”肉蓯蓉。其嫩枝可作飼料,也能為羊毛紗線著色。梭梭結的果,常被誤作花樣。它的種子,有如蒲公英,隨風到處飄散。梭梭當柴火燃燒,火力奇旺,有“荒漠活煤”之譽。陶宗儀《輟耕錄》說,用梭梭燃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
4
風拂過條條林帶、片片林網,掀起層層綠浪。塔中,建有全國首條零碳沙漠公路。這是一條綠色長廊,連通著塔里木30多座油氣田。無水維系,綠色長廊難以為繼。每隔4公里,路邊就有一口水源井,井旁,蓋著低矮的紅頂藍墻的水井房。水井房附近,穿插栽植著大量梭梭,以及紅柳、沙拐棗等。夏日到這里,清涼的氣息,無聲無息地沿著人的體表,滲透進每一個毛孔。
沙漠之中,一株樹兩株樹三株樹挺立,一朵花兩朵花三朵花盛開,都有詩意情味。駐守水井的工人,如園丁一樣,看護著井區的林木、花草植被,定期給植物澆水、施肥。梭梭是天選之物,管護工是綠色守護者,均顯示著生命韌度。
羅宗蘋與老伴龔義明,早已習慣這里的風吹日曬。他們駐守32號水源井,將井區的植物料理得活潑潑的。別人隨手帶來的一束滿天星,也被他們栽活了,長成了一大蓬。
2023年7月24日,晨風輕微,沙丘如睡。羅宗蘋同往常一樣,走出水井房。進入東面的草木叢,她突然大喊:“老龔,快來,快來看!”比她早7年來這里當管護工的老伴,聽到老婆呼喊,以為發生了什么事,趕緊跨出門,一看,原來梭梭開花了。龔義明樂了,他笑老婆大驚小怪。不知為何,羅宗蘋來這里已9年,尚是首次見到梭梭開花。她彎下腰,湊近聞了聞,拿手機拍了照。與遠在浙江的女兒通電話時,她也聊到梭梭開花。一朵小花,成了她生活的一份驚喜與念想。老伴的身體不大好,羅宗蘋悉心照顧著。煩悶時,她便與草木說話,又似一個人自言自語。當我來到32號水源井,她說起梭梭開花的事,還領著我,去看開過花的那一株梭梭。
又是一天,風呼呼吹著夜行的人。在月夜,唐代詩人李賀胸臆難抒,慨嘆大漠沙如雪。那夜,我隨眾人穿越沙丘與沙壟。月如琥珀,星光熠熠,身前身后黑黢黢的。腳下的沙,也非清亮如雪,只是細而軟,特別纏腳。走到油田管理區時,近旁灌木叢中,驀然躍出一只野兔,其毛色為黃白相間,耳朵尖而長。它時而跳躍,時而靜臥,幾分鐘后忽然停下來,一動不動,像在等人。眾人走近,七嘴八舌問好,說它是玉兔下凡。兔子豎了豎耳朵,頗似得意,倏地躥回灌木叢。
風日日吹在大漠里,吹到西氣東輸第一站,似乎減緩了節奏。站控室內外,一派整潔,又井然有序。這里被稱為“塔里木油田的心臟”,關聯著大“氣脈”。每時每刻,從這里源源不斷,向外輸送著清潔能源。
克拉是鉆石的度量,以克拉命名的一口口井,猶如嵌入地層的一顆顆巨大鉆石。克拉2—7井,每天出氣,足夠近千萬人口城市一天用量。與其他單井一樣,這口井無須人現場值守。這邊廂,安安靜靜,獨守一處;那邊廂,萬家燈火,流光溢彩。風喜歡來探視、嬉戲,從一根根紅色的管道上鉆進鉆出。淺淺流沙經過,風一吹再吹,細沙又遠去了。偶爾,雨滴從空中飄落井區,驚了鬼頭鬼腦的蜥蜴、沙鼠。
5
往塔中鎮的路上,風幾乎停歇了。一輪圓月由東升起,西邊的太陽,尚未落下。眾人又一次觸景談詩。茫茫大漠中,孤煙直上,長河靜流,落日渾圓。這般景象,若非詩人經歷,斷斷難以狀摹。王維的《使至塞上》中,潛藏著孤獨意味,更有慷慨之情、豁達之風。
不懼風沙的油田人,宛如行走的詩人,用雙腳在大漠中寫下一行行詩,詩中兼有敘事、抒情與說理。他們熟悉這里的每一天,懂得春風的多愁與煩惱,體會到夏日蒸騰似熱鍋,驚嘆秋色的鋪排與爛漫,也為冬雪覆蓋沙漠的壯美所震撼。比起他們,初來乍到的我,只是暫時從一種生活經驗中抽離出來,進入一種新的奇特的環境,不過是匆匆過客,也不過是共情未深的觀眾。
那天,在塔里木油田哈得一聯合站,看到墻報上寫著“高興也是生產力”七個字,就停下了腳步。這一行大字,上下左右都配了工人的笑臉圖。他們個個燦然,讓人看了,如沐清風。一撥撥年輕人,帶著熱血與憧憬,自天南地北奔來,披上石油紅,頂風而行,踏沙而歌。時間長了,他們也會褪去青澀,像一株株梭梭扎根于此。
千里之行,行于塔里木盆地。一路走來,如同讀書不斷。仿佛這里是一座巨型熔爐,人與風,與沙,與梭梭,與蒼鷹野兔,與高山河流,與一切存在者,同受冶煉,直面生死。在塔里木盆地,對于身外之物,一個人很可能覺得不過爾爾,而眼前的一滴油、一瓶水、一碗飯,又讓人切切珍惜。輪臺,焉耆,尉犁,若羌,庫車,且末,拜城……遇見的每一個地名,都縈繞在我的腦際。它們如竹簡木牘、古玉琉璃,折疊著過往,又讓來訪者聽到風中傳遞的密語,見識到它的滄桑、沉靜與奇絕。
時光流轉不停,塔里木盆地有鬼斧神工,更有人的創造之力。新風徐來,當長出大片大片的花木,結出滿園滿地的瓜果,它們繽紛可愛,芬芳可親,與簇簇燈火構成繁華盛景。彼時,日月昌明,水波蕩漾,人潮涌起,飛禽走獸出沒。
責任編輯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