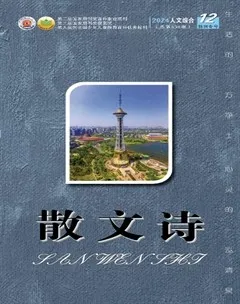工業現場的抵達
2024-01-13 00:00:00胡游
散文詩(青年版) 2024年12期
關鍵詞:情感
詩歌通常被定義為語言凝練、具有較強節奏韻律、形式美感的文體。新詩以個人發現和認識世界,不斷追問事物的存在,而成為一種發散型思維的藝術。當一首詩完成時,詩歌文本并不是固定存在于那里、等待發現和認識,而是不斷處在流動之中。顯然,詩歌不是被凝視的圖畫,也不是“精致的甕”,而是繼續流轉在我們存在的世界。在姜念光的詩歌《株洲行》里,一些龐大的、崇高的事物以另一種形式復活,如“偉大的作品”“光輝歲月”等。日常生活驅動下的詩歌寫作,造成的破碎感、碎片感,在此處被粘合為一種有意識的理性建構。它是利奧塔筆下的“元敘事”,也是現代性的特有內容。
然而,詩歌終究是非理性的文學題材,情感表現力強于邏輯的表達。這情感的著力點,我想還是在于“現場的抵達”,提供的是情感的證據,而非客觀真實的事實。《株洲行》帶著歷史的記憶,閃耀著金屬的光澤,譜寫的是株洲工業騰飛的現場。如“把工業的種子,播撒在湘水之濱的琴箱里/勞動的蜂巢,思想的星辰,鋼鐵的詞根”,這兩行詩句通過陌生化的表達形式,傳遞著語言背后的情感張力。還有“我看到一輛汽車被解構,離散又完整/這多像我的兄弟”,在“自我”的體系里,尋找到一股自然涌動的兄弟情。《株洲行》對工業現場獨特的意象捕捉,是準確生動的。工業現場不僅有汽車,也有詩歌的質感,像“啞光肌膚的硬質合金/堅不可摧,能夠抵達鉆石和事物的本源”。這表明詩歌不僅需要情感的積蓄,也需要審美意識的指導,方能在事物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傳遞詩歌的本質力量,就像詩人所寫:“我感覺自己也裝上了引擎”。
猜你喜歡
今日教育·作文大本營(2025年3期)2025-03-24 00:00:00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家庭醫學(下半月)(2020年4期)2020-05-30 12:42:50
現代裝飾(2020年4期)2020-05-20 08:55:06
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小太陽畫報(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海峽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 07:49:00
青年歌聲(2019年7期)2019-07-26 08:35:00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發明與創新(2016年6期)2016-08-21 13:4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