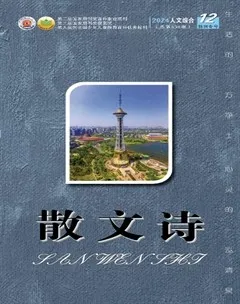“工業(yè)詩歌”如何抒寫
工業(yè)詩歌的寫作難度在于命名的難度和感受的難度。詩歌寫作是外在世界和個(gè)人內(nèi)心情感的融匯。工業(yè)題材有一種速度感、瞬間感,其帶來的內(nèi)心震驚不僅僅是高鐵、計(jì)算機(jī)和機(jī)器人帶來的,也是高速發(fā)展中“人”位置的改變帶來的。機(jī)器對人身體的解放,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面對工業(yè)生產(chǎn)一線,類似的詩歌創(chuàng)作還處在生發(fā)之中。這類獨(dú)特的體驗(yàn)遲遲未能進(jìn)入詩歌寫作視野,一方面是缺少具體而鮮活的“現(xiàn)場”,另一方面也來源于工業(yè)與個(gè)人內(nèi)心圖景聯(lián)結(jié)的難度。如何書寫、如何命名成為一個(gè)問題。
胡丘陵的詩歌《車間》帶有很強(qiáng)的工業(yè)屬性和詩人的審思力量。面對個(gè)體的內(nèi)在經(jīng)驗(yàn),詩人調(diào)動直覺的感受、覺悟和想象的熱情。“車間”在胡丘陵的筆下成為平靜的老人,這無疑是將豐富的生活和描述性的場景結(jié)合了起來。在具體的真切的呈現(xiàn)中,“車間”和“個(gè)體”自由地貫通,浸透生命的情感和個(gè)人的發(fā)現(xiàn):“年輕的火,只在肝內(nèi)憤怒燃燒/沖動的水,只在腸管內(nèi)激烈流淌”。
工業(yè)術(shù)語和專有設(shè)備名稱為詩歌增加了“工業(yè)”成分。詩人抓住工業(yè)車間里的“車銑”“鏜銑”加工工具。工具提高車間加工效率和精度,提高產(chǎn)品品質(zhì)。詩人也開始反思艱難的“長詩”寫作和輕巧的短詩創(chuàng)作。長詩和短詩本身并無高下之分,但是與工業(yè)設(shè)備關(guān)聯(lián),就變成了一次心靈的博弈。夾雜著對工業(yè)發(fā)展的欣喜,充沛的感情在機(jī)器面前有一種無措與迷茫。正如本雅明所認(rèn)為的“機(jī)械以轟然的節(jié)奏打破了個(gè)體生活的整體”。機(jī)器代替了人的手工勞動,原本的工人將何去何從。如此種種思考自然而然在《車間》一詩中呈現(xiàn)出來。工業(yè)時(shí)代決定了人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在這樣的處境下,人類如何安放心靈,如何安放自我成為詩人進(jìn)一步思考的時(shí)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