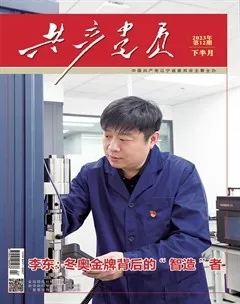陳曉東:勇闖北極點
欒光煜

2023年9月27日,中國第13次北冰洋科學考察隊搭乘“雪龍2”號極地科考破冰船順利抵達上海,標志著歷時78天的本次科考任務圓滿完成。對于大連理工大學運載工程與力學學部教師陳曉東來說,今年36歲的他已經是第三次參與北極科考了。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科考是我國科考船首次抵達北緯90度暨北極點區域開展綜合調查,陳曉東成為我國首位抵達北極點并開展現場采樣的海冰力學研究人員,他在北極點開展的工作也填補了我國海冰物理力學性質研究在該區域的數據空白。
首次到達北極點
他填補相關領域研究空白
第13次北冰洋科學考察隊于2023年7月12日搭乘“雪龍2”號從上海出發,總航程約1.55萬海里,歷時78天。
此次隨隊科考,陳曉東主要參與走航海冰觀測及海冰力學性質測試方面的工作,在47個大洋站位、6個短期冰站和1個長期冰站作業期間,完成了包括海冰力學性質現場測試及采集、走航海冰參數自動化觀測、無人機觀測等任務,共采集海冰冰坯試樣0.52立方米、冰芯柱試樣181柱,其中在北極點采集冰芯試樣15柱,填補了我國海冰物理力學性質研究在該區域的數據空白。陳曉東進行的兩項工作——首次針對北極海冰開展沖擊載荷作用下海冰力學性質的現場試驗工作與基于雙目成像的海冰厚度無人化智能觀測工作——均被納入第13次北冰洋科學考察的研究亮點。
“剛出海的日子里,和家里的通信相對多點兒,中間有40多天,通信就很費勁了,到了北緯80度以北,海事衛星都不好用了,只能偶爾在固定的位置用衛星電話聯系到家里。”陳曉東說,每次通話時間都很短,只能簡單報個平安,分明能感到電話那頭妻子的擔心和牽掛。
陳曉東告訴記者,2010年,我國第4次北極科考隊曾經到達北緯88度區域,但由于冰層過于堅硬以及氣候影響,破冰船無法再向前推進,只能遺憾地望“北極點”興嘆。而第13次科考,我國自主建造的“雪龍2”號極地科考破冰船性能更優良,加上此次北極點區域的溫度為-4℃,氣候和冰層情況都較“配合”。在行船途中,船長和隊長通知大家:“這次我們有可能到達北緯90度的北極點。”“聽到這個消息后,全船都沸騰了,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們真是太幸運了!”陳曉東說。
成立臨時黨支部
他沖鋒在前甘于奉獻
科考隊到達北極圈當天,便成立了臨時黨支部,全體黨員莊嚴宣誓。作為一名青年黨員,陳曉東沖鋒在前,用實際行動踐行著黨旗下的誓言。在冰層上打冰芯是個體力活,光機器就有十幾公斤重,再加上穿著特制的極地羽絨服,工作起來著實有些“遭罪”,一會兒工夫就是一身汗。陳曉東不僅一絲不茍地完成自己負責的工作——現場測試、采集冰芯、運輸海冰,還一有空就主動幫助水文組、大氣組、地球物理生物組等其他科研組做實驗、搬設備。進入北極圈,是24小時極晝,很多科研人員的生物鐘都紊亂了。陳曉東見縫插針地休息,當團隊需要幫忙時,他即便是剛要睡覺,也堅持爬起來支援。
在此次科考途中,陳曉東還受邀擔任“北極大學”授課教師,與大家分享極地科考對海冰力學研究的意義。看到大家饒有興致地聆聽并頻頻點頭,他的內心更增添了一份奮力前行的力量。
自從得知能到達北極點區域這個令人激動和振奮的消息后,陳曉東就想著以什么樣的方式記錄下這難忘的時刻。到達北極點的前一天,陳曉東用木板制作了一塊地標指引牌,上面刻著“大連5678km”,這是北極點到大連的距離。其他的科考隊員看到后,都覺得這個做法有意思也很有意義,于是紛紛效仿,動手制作自己城市的地標牌。北京5568km、上海6566km、天津5657km、合肥6466km……十幾個指示牌制作完畢,被釘在一根木棍上后插在了冰面上,指示牌指向隊員們各自家鄉的方向。陳曉東創意的這一地標牌,成了科考隊員們打卡拍照的“標配”,為大家定格了難忘的人生瞬間。
傳承大工科研精神
他再苦再累也無怨無悔
陳曉東反復強調,這次能有機會參與這項重要的科考工作,而且還填補了相關研究空白,并不是他個人的成績,其背后是大工幾代人的努力和傳承。
陳曉東對學校海冰力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如數家珍,無意間列出了一條鮮明的脈絡——1990年,大連理工大學青年教師岳前進針對渤海石油平臺的抗冰問題開展了結構冰載荷研究;2000年,岳前進教授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季順迎在渤海石油平臺上現場監測結構冰載荷;2014年,已經成為工程力學系教授的季順迎帶領他的學生陳曉東在“雪龍”號科考船上開展了我國首次極地船舶的冰載荷監測;2023年,參加第13次北冰洋科學考察隊的陳曉東隨“雪龍2”號科考船抵達北極點,并開展了一系列船舶結構冰載荷與海冰力學的研究工作。這是三代學者的學術傳承,更是科研精神的傳承。“經過三十余載、三代人傳承,大工人從渤海遼東灣走到了北極點。雖然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北極海冰快速變化,但大工人服務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的宗旨不會變!”陳曉東激動地說。
不管是參加科考還是在學校做教學和科研工作,陳曉東都迎難而上,積極傳承科研精神。由于經常要與“冰”打交道,陳曉東的實驗室總是像冷庫一樣,即便室外是炎熱的盛夏,但只要進入實驗室,他便要里三層外三層地“武裝”起來,外面還得套上羽絨服。在實驗室里全身心投入科學研究,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陳曉東有時甚至會“恍惚”,一時反應不過來“現在到底是什么季節”。除了給學生上課和泡在實驗室里,每年冬天,陳曉東還要隨團隊到最寒冷的地區采集冰樣、進行極寒地區海洋工程相關數據的勘測。長時間待在寒冷的室外,有時眉毛、胡子都會結冰。
陳曉東坦言:“科研工作是艱苦的,常常要舍棄一些東西,但既然選擇了這條科研報國的人生之路,就只顧風雨兼程,再苦再累也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