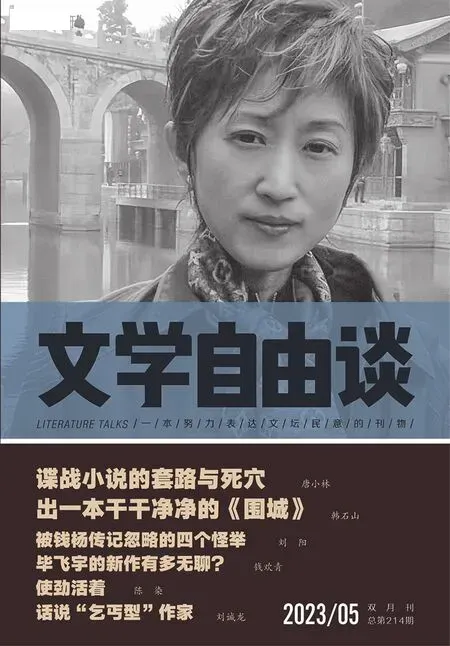被錢(qián)楊傳記忽略的四個(gè)怪舉
□劉陽(yáng)
錢(qián)是錢(qián)鍾書(shū),楊是楊絳。“錢(qián)楊”已是當(dāng)代文壇上一個(gè)醒目的符號(hào),就像“蘇張”除在極個(gè)別場(chǎng)合下指蘇軾與張懷民,一般只專指蘇秦和張儀那樣。萬(wàn)人如海一身藏的錢(qián)楊伉儷,著作至今在印,傳記至今在出。不過(guò)讀遍這些存世材料,我仍然感到,他們的若干顯得奇怪的舉止,沒(méi)有得到必要的留意,而成了身后之謎。出于對(duì)現(xiàn)有錢(qián)楊傳記在觀照這些謎、揭示傳主立體面目方面的不滿意,我將這些怪舉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四個(gè),寫(xiě)出來(lái)向大家求教。也懷著拋磚引玉的心情,期待今后新出的錢(qián)楊傳記能從正面來(lái)解這些謎。
本著對(duì)兩位先生令名的欽敬,我仿照學(xué)術(shù)體例,在逐一提出四個(gè)怪舉的同時(shí),分別以注、鑒、評(píng)三層結(jié)構(gòu)展開(kāi)。這或許也能在目感上顯得清楚明白些,更便于列位看官瀏覽和裁斷。四個(gè)怪舉里,錢(qián)楊各占兩個(gè)。女性優(yōu)先,先談楊的兩個(gè),再說(shuō)錢(qián)的兩個(gè)。
怪舉一:擔(dān)心小說(shuō)被后人隨意續(xù)寫(xiě),自己提前寫(xiě)出續(xù)書(shū)并出版。
【注】因?yàn)榕既宦?tīng)到一個(gè)讀者令她“嫌惡”的故事走向猜測(cè),楊絳先生便自行了斷故事的結(jié)局,匆匆忙忙地出了薄薄一冊(cè)《洗澡之后》。看前言:“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寫(xiě)續(xù)集,我就麻煩了。現(xiàn)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jié)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也給讀者看到一個(gè)稱心如意的結(jié)局。……我把故事結(jié)束了,誰(shuí)也別想再寫(xiě)什么續(xù)集了。”書(shū)最后不忘再?gòu)?qiáng)調(diào)一句:“誰(shuí)還想寫(xiě)什么續(xù)集,沒(méi)門(mén)兒了!”可見(jiàn)戒備之深。小說(shuō)問(wèn)世后,反響平平,甚至頗多批評(píng)意見(jiàn),和當(dāng)初《洗澡》在讀者中的深入人心不可同日而語(yǔ)也。
【鑒】在我有限的見(jiàn)聞中,一個(gè)健在的作家因怕自己的小說(shuō)被后人“糟蹋”,而趕在生前親自鎖定續(xù)書(shū)結(jié)局者,只此一例。續(xù)寫(xiě),大致有這樣幾種情形:一、作家沒(méi)把故事寫(xiě)完便去世了,比如《紅樓夢(mèng)》;二、作家已把故事寫(xiě)完并去世,但后人意猶未盡而對(duì)原故事續(xù)貂,且另有寄托,像陳忱的《水滸后傳》、張恨水的《水滸新傳》以及佚名的《后西游記》;三、作家已把故事寫(xiě)完并去世,后人借題發(fā)揮,以續(xù)書(shū)形式講今天的新故事,有童恩正的《西游新記》等為證;四、奪胎點(diǎn)金,李清照的《如夢(mèng)令》,便是對(duì)唐人韓偓《懶起》(“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cè)臥卷簾看”)的創(chuàng)造式續(xù)寫(xiě),褚同慶的《水滸新傳》也可視為此種類型。唯獨(dú)聞所未聞,有作者活著時(shí)給自己作品寫(xiě)好續(xù)書(shū)的,難道不叫人奇怪?
【評(píng)】作家珍視聲名,連帶愛(ài)惜自己的作品,本無(wú)可厚非。但為防止后人續(xù)寫(xiě)不合己意的結(jié)局,急著自己封死情節(jié),分明流露出“我的東西你碰不得”的心態(tài),和楊先生激賞的蘭波詩(shī)句“我和誰(shuí)都不爭(zhēng),和誰(shuí)爭(zhēng)我都不屑”自相矛盾——不仍在斤斤計(jì)較,和后人“爭(zhēng)”嗎?談不上做人的大透徹。請(qǐng)?jiān)徫覕M于不倫,油然想到前塵夢(mèng)影里那個(gè)拿《富春山居圖》陪殉的故事。復(fù)再尋玩“我們仨”這個(gè)被人津津樂(lè)道的書(shū)名,覺(jué)得個(gè)中的獨(dú)尊情緒和意味,也真蠻有意思的。
這是一層。另一層是,以為作者提前寫(xiě)畢續(xù)書(shū),就保證了后人老老實(shí)實(shí)夾緊尾巴、不再打這部作品的主意,未免也讓人哭笑不得:創(chuàng)作時(shí)間的終點(diǎn)不代表故事的終點(diǎn),作者能一廂情愿地“把故事結(jié)束”?忘了接受美學(xué)的原理嗎?古人云,“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別說(shuō)續(xù)寫(xiě)是正常的文學(xué)史現(xiàn)象,就算流露出翻版必究的用意,大浪淘沙,作者自家的續(xù)作良可備一格,卻不妨礙別人同樣可從自己的角度繼續(xù)平等往下寫(xiě),焉能賦予自己壟斷文本意義的特權(quán)?
至于楊絳本人倉(cāng)促殺青的這個(gè)帶有大團(tuán)圓俗套色彩的續(xù)書(shū)結(jié)局,是否成功,倒在其次了。熟稔中西戲劇理論的她不會(huì)不知,中國(guó)戲劇對(duì)團(tuán)圓的看重,歸因于中國(guó)文化的“一分為三”特征,較之于西方文化重視“一分為二”、擅長(zhǎng)形成矛盾與爭(zhēng)論,我們一上來(lái)篤信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不能由此簡(jiǎn)單判定兩種戲劇觀孰優(yōu)孰劣,我感慨的只是,期頤之年的楊先生太心急了,觀念上,藝術(shù)上,都未能將這件事處理得更漂亮——本來(lái)豈非可以更大氣些不是?
怪舉二:在預(yù)感遠(yuǎn)行前親手毀去自己的日記。
【注】從吳學(xué)昭《聽(tīng)楊絳談往事》得知,楊絳在年事漸高之后,“親手毀了寫(xiě)了多年的日記”。這倒給了好奇如我者一個(gè)意外的收獲:原來(lái)?xiàng)钕壬恢庇袑?xiě)日記的習(xí)慣。
【鑒】對(duì)照兩年前問(wèn)世的皇皇十二冊(cè)《夏承燾日記全編》,真不知該對(duì)這類老來(lái)自毀日記之舉作何評(píng)騭。一名有高地位的文化人,日記里會(huì)涉及有價(jià)值的人和事,客觀上可以為后代留下信史,作為作者就真沒(méi)隱隱考慮過(guò)這些文字將來(lái)的用途?帶著這個(gè)疑問(wèn),與作家韓石山海侃,極力鼓動(dòng)也堅(jiān)持記了半個(gè)多世紀(jì)日記的老韓,擇機(jī)出版自己的完整日記,至少可仿效今人對(duì)清代李慈銘日記的整理,從中清理出涉及讀書(shū)的部分,先勒為一編《越縵堂讀書(shū)記》。滿以為這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盛業(yè),是文人樂(lè)見(jiàn)其成的,不料此議被老韓斷然拒絕。碰了一鼻子灰后猶自在想,到得楊絳的歲數(shù),韓石山總不會(huì)也舍得一把火,將自己堆積成山的日記本燒個(gè)干凈吧?那到時(shí)又會(huì)如何區(qū)處呢?
【評(píng)】如何處理私人日記,本無(wú)須外人置喙。此中透露出楊絳對(duì)隱私的維護(hù),矜持和孤高仍舊一貫。然而,不是只有楊絳才在記日記,錢(qián)鍾書(shū)不也在記日記嗎?不錯(cuò),楊絳說(shuō)過(guò)“他開(kāi)始把中文的讀書(shū)筆記和日記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識(shí)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時(shí),他風(fēng)聞學(xué)生可檢查‘老先生’的日記。日記屬私人私事,不宜和學(xué)術(shù)性的筆記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記部分剪掉毀了”。但后來(lái)影印出版的《容安館札記》里,不僅不乏記“苗介立”等生活內(nèi)容的日記,而且有著多少口不擇言、臧否時(shí)人的言論啊。不恤出版丈夫?qū)θ说乃较略u(píng)議,卻不惜銷毀自己的日記,是否讓人感到有兩套彼此打架的標(biāo)準(zhǔn),在左右著楊絳的內(nèi)心?
實(shí)際上,出版筆記手稿是錢(qián)先生生前不會(huì)認(rèn)可的事情。硬著頭皮公之于世,固然不失為一種保存方式,避免了讓數(shù)量巨大的筆記從此湮沒(méi)于天壤間,但潦草的字跡影印推出,可能帶來(lái)誤讀誤識(shí)和以訛傳訛,這種毀不如存、存暗含毀的矛盾,是永遠(yuǎn)無(wú)法調(diào)和的。看透了這層后,用火攻之法對(duì)待自己的日記而片紙不留,委實(shí)就顯得沒(méi)太大必要了,反容易引發(fā)后人不盡的猜疑。倒莫若從容坦誠(chéng)地留下它,庸何傷?
怪舉三:對(duì)甲說(shuō)“你正確”,轉(zhuǎn)身對(duì)乙說(shuō)“甲不正確”。
【注】先看錢(qián)先生當(dāng)年的同事、文學(xué)主體性理論的提出者追溯:
我一到那里,他就說(shuō),剛才××到這里,認(rèn)真地說(shuō),《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xué)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qián)先生顯得很高興。……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后就主體性的爭(zhēng)論,他談了兩點(diǎn)至今我沒(méi)有忘卻的看法。……他說(shuō),“批評(píng)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guò)是下邊遮羞的樹(shù)葉子。”……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qián)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xué)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xué)生弄得走樣了。”(《紀(jì)念錢(qián)鍾書(shū)先生》)
如上表明,錢(qián)鍾書(shū)對(duì)這位朋友甲的文學(xué)主體性理論、以這一理論為觀念指導(dǎo)而寫(xiě)成的暢銷書(shū)《性格組合論》、以及推動(dòng)了全國(guó)“方法論熱”的《文學(xué)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一文,都持肯定態(tài)度。再聽(tīng)錢(qián)氏在同一時(shí)間對(duì)當(dāng)年同事乙所說(shuō)的話:
先生說(shuō):我看到一些文章,錯(cuò)誤太多,一知半解。我看你們研究室(我當(dāng)時(shí)在文藝?yán)碚撗芯渴遥┖芑钴S,就一篇關(guān)于主體性的文章說(shuō)了不少意見(jiàn),真是,文章經(jīng)不起推敲,這可是不行的呢!(《“我們這些人實(shí)際上生活在兩種現(xiàn)實(shí)里面”——憶鍾書(shū)先生》)
此處“就一篇關(guān)于主體性的文章說(shuō)了不少意見(jiàn)”云云,指刊于《文學(xué)評(píng)論》1986年第3期、后收入《文學(xué)主體性論爭(zhēng)集》的《自由地討論深入地探索》等文章。被提“意見(jiàn)”的,就是上面甲的文章。鑒于批評(píng)意見(jiàn)占了很大比重,這又顯示,錢(qián)鍾書(shū)迅速收回了剛才對(duì)甲的肯定,轉(zhuǎn)而埋怨其“文章經(jīng)不起推敲”——你看得懂這種態(tài)度上的一百八十度轉(zhuǎn)彎嗎?
【鑒】前面的贊語(yǔ)是不是錢(qián)先生的客套?會(huì)不會(huì)后面的批評(píng)才體現(xiàn)了老人家的真實(shí)心聲?比較一下類似的情形,會(huì)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錢(qián)氏之贊語(yǔ),發(fā)生在書(shū)信往還中,尤其是對(duì)不熟的通信者。其身后大量披露的信札告訴我們,對(duì)這些人,錢(qián)鍾書(shū)往往不吝溢美之辭,鼓勵(lì)居多,確也給不少寫(xiě)信的崇拜者帶去了受寵之樂(lè)。可在當(dāng)面場(chǎng)合,錢(qián)氏褒貶起人來(lái),不見(jiàn)得有那么多虛套。上面兩個(gè)片段都涉及熟人,談不上口是心非的虛與委蛇,其間的矛盾便令人由不解而駭怪了。
【評(píng)】就此抱以“陽(yáng)奉陰違”之譏,是容易的卻也是平庸的。我感興趣的是這一怪舉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錢(qián)鍾書(shū)的深層性格:自己對(duì)自己的矛盾不甚敏感,自我反思不夠。有時(shí),我們覺(jué)得他對(duì)矛盾似乎很敏感,比如為鐘叔河主編的叢書(shū)作序時(shí)說(shuō):“走向世界?那還用說(shuō)!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但有時(shí)我們又覺(jué)得,他的說(shuō)法頗有矛盾,比如口口聲聲“打通”——“通”的就不需要刻意去“打”,靠“打”出來(lái)的“通”,那還是真“通”嗎?
或許也正因?qū)γ懿粔蛎舾校X(qián)著在整體上,便缺少一種以自我反思為核心的哲學(xué)深度,放眼望去盡以平行鋪排為主,缺乏正反交錯(cuò)、展開(kāi)辯證駁難的深入哲思。迄今哲學(xué)界罕有談他的,沒(méi)什么研究者將他的書(shū)作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必需取徑,是不是可以說(shuō)明一些問(wèn)題?往深處窺探,其實(shí)也很少有某個(gè)專題的研究者,把錢(qián)著奉為繞不過(guò)的參考文獻(xiàn)。他的書(shū)可看可不看,看了自可增添些知識(shí)的興味,不看,對(duì)研究專業(yè)問(wèn)題也沒(méi)啥損失。隨著時(shí)日的推移,我以為錢(qián)氏治學(xué)的某種局限恰恰就在這里。這和他重廣度明顯更甚于重深度,不能說(shuō)沒(méi)有聯(lián)系罷。
怪舉四:送客時(shí)忽然發(fā)問(wèn)“何所聞而來(lái)?何所見(jiàn)而去?”
【注】事見(jiàn)劉永翔懷想近四十年前拜謁錢(qián)府的文章。前面都正常,有點(diǎn)古怪的一幕發(fā)生在賓主告別之際:
最有趣的莫過(guò)于臨別之時(shí)了。先生突然問(wèn)我:“何所聞而來(lái)?何所見(jiàn)而去?”我知道,這是鐘會(huì)去見(jiàn)嵇康時(shí)嵇康問(wèn)鐘會(huì)的一句話。若照抄鐘會(huì)原話“聞所聞而來(lái),見(jiàn)所見(jiàn)而去”來(lái)作答,豈但拾人牙慧,不是還自比陷害嵇康的鐘會(huì)了嗎?因此我笑而不答。(《受知記遇——回憶與錢(qián)鍾書(shū)先生的緣分》)
這里錢(qián)氏驅(qū)遣的典故并不陌生。三國(guó)時(shí)鐘會(huì)不認(rèn)識(shí)“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邀人同去尋訪。正巧碰上嵇康在大樹(shù)下打鐵,并不停下,旁若無(wú)人。待鐘會(huì)起身要走,嵇康才問(wèn)他:“聽(tīng)到了什么才來(lái)?看到了什么才走?”鐘會(huì)只能回答:“聽(tīng)到了所聽(tīng)到的才來(lái),看到了所看到的才走。”各種錢(qián)鍾書(shū)訪問(wèn)記中,記敘錢(qián)家大門(mén)難進(jìn)的很多,鮮見(jiàn)描寫(xiě)辭別之際細(xì)節(jié)的。這段文字難得地為之留下了風(fēng)采。只是這樣一種辭別語(yǔ),怕夠客人猜詳一輩子而不得其解了。
【鑒】在這個(gè)場(chǎng)景用這個(gè)典故,要表達(dá)什么意思?用鐘會(huì)欲害嵇康,比擬于劉對(duì)錢(qián)的“拜之倒”?把遠(yuǎn)道而來(lái)的后學(xué)說(shuō)成加害自己的鐘會(huì)?但自己熱情相待的行為迥異于嵇康,又無(wú)修辭上的對(duì)應(yīng)性,缺乏相似點(diǎn),比喻不當(dāng),好像也不能說(shuō)是想反諷什么。這算錢(qián)氏幽默?
溯自十余年前,我曾研究過(guò)錢(qián)氏幽默的幾種類型,發(fā)現(xiàn)多數(shù)幽默效果是運(yùn)用比喻實(shí)現(xiàn)的,如形容漢賦的“板重”為“以發(fā)酵面粉作實(shí)心饅首”,嫌唐朝和尚拾得論禪啰嗦有如“老婆舌”,稱韓愈老是話剛出口便反悔,“匹似轉(zhuǎn)磨之驢”,梅堯臣的以文為詩(shī)“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湯泡干飯”,清人錢(qián)載的詩(shī)則像“肥老嫗慢膚多褶”,如是等等。少數(shù)幽默效果則來(lái)自反諷,像抗議醫(yī)院里吵鬧的小護(hù)士:“你把我的病都嚇跑了!”唯獨(dú)吃不準(zhǔn),這從原文里掐頭去尾截割出來(lái)的一句“何所聞而來(lái)?何所見(jiàn)而去”,唱的是哪出幽默?思來(lái)想去,也只能叫它“斷章”了。淡化上下文語(yǔ)境而“斷章”為我所用,事實(shí)上正是錢(qián)鍾書(shū)特有的說(shuō)話和為文方式。
【評(píng)】“斷章”本身不是沒(méi)有可取點(diǎn)。《左傳》就總結(jié)了春秋時(shí)“賦詩(shī)斷章”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再聯(lián)想到漫漫科舉制長(zhǎng)河中那一道道試題,譬如“維民所止”,每每也在斷章中截搭,對(duì)錢(qián)鍾書(shū)這份癖好,自可見(jiàn)怪不怪。卞之琳還有名詩(shī)《斷章》呢。將之用于日常生活,開(kāi)開(kāi)玩笑則可,可是錢(qián)鍾書(shū)把它大剌剌地用到學(xué)術(shù)研究上去,竊以為卻是問(wèn)題很大,甚至充滿了危險(xiǎn)的。
舉個(gè)例子。對(duì)德國(guó)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的名文《藝術(shù)作品的本源》,錢(qián)鍾書(shū)“斷章”截取出一句“真理即非真理”,然后用“亦見(jiàn)亦隱”四個(gè)字,聯(lián)想式地迅速打發(fā)了它。這不但沒(méi)有詮釋清楚海氏原文之意,只同義反復(fù)了一下,而且在“斷章”的拼接中造成了三個(gè)不良后果:其一,把哲學(xué)本體論問(wèn)題偷換成“見(jiàn)/隱”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問(wèn)題,簡(jiǎn)化了思想語(yǔ)境;其二,海氏原文講的是“有”和“無(wú)”這對(duì)范疇在本體論上的關(guān)系,“無(wú)”在此是絕對(duì)的,錢(qián)鍾書(shū)卻用“見(jiàn)”和“隱”置換兩者,沒(méi)有考慮到,“隱”只是相對(duì)于“見(jiàn)”的暫時(shí)遮蔽狀態(tài),把一樣?xùn)|西藏起來(lái)讓人看不見(jiàn),這樣?xùn)|西仍在,并沒(méi)有趨于哲學(xué)上的“無(wú)”,以此類比,便從根本上導(dǎo)致了對(duì)這句哲學(xué)表述的義理曲解;其三,“亦見(jiàn)亦隱”在切換頻率上的穩(wěn)定性,又逐漸凝固成不變的同一性實(shí)體,那種形而上學(xué)嫌疑,恰是海德格爾此文試圖避免的,他要還原的“無(wú)”乃是一種非同一的差異——大道從中涌出的事件性發(fā)生源。你看,僅僅基于這三點(diǎn),靠“斷章”搞研究的短板不是已歷歷可辨嗎?
因?yàn)椤皵嗾隆碑吘故乔艾F(xiàn)代的文化現(xiàn)象,若據(jù)此信心滿滿地把治學(xué)當(dāng)作聰明有余、實(shí)績(jī)有限的跳躍式變奏和詩(shī)性活動(dòng),是容易撿了芝麻丟了西瓜,而難以長(zhǎng)久的。乍一看五湖四海、滿目琳瑯,一旦窮形極相,卻到底說(shuō)出了什么呢?它不能和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精神對(duì)話。從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精神看,符號(hào)需要置身于符號(hào)關(guān)系中,在和所有其他符號(hào)的區(qū)分中才有意義。一句話的意義,因而無(wú)法脫離它所處的整部作品,孤立地把這句話拎出來(lái)去和別的話拼接,便失去了對(duì)這句話刨根問(wèn)底的專業(yè)化深研姿態(tài),成為漂浮于話語(yǔ)效果水面上的自指游戲,真理便要打個(gè)折扣了。
于是可以理解,同樣是對(duì)疑難字詞作解釋,雖然錢(qián)鍾書(shū)的《管錐編》知名度大于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今天的人們卻似乎相對(duì)淡化了對(duì)于前者的熱情,而正在給予后者越來(lái)越高的評(píng)價(jià)——“永垂不朽,堪稱萬(wàn)世楷模”(魯國(guó)堯語(yǔ))。個(gè)中奧妙,我想在于錢(qián)氏在“斷章”中連類比附,思維上是橫向輻射的,百科全書(shū)式面面俱到,卻難免東點(diǎn)一下、西點(diǎn)一下;蔣氏則咬住每個(gè)對(duì)象本身深鉆細(xì)錐,思維上是縱向一竿子通到底,更趨專精的,其書(shū)終成敦煌學(xué)領(lǐng)域人人案頭必備之書(shū)。時(shí)過(guò)境遷來(lái)衡量,更為徹底、對(duì)學(xué)界更有助益的是蔣著而非錢(qián)著。據(jù)蔣夫人回憶:“我和云從(按:即蔣禮鴻)對(duì)錢(qián)鍾書(shū)先生有些‘微詞’,……如果他確是中文系的,那就確是有點(diǎn)‘雜’了!……他的博是驚人的,我老伴對(duì)他有些‘微詞’。”(《蔣禮鴻與錢(qián)鍾書(shū)鮮為人知的交往》)具體有何“微詞”,后人已不得而知,但估計(jì)和蔣對(duì)錢(qián)“斷章”的、東鱗西爪的治學(xué)方式的看法,多少有關(guān)系吧。熱衷于學(xué)界佚聞的有心人,何妨沿此來(lái)做做鉤沉的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