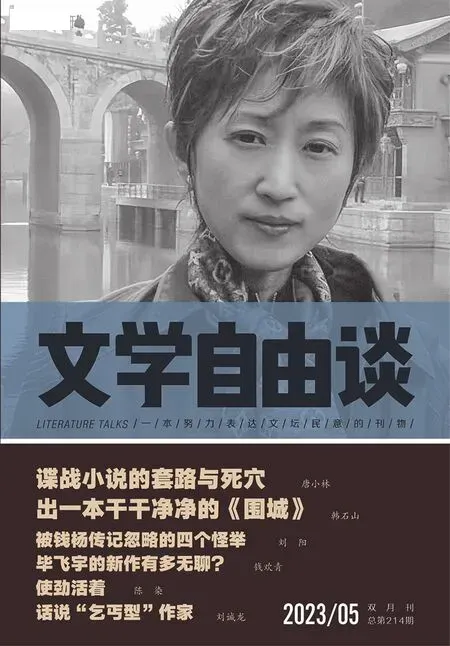林林總總名人傳
□劉世芬
這些年,每遇寫(xiě)作瓶頸,便有知心者建議:多讀作家傳記吧,最好是那種名動(dòng)世界的大作家。我當(dāng)即采納。某天盤(pán)點(diǎn)書(shū)架,傳記竟占據(jù)越來(lái)越多的地盤(pán)。好在我也不曾冷落它們,虔誠(chéng)恭敬,反復(fù)研讀。心有所得,在此分享一二。
名作家為名作家作傳,什么體驗(yàn)?
茨威格,羅曼·羅蘭,林語(yǔ)堂……某日,我竟發(fā)現(xiàn)這些大作家同時(shí)又是傳記作家,他們鎖定的傳主也皆盛名灼灼。
比如當(dāng)年讀《約翰·克利斯朵夫》,掩卷之下,意猶未盡,羅曼·羅蘭的生平及內(nèi)心世界成為極欲探究的謎窟。于是匆忙中下單《羅曼·羅蘭傳》。書(shū)到手,才留意到,作者居然是茨威格。
茨威格也寫(xiě)傳記?不過(guò),真正的意外卻是:讀《羅曼·羅蘭傳》,全無(wú)此前讀茨威格小說(shuō)隨筆時(shí)那種強(qiáng)烈的愉悅體驗(yàn),竟讀不下去。
這才新奇。正欲自我檢討,隨之發(fā)現(xiàn)茨威格的傳記作品不止于此,還有《三大師》《六大師》以及《自畫(huà)像》等。稍加思索,再下單《六大師》。
《六大師》由《三大師》中的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加上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合成,依然“讀不下去”。傳記中,茨威格的語(yǔ)言承襲了他的小說(shuō)隨筆,儼如連珠炮,那語(yǔ)速,那文法,那氣勢(shì),放在《象棋的故事》《馬來(lái)狂人》《心靈的焦灼》中,多么鮮靈生動(dòng),《人類(lèi)群星閃耀時(shí)》《昨日的世界》多帶勁。可是用于傳記,難道他想展示自己的腹笥豐贍?可為何讓人覺(jué)得濃妝艷抹、搔首弄姿呢?又仿佛大象與小兔的雜交,不得要領(lǐng)的“四不像”。至此,我明白為何此前長(zhǎng)期忽略茨威格的傳記,是否在他的小說(shuō)散文面前,傳記已為他“減分”?前半部大多介紹作家生平,后半部則解析作家代表作,看不出人物成長(zhǎng)的脈絡(luò)、軌跡。當(dāng)然,這種寫(xiě)法倒無(wú)不可,毛姆寫(xiě)作家們的評(píng)傳手法也多類(lèi)似,只是在茨威格這里,總是他一個(gè)人在那里自顧自喋喋不休,高談闊論,雜亂的堆砌感往往令人不知所云。
為進(jìn)一步印證,索性又讀《自畫(huà)像》(即《三作家傳》):托爾斯泰,司湯達(dá),卡薩諾瓦。翻閱之下,風(fēng)格一致,感覺(jué)如故。茨威格放得開(kāi),如洪水激流,汪洋恣肆,不像是在寫(xiě)傳記,而是演講臺(tái)上的自我抒發(fā)。大段的粉飾雕琢,沖淡了傳記的應(yīng)有內(nèi)核,弄粉調(diào)朱之處,就顯得極多贅筆。
之后讀羅曼·羅蘭的《名人傳》,也遭遇同樣尷尬——他們都把小說(shuō)筆法平移到傳記寫(xiě)作。這讓我極為撕裂、震驚:羅曼·羅蘭可是我熱烈崇拜的作家啊!以至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不能理清這種思緒:同一作家,《約翰·克利斯朵夫》令人心心念念,久久震撼,恨不得一讀再讀,為何讀《名人傳》卻截然相反?
還有更奇葩的:由于我正準(zhǔn)備即將成行的歐洲“文學(xué)游”,特意讀了《夏洛蒂·勃朗特傳》,竟經(jīng)歷了與茨威格和羅曼·羅蘭相近的體驗(yàn),冷硬,生澀,幾欲放棄。
初讀,封面上以三“最”概之:“這部傳記早已被公認(rèn)為英國(guó)最偉大的傳記之一,而且也屬英國(guó)最有成就的小說(shuō)家之一蓋斯凱爾夫人的最佳作品。”我雖說(shuō)服自己不被“三最”先入為主,讀后失望卻是事實(shí)。在我眼里,這本書(shū)極不成功,蒼白,無(wú)趣,甚至味同嚼蠟。與茨威格相反,這位夫人給人的印象是“放不開(kāi)”,為傳記而傳記,特別是大量書(shū)信引用(超過(guò)半數(shù)),形成作者與傳主彼此互證之嫌。
本來(lái),名作家為其他名作家作傳,這本身多么值得期待?當(dāng)初正是好奇名作家筆下不同凡響的“這一個(gè)”,哪怕成為“不同”甚至“另類(lèi)”,也不枉“著名”啊!結(jié)果卻成為“好奇寶寶”鎩羽而歸。
同樣“讀不下去”的還有林語(yǔ)堂的《蘇東坡傳》。或許從英語(yǔ)翻譯而來(lái),經(jīng)歷了二手創(chuàng)作,我只能勉強(qiáng)自己閱讀。
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我就在這種矛盾且復(fù)雜的閱讀體驗(yàn)里久久沉浸,最后嘗試自我說(shuō)服:每個(gè)作家是否并不都適合涉足新文體?是否應(yīng)把一口井掘到極致,并力爭(zhēng)水質(zhì)最佳?
是的,該請(qǐng)出《毛姆傳》了。
到底是玩過(guò)月亮的人,一枚月亮讓毛姆既玩轉(zhuǎn)世界,同時(shí)又給世人提供了“把玩”他的諸多機(jī)會(huì)——不信你瞧,算上毛姆畫(huà)傳,我收藏的毛姆傳記的中譯本共計(jì)七個(gè)版本,若把英文原版和中文繁體版統(tǒng)計(jì)在內(nèi),就是九個(gè)。從48萬(wàn)字皇皇巨著,到幾萬(wàn)字的少兒讀物,被我翻爛的有兩本:特德·摩根的和賽琳娜·黑斯廷斯的。無(wú)論語(yǔ)言還是情節(jié),首先是“好讀”;我并未關(guān)注二位是否為“傳記作家”,至少他們的版本鏤金得當(dāng),鋪翠有致,疏密有度,讓人如沐春風(fēng),并準(zhǔn)確傳達(dá)了毛姆的一生。有時(shí),兩本傳記互為映照補(bǔ)充,成為我欣賞毛姆生平最權(quán)威最精準(zhǔn)的資料來(lái)源,在我這里,大抵上可稱(chēng)傳記天花板了。
其他幾個(gè)版本也各有千秋,幾乎都把毛姆的人生呈現(xiàn)出共同特點(diǎn):文學(xué)成就驚人,又是“享受大師”;超級(jí)驢友,“生活在行李上”;樂(lè)觀向上,輕松詼諧,同時(shí)毒舌尖刻,視幽默感為生命。并且所有毛姆傳記都給出一個(gè)道理:當(dāng)你不為生存去做一件事的時(shí)候,才能做到極致。
平時(shí)我混在一個(gè)毛姆讀書(shū)群,有文友看到我收藏了黑斯廷斯的英文版《毛姆傳》,驚道:能讀原版,真牛!
自然沒(méi)那底氣。只是有一個(gè)特別的橋段:讀過(guò)毛姆《一位紳士的畫(huà)像》,我在群里與文友探討毛姆是否到過(guò)首爾,就有一位骨灰級(jí)毛粉告訴我:毛姆從中國(guó)回歐洲時(shí),就是從沈陽(yáng)經(jīng)朝鮮半島再到日本乘船,路線是:奉天—安東—新義州—首爾—釜山—馬關(guān)—東京。問(wèn)他出處,答“英文版《毛姆傳》”!并指出具體頁(yè)碼。我立即動(dòng)用英語(yǔ)世界的所有人脈,最終一位僑居加拿大的朋友為我買(mǎi)到這本英文版。
黑斯廷斯的中文繁體版《毛姆傳》則是一位朋友去東南亞旅行時(shí)帶回。繁體版的封面采用老年毛姆大頭像,占據(jù)整個(gè)畫(huà)面;底版幽黃,古意悠悠,所呈現(xiàn)的意蘊(yùn),一下子將人拽到百年前毛姆的馬來(lái)亞歲月,以及他帶給世界的婆羅洲風(fēng)情。事實(shí)上,當(dāng)我把簡(jiǎn)繁兩本掂在手中,仿佛“雌雄同體”,兩個(gè)封面散發(fā)的不同情味,包括大量字詞的差別用法,無(wú)不透射出一個(gè)別樣的華語(yǔ)世界,其人文意象如汩汩江水,遍地流漫,引得內(nèi)心頻掀波瀾。
盡管我并不因《巨匠與杰作》就把毛姆定義為傳記作家,但又必須承認(rèn),毛姆所做的人物評(píng)傳,包括《隨性而至》《觀點(diǎn)》中的部分人物,著實(shí)好讀、耐看,且對(duì)得起時(shí)間。
我讀過(guò)兩遍以上的作家傳記,有毛姆、雨果、奧威爾、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當(dāng)然,它們中的大部分,就沒(méi)毛姆這般妖嬈有趣卻又意韻深邃。
我手中的雨果傳記有兩個(gè)版本:莫洛亞《雨果傳》和葛麗娟《法蘭西詩(shī)神》。僅論厚度,前者是后者的五倍。二者皆可讀,忠實(shí)再現(xiàn)了雨果澎湃跳宕、坎坷滯重的一生,并傳達(dá)出他那不可泯滅的花心、政治野心以及感天動(dòng)地的悲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版本眾多,我讀過(guò)三四個(gè)。有的讀之不暢,只能翻閱速讀。印象深刻的有兩個(gè):安德里亞斯·古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和曾嘉的《煉獄圣徒》。特別是后者,是“世界十大文學(xué)家”(包括莎士比亞、雨果、海明威、杜甫等)叢書(shū)中的一種,我索性下單全套。十位作者,角度別致,給人全新的收獲和感受。閱讀過(guò)程中,結(jié)合此前讀過(guò)的其他版本,更易獲得完備體驗(yàn)。比如雨果、莎士比亞和陀氏的傳記,作者都為一外一中,容量也是一厚一薄,兩相對(duì)照,相得益彰。陀氏的精神困頓、對(duì)犯罪的迷戀,雨果的矛盾人生,莎士比亞的精靈般的才思與難以遏止的好色,經(jīng)不同作者之手,情味盎然,余韻悠悠。
最為沉重的,還是奧威爾傳。作為《一九八四》《動(dòng)物農(nóng)場(chǎng)》《倫敦巴黎落魄記》的延伸閱讀,下單傳記時(shí),竟遇到兩本書(shū)名“雷同”的書(shū)——《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和《冷峻的良心——奧威爾傳》,作者分別為美國(guó)人杰弗里·邁耶斯和中國(guó)人押沙龍。同一傳主不同作者太正常,但同一傳主書(shū)名“撞車(chē)”,卻是不同作者,不尋常,我急欲探個(gè)究竟。
兩書(shū)到手,相較之下,欣喜萬(wàn)分:兩書(shū)各有千秋,儼如釵黛,兩山對(duì)峙,二水分流。奧威爾的生平是固定的,同樣的伊頓童年,同樣的緬甸歲月,同樣落魄的巴黎倫敦,同樣“老大哥在看著”的BBC,同樣凄寒的朱拉島……來(lái)到二人筆下,就有了不同樣貌,卻一樣“驚美”——不是精美,也不是驚鴻。
沉重的,在于傳主本人。奧威爾與羅曼·羅蘭、茨威格、馬洛伊·山多爾等均為同類(lèi),是一種良心的代表。為追求文學(xué),放棄了警察職業(yè);在巴黎、倫敦流浪四年,乞丐、洗碗工都是他的標(biāo)簽;當(dāng)他的文名終于被世界接納,肺結(jié)核卻耗盡了他的生命。《一九八四》在病榻上寫(xiě)就,咳血,哮喘,醫(yī)生屢屢沒(méi)收他的打字機(jī),他只能偷偷寫(xiě)在紙上。好在,他離世前半年,《一九八四》付梓。只有讀過(guò)奧威爾傳,才知他的良心浸透了鮮血,讀之,淚流滿(mǎn)面。
同樣令人惋惜的,還有洛特曼的《加繆傳》。前半部尚可,到了后面,簡(jiǎn)直成了加繆的政治生涯概述。他雖與奧威爾有著同樣的政治良心以及參軍報(bào)國(guó)之志,無(wú)奈肺結(jié)核堵住了這條路;當(dāng)然,尚有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支撐。只是,當(dāng)他殞命于一場(chǎng)莫名其妙的車(chē)禍(有傳聞?wù)f,正因?yàn)樗^(guò)度參與政治,而被蓄意陷害),不由得令人扼腕:倘若上天多給他一些時(shí)日,《第一個(gè)人》定能完成,才華的落地,或許能夠奪回因政治損失的文學(xué)時(shí)間。
在這些傳記中,大仲馬是個(gè)例外。莫洛亞的《大仲馬傳》,自始至終讓我爆笑不止,以至我煩了累了就翻開(kāi)這本書(shū)。我覺(jué)得作者的筆法倒在其次,大仲馬本身就是個(gè)大活寶,每個(gè)細(xì)胞都塞滿(mǎn)笑料。
《康德傳》是我讀的唯一一本哲學(xué)家傳記。本來(lái)對(duì)哲學(xué)望而生畏,沿著毛姆的《對(duì)某本書(shū)的思考》,康德的生活片斷引導(dǎo)我探究其生平。也有獵奇:毛姆這個(gè)資深驢友,如何欣賞一個(gè)固守在出生地的人?
這本《康德傳》53.4萬(wàn)字,“啃”起來(lái)頗為艱深晦澀。不過(guò),我終于發(fā)現(xiàn)了康德死守哥尼斯堡(現(xiàn)為俄屬加里寧格勒)的真相:他分別在1769 年、1770年、1778年拒絕了埃爾蘭根大學(xué)、耶拿大學(xué)和哈勒大學(xué)的高薪高職聘請(qǐng),理由是“生命能量有限”,哥尼斯堡的社交生活也讓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此外,康德雖拒絕這三次遠(yuǎn)足,但若說(shuō)他從未離開(kāi)哥尼斯堡也不對(duì)——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曾離開(kāi)哥尼斯堡城區(qū),去鄉(xiāng)鎮(zhèn)當(dāng)過(guò)家庭教師,先后受雇于阿倫斯多夫、于特申以及凱澤林克等鄉(xiāng)鎮(zhèn)的各類(lèi)家庭,距離主城區(qū)百公里之內(nèi)。當(dāng)然,從行政區(qū)劃的意義上,這些鄉(xiāng)鎮(zhèn)都受轄于哥尼斯堡,也因此,后人認(rèn)為康德一生從未離開(kāi)哥尼斯堡,也不算錯(c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