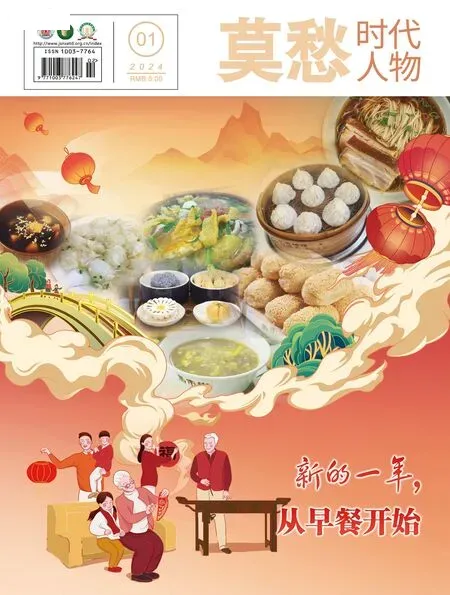世間花草會療愈
文夏麗檸


千萬不要以為“治愈”故事只發(fā)生在電影中。蘇·斯圖爾特·史密斯的《花花草草救了我》讓我們知道,這一切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書中指揮家的故事,僅僅是成千上萬的“園藝治療”中的個案。作為英國精神學家、心理治療師,以及科普作家的蘇,在書中將“花花草草”的療愈方法,沿著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脈絡,說得清清楚楚,最終將我們引向“自然與人類關系”的永恒母題。
要想了解“園藝治療”,我們首先得對花園的存在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法國園藝大師阿蘭·巴哈東曾經這樣評價他創(chuàng)造的花園,“有心跳,有靈魂,是造園,也是造世界。”花園作為人類居所與外界喧囂世界的緩沖帶,是人們內心世界向外在世界的過渡空間,它的存在是有發(fā)展歷史可循的。亞當和夏娃即是伊甸園里最早的園丁。
在蘇眼里,“沒有照顧就沒有嬰兒,同樣,沒有園丁就沒有花園。花園永遠是一個人心靈的表達,是一個人付出愛心的成果。在栽花種草的過程中,要對‘我’和‘非我’進行清晰的歸類也是不可能的。當退后一步欣賞我們的成果時,我們能分得出哪些是自然的給予,哪些是我們的付出嗎?”莊子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無我”。花園,恰好提供了一個體驗“無我”的最佳場所,不斷付出,不問收獲。但大自然的獎賞,總是隨著四季更迭不期而至。盡管其中包括枯萎與新生,但我們仍然覺得這是平等的禮遇。園丁無法主宰花朵,只能不斷地給予植物關懷,而支撐這種關懷的動機,是對愛與美的向往。因此說,在園中栽培植物也是一種藝術。
但現(xiàn)代人不完全認可“園藝”的價值,“現(xiàn)代社會強調的是自我提升和自我投資,關心他人就好像一種自我的損耗,因為這要求我們把精力放在自己以外的人和事物上。”蘇認為,基于這個理由,絕大部分人不會將精力傾注于土地之上,而是鼓足干勁去參與社會和工作的競爭,導致精神壓力劇增,各種病灶出現(xiàn)。所謂的內卷,說的就是這么一回事吧。當人們在不經意間將大腦比喻成電腦時,也就說明我們離自然本性越來越遠。
利用花園和自然進行精神康復,于18 世紀的歐洲興起。當時在鄉(xiāng)村建立的精神病院,稱為“療養(yǎng)院”,就像現(xiàn)在的園藝治療項目里的病人被稱作園丁一樣。這種療法的好處在于,一切都是建立在仁慈、尊嚴和尊重的基礎上。參加園藝活動的有抑郁癥和焦慮癥患者,有服刑的犯人……總之,希望喚起心中新生種子的人都可以加入進來。他們所做的是與自然合作,拒絕對抗自然。
如果我不是“病人”,我不需要治療,那么我是否需要花園?答案是肯定的。簡單來說,綠色帶給人一種安全感,讓人感受到庇護的力量。比如唐代的王維是避世者,他躲避戰(zhàn)亂是一種自覺的防御行為。而東晉陶淵明,就比王維幸福一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展示的是陶淵明對農事的熱愛,有重新融入生活的感覺。生命與自然,由此產生了新的關系。
如果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那么自然就是唯一的懷抱。愿我們都能成為自然之子,在母親的懷抱里汲取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