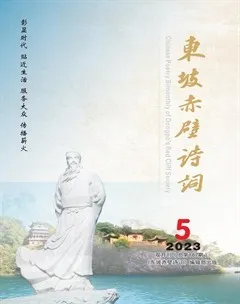詩心萌發在田園
周峰光
詩心萌發在田園,除草施肥何所偏。
不管收成豐與歉,精耕巧作一年年。
——題記
我的童年,在我的生活軌跡里,有一筆重彩,是寫在美麗的鄉下。那時,父母常年工作在外,我只好生活在外公外婆的家里。所以,自幼受外公外婆的照拂,并陪伴我長大。多年來,鄉下的見聞,讓我有了田園生活的經歷。詩芽,大概是種在那個時候吧。
上學后,我離開了鄉下。但家鄉的一山一水、一磚一瓦、一田一地、一草一木,均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我眷戀故鄉,常常流連忘返,以致數十年后,依然魂牽夢繞。盡管青山依舊,田園依舊,可外公外婆,卻早已去世。每年的清明,我必定回去祭拜二老。當我走在昔日鄉間的小道上,總想尋找一絲慰藉。惟于此,靜下心來去細細體味,此心安處,尤感鄉間的親切。
或許是,從小受父親影響,受中醫湯頭歌的熏陶,加上對文字情有獨鐘,為表達心境,偶作打油一二。作為后學者,我于2018年8月正式接觸詩詞,并迷上中華詩詞那結構里的古香古色,那韻律中的悠遠典雅,頗有失之東隅、得之桑榆的感慨。父親的突然離去,如當頭一棒,我的天塌了,是詩詞給了我救贖,引我走出了陰暗。我的第一首處女作,是在父親離世當晚寫的,雖笨拙不堪,但詩芽悄悄萌發。從此,我如一頭饑渴的牛犢,心無旁騖,一頭扎進詩詞之山,汲取營養。從唐詩的多彩,到宋詞的婉約,無一不讓我心生歡喜,并心摹手追。
讀到田園詩詞,我體會李清照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時,看到荷塘月色,便寫下了《如夢令·荷塘》:“月色頻頻相顧,玉露輕輕憐撫。蛙鼓鬧池塘。唯有幽香不住。爭妒,爭妒,激起嫣紅無數。”品讀蘇東坡《浣溪沙·游清泉寺》詞時,就會想到聞名遐邇的清泉寺,就在我家附近,所以,讀來宛如身臨其境,倍受感動。2019 年5 月抗洪期間,親身目睹抗洪,步韻寫下了《浣溪沙·抗洪》:“南水北移轉作溪,千村萬樹裹洪泥。昏鴉不住對江啼。鐵骨錚錚無老少,煙樓泛泛日歸西。凱歌奏響聽鳴雞。”曾記得,外婆家的門前,有一條小溪,緩緩繞門前流過。溪水源于一口池塘,夏天一到,我們在池塘邊抓魚蝦,村里婦女手拿棒捶,在石頭上捶洗衣裳,鄰里之間和睦相處,小伙伴結伴嬉戲。農民伯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雖物質匱乏,日子貧窮,但過得非常愜意。排律《故鄉吟》,便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燕剪東風穿陌上,同花暫住接天梯”,是看到油菜梯田,如詩如畫的畫面,而想到與花同住田園。春耕時節,更別有一番風景,燕子歸來,布谷催耕,便寫了《春耕》:“乳燕雛鶯恰恰啼,云天布谷播聲宜。田頭一喝鞭長嘯,露潤風催春水犁。”是所見所感的結果。看到田頭插秧,聽到蛙聲四起,如同天兵布陣,于是便有了“十里蛙聲蕩滿田,低頭便啟水中天。秧針輕點云俱陣,是處新兵退向前”的詩句。
我喜歡親近田園,更喜歡花花草草。《小草》的“生來夾縫未迷茫,得雨乘風赴遠方。不羨飛花如是夢,扎根薄土亦輝煌”詩句,便是我這愛好所得。行走在田園里,看到飛舞的蜂蝶,于是便寫了“日與晨曦約會忙,吟花采蕊甚疏狂。足書小字貽深意,不錯平生一縷香”(《蜜蜂》)。看到嬌艷的海棠,便有了“欲借東風巧扮妝,深紅淺綠染霓裳。無因逗蝶憐蜂至,只把春心托艷陽”(《海棠》)。因鐘愛桂花,自然又寫了“手扶瓊枝對對排,神州又到問天街。人間已近重陽日,暈臉嬌羞釋夢懷(《桂花》)。行走于鄉村看蜜桃,陶醉其中,有了“望處深山綠意濃,長陰蔽日有情衷。含羞復見郎君面,暈上胭脂滿臉紅”(《水蜜桃》)。總之,一縷清風,一聲雨滴,一朵花開,都會引發我的靈感,都會激蕩我的詩情。不妨說,我的這些田園習作,既是田園的啟發,更是田園的饋贈。
2013 年12 月,為響應國家號召,我接到精準扶貧任務,到浠水魚塘角村扶貧,讓我有機會再次親近田園,看到農村。其間,我興之所動,寫了一組反映新時期農村題材的詩詞。《打工者》:“閉戶山前雀守家,村頭老樹望天涯。三年幾度無消息,路轉峰回一片霞。”《留守兒童》:“荒村冷灶犬圍爐,欲見慈親夢里呼。日歷翻刪何所剩,一年好聚幾天無。”《留守婦》:“鴛衾不減雪風寒,弱女更深倚月眠。好夢成真千里外,嬰兒揉碎一方天。”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通過產業扶貧、疾病救助、稅費減免等諸多政策扶持,一些家庭生活得到了改善。2022 年11 月11 日,我又到鄉村振興示范村參觀,隨之留下了《鷓鴣天·壬寅初冬走進蘆河村》:“樂訪城郊見古風,白墻黛瓦世情濃。拈來日月情無盡,行處桃源夢欲同。分墨色,合秋容。村中院落露花叢。酒香陣陣留賓客,報道今年五谷豐。”
“久住桃源心境遠,情牽世上浥輕塵”。從邯鄲學步,到東施效顰,一路走來,我深知自己文學功底淺薄,詩詞尚不夠成熟。我相信只要有詩心在,只要有師友的幫助,我會勇往直前,未來不會迷茫。我仍然會從田園出發,乘風破浪,奔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