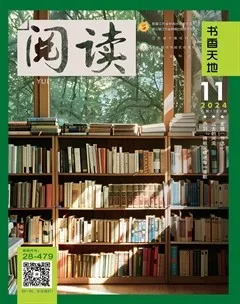繁華如夢: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


兩宋時期,繪畫創作主要有民間、文人士大夫和畫院職業畫家三個群體。民間畫家畫風樸實自然,題材廣泛,貼近現實生活;文人畫家則以寫意為先,講究筆墨情趣,抒發個人情懷,注重意境的表達;畫院職業畫家多追求嚴謹工細、造型準確、色彩華麗。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風格,呈現出宋代繪畫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時,這些畫家群體之間又相互交流借鑒,職業畫家畫作的精湛技藝與文人畫作的思想意境彼此滲透融合,取長補短,文人畫作的技藝水平與職業畫家畫作的藝術境界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鳥畫在題材的廣泛性和藝術水平上已經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產生了眾多杰出的繪畫藝術家以及大量的曠世畫作,對元、明、清以及現代繪畫形成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如此的輝煌與榮耀之中,無論是繪畫藝術水平,還是繪畫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繪畫作品的影響力方面,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都處于絕對的中心地位。如果說宋代是中國文人畫的第一個里程碑,那對于中國古代畫院以及院體畫來講,宋代則已經成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雖然明、清兩代也建有類似的畫院,但在畫院的建制規模和藝術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兩宋時期。
一
根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宋代已經完成了由貴族門閥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型,加上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平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隨之增加,尤其是對包括書畫在內的藝術品更是渴求。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下,大量民間畫家應運而生。
這些民間畫家們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繪出一幅幅生動逼真、引人入勝的人物、山水、花鳥圖畫,在大街小巷擺攤出售,換取柴米油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技藝精湛,名聲也很響亮。如擅畫小孩的杜姓畫家被百姓們稱之為“杜孩兒”,擅長樓閣亭臺的趙姓畫家則被譽之為“趙樓臺”,而他們的真實名字卻被淹沒在浩瀚的歷史長河里,反而不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有一座大相國寺。說起這個大相國寺,在那時可是大大有名。《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花和尚魯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園子當過臨時主管,還在那里練過倒拔垂楊柳的功夫。
大相國寺始建于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國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賜名該寺為“大相國寺”。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的規模達到了頂峰,占地540畝,有64禪律院,僧眾達數千人,寺內還有大量的佛教壁畫,香火極為旺盛,是當時全國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廟。除此之外,大相國寺還是帝都汴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大相國寺每月都有五次廟會,廟會上人流熙攘,交易興隆,不僅有各類生活、文化、宗教用品,還有大量民間畫家銷售的圖畫攤點,逶迤蜿蜒如一條長龍,使人目不暇接,其繁華程度絲毫不亞于當今北京的琉璃廠。
由于生意興隆,有利可圖,大量畫商也隨之出現。當時,一些著名畫家的畫作價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錄》中說:崇寧年間,徐熙的一幅《牡丹圖》,有人出價二十萬;《洞天清錄》也提到:江西人楊補之的一幅梅花“價不下百千金”;《圣朝名畫評》中記載:大中祥符年間,一個名叫丁朱崖的官員為了求得著名畫家趙昌的畫作,借賀壽為名給趙家送去五百兩黃金。
二
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建于何時?美術史家歷來有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建于宋太祖時期,其依據是《圖畫見聞志》中的一段記載:晉末時,畫家王靄與王仁壽被契丹人擄去,宋太祖登基后二人被放回,在圖畫院任祗候。另外,據《圣朝名畫評》中所載:西蜀被滅后,其宮廷畫家們被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圖畫院中的。
另一種則認為,畫院應該始于宋太宗趙光義雍熙元年,理由是《宋會要輯稿》所載:“(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圖畫院。在內中池東門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門外。”根據這一記錄,北宋“翰林圖畫院”正式掛牌成立應是公元984年。
“翰林圖畫院”的主管部門名義上是翰林院,實際上卻是由內侍省負責畫院的具體工作。據《宋史·職官志》以及《宋會要輯稿》記載:“翰林圖畫院”成立之時,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員負責管理畫院,而這名官員則是由內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擔任。內侍省相當于皇家事務管理局,負責宮廷的內部事務。內侍省下面還有“翰林書藝局”“翰林太醫局”“翰林匠作局”等與“翰林圖畫院”類似的部門,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藝人集中的地方。
畫院最初沒有定員,畫家的人員編制和職稱等級并不固定,宋仁宗時才開始正式設待詔三人、藝學六人、祗候四人、學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三
宋代數百年間,歷代皇帝們都給予了畫院畫家比較高的政治地位。他們分別被授以“翰林待詔”“翰林祗候”“翰林司藝”“內供奉”“畫學正”“學生”等職稱,穿戴官服,領取工資,享受著與現代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類似的待遇。
在內侍省中,還有一個單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稱之為“畫工”的人員,這些畫工與畫院畫家之間的身份地位差別是非常大的。據《畫繼·雜說》中記載:“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圖畫局和書藝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眾工待也。”畫工們的報酬叫生活費(“食錢”),畫院畫家的報酬卻被稱作工資(“俸值”)。一個“食錢”一個“俸值”,叫法不同,區別也很大。另外內侍省還有翰林書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這些局、院中,畫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這在《畫繼》中也有記載,“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為首,書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宋徽宗時期,由于趙佶對書畫情有獨鐘,還特別“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佩魚就是一種魚形的袋子,本是一種裝飾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員才能佩戴。宋代時一般賜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夠級別的官員以及皇帝的近臣,而武官、內侍等均不配發。畫院的畫家們能夠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難得的。此外,趙佶還打破了宋初以來朝廷技藝人員不得為官的傳統(個別情況除外),任命了不少畫家出任正式官員。
南宋高宗時期,畫院畫家的地位更是直線上升。出任官員的畫家數量更多,級別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工部侍郎。更為特別的是,很多畫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別賜予的“金帶”,所謂“金帶”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員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四
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為了培養高水平的繪畫人才,在“太學”之內興辦了“畫學”,以科舉考試的方法選拔學生。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南遷后的高宗、孝宗時期(公元1127—1189年)。“畫學”的興辦,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創辦的波倫亞學院——人們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美術學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據《宋史·徽宗本紀》和《宋會要輯稿》的記載:“畫學”設立之初由國子監管理,并設有專門的官員如博士、學正、學錄、學諭、學直等。其中博士大多由精通書畫的士大夫官員擔任,如禮部員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過“畫學”博士(院長)一職。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以后,朝廷對“畫學”進行了體制改革,國子監不再管理“畫學”,改由翰林圖畫院負責。
“畫學”的入學考試十分嚴格,有點類似于現在的美術高考。除了繪畫專業技能之外,還要進行文化考試。專業課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課則有《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
同“太學”的其他科目一樣,考生考試合格后方能進入“畫學”深造。整個流程從試卷封印、評卷、擬錄取名單、復審、注冊,直至張榜公布,都很規范、嚴謹。入學以后,學員的學習、生活費用則完全由官方承擔。
“畫學”的專業考試形式則很有意思,考題都是古人的詩句,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亂山藏古寺”“萬綠叢中一點紅”等,要求應試者在創作時不僅要貼題,還要有詩一般的意境,做到畫中有詩。其中某一次考題,據說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時的靈感,題目為“踏花歸去馬蹄香”。奪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畫面上僅畫了一匹奔跑的駿馬和數只蝴蝶在馬蹄后面飛舞追逐,便將考題的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了。
通過這樣的考試方式,進入“畫學”的學生不僅有良好的文化修養,還有很強的藝術創造力。譬如流芳萬世的《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在“畫學”學習以后,再由宋徽宗趙佶親自指導后出現的杰出青年畫家。
五
大宋的皇帝們一直都非常注重畫院人才的選拔,采取多種形式吸收畫家進入“翰林圖畫院”,凡是技藝高超的畫家不論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間高手因此也相繼進入畫院。
傳奇并非只屬于仗劍走江湖的俠客,同樣也屬于藝術家,對于李唐、蕭照師徒來說就是如此。
李唐(公元1066—1150年)河陽三城 (今河南孟州)人。詩文書畫門門精通,天賦極高。他先是以賣畫為生,徽宗政和年間(公元1114年)參加畫院殿試,以優異成績被畫院錄取。“靖康之變”后,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廚師、倡優等10余萬人被當作戰利品押往金國,李唐也沒能幸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備,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絆絆,受盡磨難,當行至太行山下時,不料卻被一伙強盜攔住了去路。強盜們打開他的行囊,不見任何財物,只有筆墨顏料以及幾幅畫作。正當李唐絕望之際,哪知峰回路轉,強盜中突然閃出一人,伏地便拜,頓時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當場。
此人自稱是業余書畫愛好者,名叫蕭照,宮廷大畫家李唐的名聲對他來說如雷貫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級偶像。名家就在眼前,豈能就此放過,當場就要拜李唐為師。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無奈之下,只好收下這位強盜徒弟。于是師徒二人告別山寨,南下臨安(今浙江杭州)。
經過長途跋涉,一路艱辛,兩人終于到了臨安。可是身處亂世,舉目無親,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舊業,又在大街上擺起了地攤。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正在街頭賣畫的李唐被宋高宗的舅父韋淵偶然遇見,時來運轉,李唐這才回到畫院任待詔,后來授成忠郎,賜金帶。浪子回頭的蕭照跟著師傅努力學畫,一段時間后畫藝大進,不久也被招入畫院,補迪功郎,賜金帶。一個攔路打劫的強盜改邪歸正,蛻變成為一個杰出的畫家,從此踏入藝術的殿堂。蕭照的華麗轉身,既展現了繪畫藝術的特殊魅力,也反映了畫院不論出身、唯才是舉的用人態度。
翻閱著陳舊泛黃的史料,回望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的發展歷程,我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絢爛與輝煌。中國古代畫院從五代時期的濫觴,到兩宋時期的繁榮興盛,既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也有上層統治者高度重視的因素。良好的創作環境,優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畫家們能夠心無旁騖地進行藝術創作,從而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畫家和繪畫藝術的經典之作,在中國美術史上寫下了極為華麗的一章。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