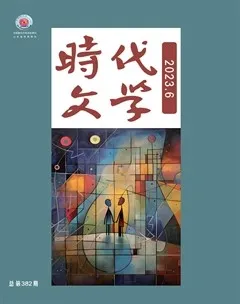小白
趙峰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前后五個村只有一個代銷點,在二里路外的北村。代銷點就兩間小房,很憋屈,貨架上的東西稀稀拉拉。可還是有一些饞死人的東西,砂糖、糖塊、五顏六色的糖球等,還有口蘇,來了就挪不動腿兒。村里男女老幼都愛來這里扎堆,這讓那小屋蓬蓽生輝。一到門口,好聞的醬油、醋、糖的味道就撲過來,小孩哈喇子流一嘴巴。雪花膏的濃香直往鼻孔里灌,讓人受不了,比吃一頓飯都享受。
村里的小學,就一個公辦教師,還兼著校長。那時,公辦教師家屬多半是農村戶口,還要在老家參加生產,不能帶出來,公辦老師就要自己開火做飯。他買醬油、醋、電池啥的,自己不跑,給錢讓我們輪番代勞。
去一趟代銷點,鼻子和眼都能過足癮,嘴也不吃虧,路上可以喝老師的醬油、醋。瓶里落下去的那塊空白,就順手在路邊的溝里撩幾把水,灌到瓶頸高度。水不能摻太多,兌太寡淡了,老師能嘗出來。
老師輕信我,便經常抓我的差,可我喝他的佐料從沒客氣過,有時也抹幾口甜醬。白跑路又不給錢,該吃!該喝!老師派人,一般是兩個,便于監督,但只要一起喝,就沒法相互告發。就是那次出來北村口,在石渠邊遇上了小白狗,后來我叫它小白。一見面,小白就萌萌地趴我腳面上,兩個小爪子亂扒拉,后來又緊緊抱住我的褲腳,像個撒嬌的孩子。這個小“自來熟”讓我心花怒放,覺得好像它在那里已等我好久。很多不期而遇,口不能言。當時,小白的奶胖勁還沒過去,像個大白毛線團。不知道是誰家小狗,四周望一下也沒看到大狗,逗弄它一會兒,我倆就連蹦加躥地跑回來。剛進學校,扭頭卻發現小白竟在后面尾隨了來,連滾加爬喘著粗氣,晃著圓圓的身軀。我內心頓時生出一股莫名激動,同去的同學看我,我也看他,束手無策了好一陣。同學家已有條“四眼狗”,他當即決定放棄,小白便無可爭議地歸了我。
狗小,目標也小,用書包裝上它,跟著我上了最后一節課,它竟然一聲沒吭。放了學,我把小白帶回了家,總算是有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狗。我養過羊、兔子、鴿子、貓,一直想養條狗。小白來家理所當然受歡迎,反正有剩飯,餓不著它,多個盆兒的事。小白安居下來,一家人都稀罕,有好東西先給它吃。趕上吃肉,也不會讓它看著,不只是給骨頭啃,我分到一塊肉要夾開一半給它。小白沒看家的任務,屋里屋外沒一件值錢的東西,想看也沒東西可守。所謂的大門形同虛設,很多人家都是隨便放幾根杠子、排幾個秫秸擋一擋了事。
每次放學,小白都會搖頭晃腦地到前街接我。我很在意這份禮遇,見面總是先抱它一會兒再玩,沒事也帶到街上、地里,跟我四處轉悠。它不亂跑,在我后邊亦步亦趨。生人抱,它不樂意,使勁掙扎著向我求援,像個怕被人抱走的孩子。
一次小白跟我上街,我突然發現它走路有些別扭,順拐。像是買回來帶裂縫的碗或是裝訂錯頁的畫本一樣,我興頭上被潑了瓢冷水,無疑,這是殘疾。順拐的人我見過,就是同一邊胳膊和腿一起動,擺臂也無法交叉。人順拐不怕,只是不協調,不好看。狗順拐,失重,瞬間要半邊身子懸空。我覺得很沒面子,小白成了最丑的狗,前街的宏說:“咋弄了個這么丑的狗!扔了算了,我給你一只。”我聽得出他話里的奚落和幸災樂禍。他家的狗剛生了一窩,很快就能抱出來。可小白我不能丟,丟了,成了野狗,整天靠打架為生,那就苦了,淪落在街頭荒野,都不一定死在哪兒。
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宏的慷慨饋贈,小白拿啥我也不換。
從那天開始,我割草回來,就掰著小白的腿練走路。小白并不順從,拗著勁和我唱反調,弄急了它還嘴里嗚嗚著發怒,像是抗議。我氣急了,打它幾下,它一臉委屈,眼里全是淚。直到多年后,我才真的懂了,改習慣,很難!但沒有白搭的工夫,一個月后,小白有了明顯好轉。
我去姥姥家,小白也非要跟著。我怕它走丟了,一個勁地往回攆,往返十幾次它還是粘著我不放。我只好把它關在一個放柴火的房子里,掩上門,才放心地走了。
姥姥家是山區,離我家十八里路,那一帶東高西低,過了公路就一路上坡。走到辛莊,我就累得夠嗆,口也渴得厲害,一屁股坐在地上,使勁呼哧粗氣。恰好路邊就有一條壟溝,水清見底,成群結隊的小魚蝦在水中游來游去。我蹲坐在溝邊,俯下身捧了水喝。我不經意地扭頭,居然看到小白就在不遠處,怯生生地和我對視。它有一絲尷尬,還有一絲慌張,好像怕我責備它擅自行動。一種莫名的暖流在我全身涌動,我幾步跑過去把它拉到懷里,在臉上蹭了好久。想想它費了多大勁才頂開兩扇沉重的門板,又費了多少心思,跟我一路躲躲藏藏,追隨至此。
它是我的好朋友!我心里一遍遍念著。后續發生的事,更能證實這一點。
快走出太和村時,從一戶人家大門里出來條黑狗,張著大嘴齜著牙汪汪地狂叫,著實嚇我一跳。我不大怕狗,可手無寸鐵,又穿著單衣,顯然不能冒失。狗怕彎腰!我一俯身,狗打個激靈,往后退了幾步。但見我兩手空空,黑狗更囂張,逼我越來越近。這時,小白像只箭迅疾閃過,又趁其不備,幾乎貼著黑狗的身子跑過去。小白跑起來姿勢矯健優美,像是劃了一條飄逸的白線。小白的大膽把我給嚇壞了,它和黑狗體型懸殊太大,要是被抓到,后果一定很慘。狗咬狗,都是下死口。黑狗遭到挑釁,臉上掛不住,反身去追小白。我趁機在柴火堆上抽了根木棍,拎著往前追。村口東是個場院,小白借一個柴垛和黑狗兜圈子。小白身子靈活,黑狗占不到便宜,幾次跌倒,滾得滿身是土。畢竟離了家門,黑狗的氣焰也明顯弱了,特別看我手拿棍子,更有些怯,不再戀戰,耷拉著尾巴,吊著一條腿跑回去。虛驚一場,我再次對小白刮目相看,小個頭的硬漢!我在心里給它豎大拇指。
姥姥家三面環山,進村只有一條路。山道讓小白很興奮,它一刻也不閑著,噌噌地躥一段路,便停下招呼我。平時它跟我在河汊縱橫的黃河灘區玩,沒見過這山嶺溝壑。它一會兒追翩翩飛舞的蝴蝶,一會逮胡蹦亂跳的螞蚱,一點都不覺得累。
帶小白串門很威風,像是跟了個衛士。多了它,一路很多趣事,忘了路途漫長。姥姥村里的狗淳樸好客,好像知道是親戚自遠路來,都遠遠地在門口或街上,搖尾和點頭,眼里全是友善,沒有一只狗找我們麻煩。
小白長成年了,卻沒有一般土狗的身量,也就比柴犬大一點,比秋田犬還小一點。整天廝守著我,形影不離。
小白之于我,越來越重要!
小白不在狗群里混,它除了跟我玩,就是在家恪盡職守。出門總是單溜,和其他狗保持著距離。
五爺爺沒少給它好東西吃,可五爺爺下地撿糞,它卻不跟著。看到糞筐,它本能地顯露出鄙夷,扭頭跑開,從不吃臟東西,都說它“妖調”。家里來了外人,它基本上不咬,只是寸步不離地盯著。本人若拿了東西走,它就在大門口攔著嗚嗚地叫,家里人得去解圍才行。
村里人說到小白,想褒說不出理由,想貶更挑不出毛病。我私下想,真正欣賞它的人可能就我一個。
大約五六年后,一個冬天的早晨,全家人正吃早飯。小白從外面跑回來,像是醉了酒,東一頭西一頭地亂撞,腦袋像個撥浪鼓,然后轉著圈滿地打滾,叫聲撕心裂肺,像是吃了有毒的東西,心如刀絞卻又吐不出。
我不敢近前,只能扒著門縫往外看。它難受得不行,鉆到磨盤底下,不久又踉蹌出來,還是那樣轉。大門外也圍了不少人往里瞧,都一臉迷茫和驚恐。東胡同做豆腐的人說:“打死吧!瘋了,咬著人麻煩!”我聽了很氣憤:“不是您的狗,少管閑事!”
小白更瘋狂了,頭在墻上撞得砰砰作響,嘴角流出的白沫里還有血。最終小白耗盡最后一絲力氣,摔倒在地,腿蹬了幾蹬,氣絕身亡。我出門看著沒有合眼的小白,趕緊找了一個破草苫子蓋住它,心疼不已。
五爺爺住前街院里,我去院里挖了個大坑,把它埋在葡萄架下。小白就這樣愴然走了,它的死因卻一直是我的心病。幾種猜測都被我否定了,它不可能吃了藥死的老鼠,身上沒傷,也無被人打的可能。
那架葡萄長得實在好,蓬蓬勃勃地覆蓋了半個院子,一到秋天奶香飄得滿街都是。它的籽粒和現在的巨峰、提子都不一樣,是牛心狀的,可我一直沒有查詢到它的學名。漸漸的,小白被遺忘了。吃葡萄,年年吃年年陶醉,想起小白的估計也只有我,頂多還有和它朝夕相處的我的家人。外人,不需要勞這個神記住它。宏說:“好狗命短!”這話不新鮮,是句陳舊的套話,邏輯上也不嚴謹。
后來家里又弄來一條灰狗,是個德牧串,比小白壯,也惡,見生人就咬。它彈跳很出色,上香臺子、大桌子輕而易舉,妹妹叫它“跳跳”。因心里仍放不下小白,我無法對它滿腔熱忱,連這只狗是怎么樣的結局,我都忘得一干二凈。我只記住了小白,一條不一樣的狗。罵人愛拿狗說事,好像狗是底線,他們沒看過蒲松齡的《義犬》,那只狗稱得上道德楷模。狗對一個人忠誠,天經地義,比見誰都搖尾乞憐好。
小白它不是瘋狗。多年后我曾參與過一陣犬業協會工作,見過形形色色的狗,東奔西走地出席過很多狗展、狗賽,也認識了不少專治狗疾的獸醫。我向一位著名的獸醫描述我的小白之死,他略作沉思回答我:“你那只狗得的應該是病毒性腸炎,長期得不到醫治,內臟全潰爛了,疼痛難忍,所以像瘋了一樣。”教授解了我多年疑惑,對于小白的死,我也就釋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