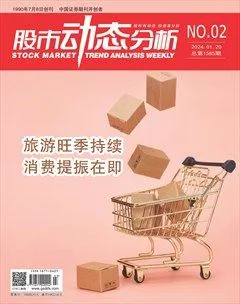2024年中國經濟:一點思考和期望
李迅雷
這是最近一場會議演講的記錄稿。2024年已經來了。結合去年12 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談談對2024 年經濟政策的理解和經濟走勢展望。
2023 年經濟增長5% 左右的預期目標應該實現了,但2024 年壓力也還比較大。記得2021 年、2022 年連續兩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用了“三重壓力”的提法,即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2023 年末的經濟工作會議則提了六個方面的困難或挑戰。前三個分別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轉弱,這三個分別對應了前兩年所提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只是提法有所變化,描述困難更加具體。
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呢?有效需求是指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我們過去講中國的需求潛力很大,但是需求潛力大,沒錢怎么消費?對這個問題我糾結了很多年。記得2016 年全社會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覺得確實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但也不能忽視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因為我看到有一個異常現象:從2012 年初到2016 年8 月份連續四年中國的PPI 都是負的。
對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轉弱”這兩大問題,我認為也與有效需求不足有關。需求上升了,供需關系才能平衡,過剩現象自然緩解,預期也會轉強。
另外,這次除了前面三大壓力之外,還提了三條,分別是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過去連續兩年都會提三大壓力,這次又新提了三個,說明什么?我們2024 年可能面臨的困難更多,任務可能會更艱巨。
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面臨的問題講得比較透,比較深入。這次也不例外,反映出2023 年二季度以來,中央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問題摸得非常清楚。這對于解決問題至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依據。
如何看待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我覺得確實是不同以往了。過去我們講到困難和問題,感覺都是暫時的,即便這條路走不通還可以走另外的路。現在來看,過去容易做的事情都已經做了,留下來的都是不太容易做的,都是繞不過去的。
十九大報告就提出要實現高質量增長,要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要以科技來引領。但從國際經驗看,轉型過程是非常艱難的。每個國家它都有自己的增長模式,當年日本增長也很快,但是當它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經濟就步入到一個低增長的階段,甚至是長期低增長或負增長,徘徊不前。
如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應對這些困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九大任務,九大任務的第一條就是產業政策,“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相比2022 年會議第一條“擴內需”,這次中央把科創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了突出位置,實際上也是要實現經濟轉型,因為科技創新才能夠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核心要素。
但是,科技創新的投入往往是巨大的,但依賴科技進步來提升勞動生產率往往不是立竿見影的,或許存在一個較長的時滯,如歷史上三次工業革命,從蒸汽機、內燃機、計算機的發明到真正獲得商業應用,一般都需要滯后幾十年時間,但經濟保持穩定則是當務之急。為此,政策上需要協調好輕重緩急。
會議提出要統籌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提出2024 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適度加力”,與2023 年的“ 加力提效”的提法相比,似乎要審慎。從2023 年國家的廣義財政支出的規模來看,感覺比2022 年要少了一些。現在通常講的官方財政赤字率是狹義的,覆蓋面比較少,廣義財政支出就包括地方專項債、特別國債、三大政策性銀行發行的債等,這個范圍是比較廣的。
而美聯儲加息周期的結束,有利于中國釋放一個貨幣政策空間,因為我國實際利率水平比美國要高,應該可以采取降準降息等舉措來應對經濟收縮問題。
因此,2024 年政策環境可能會比較寬松,盡管貨幣政策要“精準有效”(2022 年年末的提法是“精準有力”),但不等于我們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一定會縮手縮腳。2024 年要防范發生系統性的風險,故政策的總基調還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保持底線思維,確保不跌破底線,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如果在經濟運行中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險,則政策的相機抉擇或逆周期政策一定會是實施的,大可不必過度擔心。
2024 年,我國將迎來建國75 周年,同時基于2035 年GDP 的翻番目標必須完成,2024 年GDP 的增長目標不宜過低。為此,對2024 年的GDP 增長,現在賣方研究或者國內金融機構普遍預測都是5% 左右,境外金融機構包括IMF、OECD,以及高盛等投行的預測普遍在5% 以下,4.5%-4.8% 左右。
但2024 年GDP 如果要實現5% 的增速,必須得加大政策的寬松度。而宏觀分析師們也普遍認為要加大基建投資的力度才能實現該目標。因為消費是慢變量,不能期望短期內有大的提升,出口受制于外需,唯有基建與房地產可以成為調控GDP 增速的重要工具。但問題是,若今年靠基建拉動來實現5% 的增速,明后年怎么辦?基建投資最終屬于增加供給,我們面臨的主要壓力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基建項目的投入產出比不高,同時又將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這是否與當下提倡的高質量發展目標有點南轅北轍?
我建議2024 年GDP 的增速預期目標大概要維持在全球平均水平的1.5 倍到1.7 倍。如果2024 年全球GDP 增速是3%,1.5 倍就是4.5%,1.7 倍就是5.1%,也就是在4.5%-5.1% 之間。那么,如果2024 年全球GDP 增速是2.7%,那么,就是4%-4.5% 之間。因為天有不測風云,就像三年疫情拉低了我國的GDP 增速一樣,中國是開放型經濟大國,受國際影響較大,應該按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要更好統籌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堅持以質取勝,以量變的積累實現質變”。
2024 年大家的預期可能還是偏弱,我覺得應該看到好的方面。如一些風險在不斷釋放,房價下跌就是風險釋放的過程,股市處在歷史低位,機會或大于風險。現在我們認識到問題,且越來越多的問題大家已經達成共識,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期望2024 年的政策力度會更大一些,只有超預期才能穩預期,尤其希望更多的政策能從增加居民收入和促消費層面發力,通過活躍資本市場來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通過增加社保收入來提高消費意愿,通過擴大消費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通過增加消費訂單來解決民間投資意愿不足等問題,以推動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克服種種困難,穩中向好、以進促穩。
經過三年的調整,A 股的估值水平已經步入價值投資區間,資本市場或能夠見底回升;房地產在調整過程中的對經濟的負面效應也會漸漸地減少。當大家預期普遍偏悲觀的時候,往往也是機會在增大的過程,因為按照相反理論,大家普遍偏悲觀的時候,往往實際結果會比預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