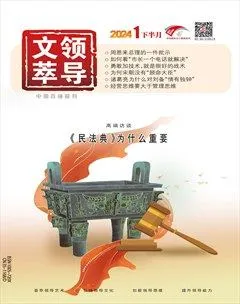為何宋朝沒有“顧命大臣”
吳鉤

兩宋300余年,也曾出現過幾個未成年便繼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繼位時只有12歲,宋哲宗繼位時只有9歲,宋恭帝繼位時只有4歲。
不管是宋仁宗,還是宋哲宗,登基時都還是孩童,當然離不開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輔政與教導。不過宋朝未設顧命制度,老皇帝在終臨前,并沒有特別指定若干重臣為托孤大臣。盡管如此,那些先帝時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權交接過程中及新朝開局時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乾興元年(1022),宋真宗駕崩,留下遺命:12歲的兒子趙禎繼皇帝位,“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根據真宗的遺命,輔臣商議如何起草遺詔,宰相丁謂欲討好劉后,提出將“權”字刪掉。“權”有從權、暫時的含義,去掉這一字,即意味著承認太后擁有聽政的正式權力。參知政事王曾堅決不肯讓步,說女主臨朝已是非正常情況,稱“權”已屬無奈,你還想將“權”字刪去,是什么意思?丁謂不敢再堅持己見。
宋神宗病重之時,宰相蔡確曾有意擁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為皇儲,為此他試探過另一名宰相王珪的意見,但王珪說皇上有子。他認為皇位應該由神宗的兒子趙煦繼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即趙煦)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哲宗繼位,由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是同情舊黨的人,原來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大臣,重回朝廷輔政,大儒程頤則被召來擔任小皇帝的經筵官,負起教化哲宗、養成君德的大任。
從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大臣,雖然沒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們卻在立嗣、太后臨朝等重大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這些宰相,雖無顧命大臣名分,卻盡到顧命之責,輔佐幼主,穩定朝綱。
宋朝有一個現象:皇帝若是沖齡繼位,都出現過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與漢唐相比,宋朝雖然先后有多名太后臨朝聽政,卻從未產生“女主禍政”的亂象,也沒有誕生一名像漢朝呂后、唐朝武則天那樣把持朝政的女強人。這又是為什么?
從制度角度來解釋,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權力結構。
君主作為天下道德的楷模、國家主權的象征、國家禮儀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貴的地位與最高的世俗權威。
同時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雖然一切詔書都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但基本上都是執政官熟議后草擬出來的意見,皇帝照例同意即可;治理天下的執政權委托給宰相領導的政府,用宋人的話來說,“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監察、制衡政府的權力則委托給獨立于政府系統的臺諫,“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
就如秦觀所言:“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君主只要協調好執政與臺諫的關系,使二者達成均衡之勢,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中,出現一個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會對整個帝國的權力運轉構成巨大的障礙,因為皇權已經象征化,君主不用具體執政。也沒有必要為小皇帝專門成立一個顧命大臣團隊,宰相領導的政府與制衡政府的臺諫保持正常運轉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權,垂簾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為皇權象征化,臨朝聽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現權力膨脹。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權責,不容相侵,一旦出現女主專權的苗頭,立即就會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和抵制。這一點跟清朝的政體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太后垂簾聽政代行皇權,當然也就獲得了專斷、親裁的絕對權力。
顧命大臣之設,通常是應皇權專制之需的產物;而顧命大臣之被誅,則是其隱權力通過自我繁殖,高度膨脹,進而威脅到皇權專制的緣故。宋朝政體并非皇權專制,君權、相權、臺諫權各有分際,權力的運行自有程序與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著在一個理性化的權力結構中,突兀地設置顧命大臣攝政。
(摘自《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